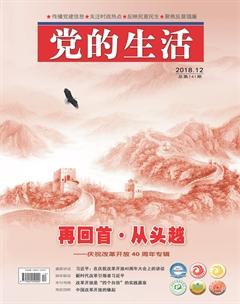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蓬勃偉力
1978年關于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思想理論根源,就是馬克思的思想、馬克思主義
《理論周刊》:陳教授,您好!對我國思想理論界來說,今年是一個特別有意義的年份,既是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又是紀念真理標準大討論40周年。那么,如何看待這兩個具有重大意義的紀念日在時間上的偶合與理論上的關聯?
陳先達:今年恰逢這兩個具有重大意義的紀念日同在一年,從時間角度說當然是偶然的,但從更深層次、從理論的關聯性說卻是必然的。
1978年關于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思想理論根源,就是馬克思的思想、馬克思主義。沒有馬克思的思想指導,就不可能出現以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核心命題,因而就找不到處于歷史轉折關鍵時刻突破人們思想束縛的強有力的哲學指導;反過來說,如果當時不通過這場大討論,解放思想,恢復實事求是路線,中國就不可能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確立“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路線,逐步走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道路,創造性發展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
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在世界上馬克思主義發展處于低潮、社會主義受到極大損害時,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成就喚起世界對馬克思主義的重視和信心,樹立起對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新認知。
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紀念和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是兩件事,又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如果從真理標準大討論中、從改革開放中看不到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威力,或者從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偉大成就中看不到馬克思的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價值,只看到時間的偶合而看不到理論的必然,把兩個紀念視為互不相關的兩件事,就不可能深刻理解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力量。
真理標準大討論具有學術性,不是純粹為政治需要而臆想出的命題
《理論周刊》:社會上曾有一種觀點,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是出于當時的政治需要,不具有學術性。您對此怎么看?
陳先達:這種觀點是片面的。毫無疑問,1978年真理標準大討論是政治性的討論,不是純學術討論。它是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關節點上,對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命運和走向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重大政治事件。但并不能因此就說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命題不具有學術性,是純粹為政治需要而臆想出來的命題。
真理標準問題本身是一個哲學問題。在中外哲學史上,哲學家們曾為認識正確性標準進行過無數次爭論。中國哲學史上莊子與惠施的濠梁之辯,“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和“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的反復詰辯,以及西方哲學關于理性標準與經驗標準的爭論,都沒有科學解答這個問題。只有馬克思才科學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因為任何主體標準或理性與經驗標準都不可能與實踐標準相比。實踐高于認識,也高于任何主體的觀念;實踐具有普遍性和直接現實性的品格。
正因為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是具有真理性的判斷,它才有可能在1978年的歷史轉折中發揮思想解放作用。可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揮的作用,是真理的作用,是馬克思主義的作用,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說過,“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最終要落實到怎么用上”,并引用古語“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作為論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說到底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并在運用中創造性發展。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大討論就是一次卓有成效的運用。
真理標準大討論為我們提供了繼續解放思想、全面深入推進改革、衡量正確與錯誤的“金標準”
《理論周刊》:真理標準大討論已過去40年了,在今天還有什么現實意義?
陳先達:真理標準大討論是在特定時期發生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可實踐作為認識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標準是普遍真理,并非僅僅適用于中國1978年的歷史轉折時刻,“用過”之后便束之高閣。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始終堅持實踐和實踐標準的觀點。在40年的改革開放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都是立足于實踐,在實踐中不斷向前發展的。同時可以說,每一步都是在接受實踐的檢驗。
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始終是有效的。而且我們應該懂得,實踐作為真理標準的雙重含義——既是真理性認識之所以是真理的標準,也是錯誤之所以是錯誤的檢驗標準。因此,實踐既可檢驗真理,也可糾正錯誤。不能認為真理性認識標準是實踐,而是否錯誤是主觀認定的。其實,不少被主觀認定是錯誤的東西,事后在實踐中最終被證明是正確的情況并不罕見。無論真理或謬誤,一切都應該通過實踐檢驗,這才是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
真理是有用的,但有用的不等于真理。這是馬克思主義真理觀和實用主義的分界線。毛澤東同志說過:“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證明了是對的。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從這個角度說,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不僅拓展了我們當時的理論視野,而且在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都成為我們繼續解放思想、全面深入推進改革、衡量正確與錯誤的“金標準”。
在當代哲學社會科學中,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僅具有政治性,而且具有極高的學術性
《理論周刊》:在馬克思誕辰200年之際,人們對馬克思及其著作的關注與日俱增,討論也非常激烈。有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政治性的、非學術的。該怎么看待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性與學術性?
陳先達: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性源于馬克思經典著作本身的政治性。馬克思經典著作本來就具有鮮明的政治性和明確的階級性,因為馬克思本來就是為工人階級和人類解放而進行研究和著述的。《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最著名的經典著作,誰敢說《共產黨宣言》只是學術經典著作而不具有政治性呢?事實上,它至今仍然使資本主義統治者感到震怵和恐懼。其實,何止《共產黨宣言》,可以說馬克思的每部著作,無論是像《資本論》這樣的皇皇巨著還是發表在報刊上的評論,無論是正面闡述自己觀點的著作還是與對手或論敵的論戰文章,無不是既具有高度學術性又具有立場鮮明的政治性。這并不奇怪,馬克思首先是個革命家,這就決定了馬克思的經典不可能只是學術著作而不是具有政治傾向性的著作,因而對馬克思經典研究不可能避免雙重特性——學術性和政治性。你只要讀讀西方有些學者從馬克思經典中斷章取義得出的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結論就可以看出,他們是純粹的學術研究而不具政治性嗎?事實上,對馬克思的經典的研究,完全可以有兩種不同的立場和態度。我們應該重視馬克思的經典,認真研究馬克思的經典,學習馬克思的經典,因為它能幫助我們掌握和精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馬克思的經典是我們的理論寶庫,而非只是作為后人注釋和考證的文本。因為在注釋和考證中,必然會滲入研究者詮釋文本的理論結論和政治傾向。
另外,確如你所說,在有些人看來研究馬克思主義沒有什么學術性,仿佛只有研究中外某個大思想家的著作才叫學術研究。這是對學術性的錯誤理解。對中外著名思想家的研究,當然具有很高的學術性,我們需要專門人才進行深入研究,正確詮譯和解讀他們的思想,以便汲取他們的智慧。我們提倡學習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原因正在于此。但不能因為馬克思主義鮮明的政治性而貶低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學術性。在當代哲學社會科學中,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僅具有政治性,而且具有極高的學術性,因為它是建立在對世界發展普遍規律和人類社會規律揭示基礎上的學說。恩格斯曾經說過:“人們的意識決定于人們的存在而不是相反,這個原理看來很簡單,但是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立即發現,這個原理的最初結論就會給予一切唯心主義,甚至最隱蔽的唯心主義當頭一棒。”我可以大膽斷言,馬克思主義中每條基本原理都具有極豐富的內涵,要真正弄懂、弄通,能闡述、能運用,可得下一輩子功夫。
自馬克思主義產生之后,馬克思主義研究逐漸成為一門顯學。不僅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和理論家們精心研究馬克思主義,而且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同樣關注馬克思主義研究。在當今世界,馬克思主義研究學者之多,是任何一個思想家都無法相比的。不管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不同意甚至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學者,都無法繞開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學術寶庫,是哲學社會科學中一座巍巍學術高峰。
值得一提的是,當前,我們應該反對那種以學術的名義把馬克思以后的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對立起來的觀點,有些西方學者往往引用馬克思在特定環境特定語境下說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句話作為立論根據。其實,1890年恩格斯在批評德國黨內的一些大學生的幼稚行為時,曾明確指出馬克思這段話的真實意義是批評當時法國的共產主義者,是為了區分“龍種與跳蚤”。
另外,馬克思主義是科學,但并不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者的成果就天然具有學術性。一門學說的學術性和研究者的學術水平是不能等同的。實際上,在任何學科中,研究者的水平都是參差不齊的,有高有低,就像自然界,有高峰,有平原,也有低谷。每門學科都有大學者,也有成就一般甚至毫無成就可言的人。這無關學科的學術性,而是與研究者個人的資質、條件與努力有關。我們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在增強政治意識的同時,應該努力提高自己研究和教學的學術含金量。馬克思主義研究成果的含金量越高,學術性就越強,就越有說服力。
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我們要始終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觀點,立足實踐,繼續解放思想,大膽創新。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我們要無愧于馬克思主義這個稱號,就必須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始終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道路。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我們應該當“龍種”,決不當“跳蚤”。
《理論周刊》:謝謝您接受我們的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