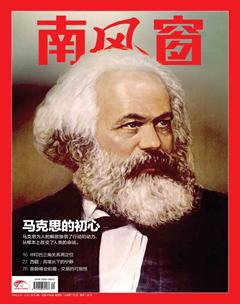18世紀中歐貿易與“中國趣味”
張國剛

大海航時代對于絲綢之路最重要的影響,就是中國商品直接輸往歐洲大陸和英倫三島。具有異國情調的中國商品大量輸入歐洲,不僅改變了歐洲人一些生活習慣,也成為歐洲人認識中國的第一窗口,還滋長了流行于18世紀歐洲上流社會的充滿異域情調的獨特藝術品味—“中國趣味”。
所謂“中國趣味”(Chinoiserie),乃是指17和18世紀歐洲社會流行的一種風尚,主要表現在室內裝飾、家具設計、陶瓷樣式、紡織品花紋和園林景觀造型諸多方面,受到“中國風格”的影響。
中國趣味得以形成的直接靈感,來自于那些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包括瓷器、漆器、織物、壁紙。
17世紀末有人在《世界報》(World)上撰文說,中國壁紙在豪宅中極為流行,這些房子里掛滿最華麗的中國和印度紙,上面滿繪著成千個根本不存在的、想象出來的人物、鳥獸、魚蟲的形象。
18世紀初,中國絲綢也已在英國蔚為風尚,公眾審美觀由東印度公司的進口商品所指導,連當時的安妮女王(1665-1714)也喜歡穿著中國絲綢和棉布露面。17世紀末期,英國東印度公司運來的一船又一船瓷器刺激了英國和歐洲市場對這類商品的需求,英國上流社會以收集和展示瓷器相標榜。類似的風氣在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宮廷同樣盛行。
進口中國商品俘獲了歐洲顧客的人心,本地的生產者和經銷商自然不甘寂寞,出于產品競爭的考慮或借助時尚獲利的考慮,開始摹仿這些中國的櫥柜、瓷器、繡品上的裝飾風格,這便產生了中國趣味。先是工藝品和日常用品等小東西的仿制,如制造瓷器、絲綢、壁紙;進而是室內裝飾與園林設計這些大工程,誕生了風靡一時的“英華園林”并在今天都留下許多建筑痕跡。
1753年7月24日,瑞典王后收到國王贈送的一件特殊生日禮物,一座木結構的中國亭,她描述道:
“我吃驚地突然看到一個真正的神話世界……一個近衛兵穿著中國服裝,陛下的兩位侍從武官則扮成滿清武官的樣子。近衛兵表演中國兵操。我的長子穿得像個中國王子一樣在亭子入口處恭候,隨侍的王室侍從則扮成中國文官的模樣。……如果說亭外出人意料,亭內也并不少讓人驚奇……里面有一個以令人賞心悅目的印度風格裝飾成的大房間,四角各有一只大瓷花瓶。其他小房間里則是舊式日本漆柜和鋪著印度布的沙發,品味皆上乘。有一間墻上懸掛、床上鋪蓋印度布的臥室,墻上還裝飾著美妙的瓷器、寶塔、花瓶和禽鳥圖案。日本舊漆柜的一個抽屜里裝滿各種古董,其中也有中國繡品。廂廊陳設桌子:其一擺放一套精美的德累斯頓瓷器,另一張則擺放一套中國瓷器。欣賞過所有東西之后,國王陛下下令演出一場配土耳其音樂的中國芭蕾。”
這座所謂中國亭在建筑上到底有幾分中國風味不得而知,但顯然它就如17世紀末期流行起的中國屋一樣,以內中陳設有關中國的物品而得名。顯然,在瑞典這座中國亭里,各種異國情調和歐洲風味混為一體,歐洲人創造的“中國趣味”,成為他們所理解的中國的實體形象。
另外一種創造來自東印度公司。他們給中國工匠提供加工圖樣,迎合歐洲顧客的需要,這樣便形成了中國趣味的另一個制造地。
比如18世紀中期進口到歐洲的中國玻璃畫,常見的主題是富裕的中國男女在樹蔭下悠閑舒適地過活,或者中國仕女帶著貴族式的無所事事的憂郁神情坐在花園或牧野中,這都是專門設計來吸引歐洲買主的。這不難理解,當時的歐洲,英國已經產生大批富裕悠閑的中產階級,法國那些被剝奪了政治特權而依然經濟富有的貴族們則麇集在宮廷,百無聊賴地以虛耗光陰為最高追求。這些中國畫實則正迎合了歐洲上流社會的理想。
中國進口瓷器在形制上亦做成符合歐洲人需要,比如英國公司訂購的便以英國銀器為模型,而此風以雍乾時期最盛。如此,歐洲人看到的究竟是中國瓷器還是歐式器皿,是中國人的生活風貌還是歐洲有產階級的人生理想?但恐怕他們以為從這些圖形、紋飾、質地、形狀中所看到的就是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