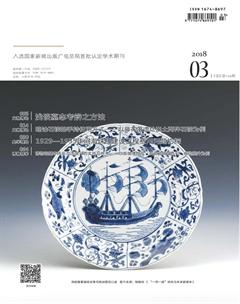晚清司法運作實態之試析
袁昭昭
摘 要:從戰國時期李悝制定的第一部比較系統的成文法典《法經》,到清朝乾隆時出臺的最后一部法典《大清律例》,中華法系已歷經兩千多年。目前已有學者對我國古代司法行政體制進行了研究,但關于司法在實際運作中的情況考察相對較少,特別是以個別案例為研究路徑。文章以同治年間的刺馬案為例,對當時的司法運作進行了簡單的分析。
關鍵詞:晚清;司法運作;刺馬案
1 刺馬案之梗概
馬新貽,字谷山,山東菏澤人。1870年7月25日,結束檢閱箭道任務的馬新貽在返程途中被刺客刺傷,兇手張汶祥被當場擒獲。次日,馬新貽死亡。
案發后,江寧布政使梅啟照、江寧將軍魁玉等人提訊張汶祥。8月23日,魁玉向朝廷匯報案情。奏折表明刺客言語顛倒,僅交代姓名及籍貫,拒絕說出作案理由。9月1日,魁玉再次上奏表態對張汶祥的審訊并無多大進展,但已抓獲收留張犯的朱定齋、周廣彩二人,以及向馬新貽跪道求助的王咸鎮和指引者劉學。除此之外,魁玉加強了安保力度,晝夜巡防,添加兵勇,保護教堂[1]。朝廷在接到下屬的奏折后,認為此案駭人聽聞,必須要嚴懲兇犯,并連發三道諭旨,令曾國藩調任兩江總督,安徽巡撫英翰加強地方治安及長江防范,魁玉研訊確情,嚴懲兇犯[2]。隨后,任命江蘇巡撫張之萬會同問案,但審訊工作依舊進展緩慢,被朝廷責令重審。12月12日曾國藩到江寧,張之萬、魁玉總算給出一個交代。但是,朝廷對此回應并不滿意,令曾國藩會同嚴訊,并派鄭敦謹前往參與審理工作。最后,此案以張汶祥受海盜龍啟沄等人鼓動,為報私仇定案。綜合張汶祥所犯,情同叛逆,擬判決其凌遲處死,其他相關人犯,一并判處不等刑罰[3]。
2 本案所暴露的司法運作的弊端
作為古代中國留給世界的重要文化遺產——中華法系淵源已久。完善的司法制度若不付諸實施,就不會體現其優勢,更不利于維護社會穩定。作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馬案,在實際的審判過程中,所暴露出來的弊端不止一處。
2.1 審判中的瑕疵
清代官吏的司法職責很重要,清代官吏在處理日常政務的過程中,司法訴訟的處理占據重要位置。承審官員在審理案件時,首先根據訴狀和犯人口供來了解案情;其次,通過勘查搜集證據,以此作為判案的依據。
刺馬案的案情所述中,如果從常理推斷,似乎并無不妥。但其中的“尚屬可信”卻讓人瞠目結舌。作為司法審判官員,對于案犯所交代的供詞,沒有用證據證實,反而憑己見揣測其真實性;其次,張汶祥在被抓之時,曾有“養軍千日,用軍一朝”之詞,據此,此案必有主使之人,但幾次審理的結論中,都稱并無主使之人;再者,據驗傷表明,受傷的地方皮肉縮回,但是沒有出血,脖項腫脹,十指呈現青色。這些癥狀表明,馬新貽之死,出自毒藥。但在結案中寫道“刀鋒白亮,量視血陰,計投入三寸五分,暫無毒藥”[4]。這些作為案件的可疑之處,承審官員在調查取證之時,并未對其進行佐證,以案犯“語言顛倒”“堅不吐實”的供詞帶過。這是對案情中取證環節的踐踏,倘若沒有足夠的證據作為基礎,很有可能出現誤判、錯判的情況。例如“晚清四大冤案”之首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就因地方官吏懶于去核實案情的細節,僅憑自己的主觀臆斷確定了兇手,在結案過程中發現存在疑點,不但沒有急切地尋求真相,僅忙著收集證據,將案件定案。后來在《申報》的追蹤報道下,以及朝廷意欲打擊地方督撫,重塑中央權威的前提下,這個鐵案才獲得平反。回顧當時的歷史,類似的案件多如牛毛。可見,承審官員在辦理訴訟案件時,要著重取證,做到公正合理,避免冤案、錯案的出現。
與此同時,這時因積案造成的“訟累”和判官的“魚肉百姓”為特征的司法制度的衰落,早已不能適應于當時的現實社會。如1851年頒布施行的“就地正法”制度,雖使得銹死的國家機器得以重新運轉,但要想使封建統治的正常秩序得以恢復,恐難以實現,更不可能達到民安國治的效果,反而激發了百姓的反抗。由此可見,這時期的司法制度以及司法在實際運作中都遭到了嚴重的毀害。
2.2 承審官員的雙重身份及皇權政治的干預
在我國,以皇權至上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在清朝增設軍機處、大興文字獄之后,達到了頂峰。與此同時,司法的行政體制也發展到成熟時期。
司法審判的結果最終要由皇帝批準。即使在審理案件過程中,皇帝也會通過庭審、朝審等方式參與其中,甚至于直接參與審判。如此以來,承審官員在行使自己司法審判權利時,很難做到公正合理。
刺馬案的發生,因受害人身份異于黎庶,所以朝廷格外關注。僅在接到奏折后,就連下四道上諭,向承審官員施加壓力,望其盡快研訊確情,嚴懲兇犯。可見朝廷上層對此案的重視。審理過程中,朝廷多次要求承審官員匯報案件進展,并作出指示。最終在擬判后,還需請旨批準,方可結案。
在此案件中,皇帝對本案的特殊關注體現在對案件審判結果的干涉。這種皇權控制司法的做法,最初可能源于預防司法徇私舞弊,但在實際運作中卻妨礙了司法的獨立審判,使得公正的法治逐漸變成了人治。立法由皇帝指派若干大臣或者六部編寫,《大清律例》由刑部整理例文并重修。六部之刑部,作為司法行政執行的機構,都察院負責監督,與大理寺協調。由此看來,司法運作貌似獨立。但是,這些部門都對皇帝負責,它只能在皇權允許的范圍內實現一部分的獨立。司法審判只有不受政治、人倫、輿論、法律文化等因素的影響,才能做出公正的判決。因此,一個有效的司法行政運作,必須要有完善的運行模式,否則必然漏洞百出。
2.3 司法審判中的維護儒家倫理秩序和封建等級制度
中國古代的法律自誕生之日,就充當著族姓統治的合法武力,其功能也就表現為統治者的鎮壓工具,簡單一點來說就是刑。這種刑罰制度流于后世,便成為了古代法的根本特征之一。后來,人們發現這種單純的刑罰毫無意義,必須和一定的行為規則相匹配,而這種規則就是我們所說的道德。因此,中國古代的法經常與倫理道德結合,從而維護儒家倫理和封建等級制度。
刺馬案中,受害者馬新貽為朝廷命官,作為晚清政壇上頗有才能的重要人物之一,被一介平民所刺死,實屬駭聞。作為統治階級的官員來說,這是對其統治的挑釁,他們認為張汶祥的行為實屬叛逆,必須嚴懲,凌遲處死,以此達到殺雞儆猴的效果,企圖維護現實的社會秩序和封建等級制度。
除此之外,春阿氏案因涉及“人倫”,最后判處春阿氏監禁。繼續詳細訪查,可據實定斷等,這些案件的審理均表明,所謂的“孝道”“人倫”“君臣父子倫理觀念”無不引導著案件的審判。
由此可見,晚清時的司法審判并不完全是法律公平正義的體現。司法的行政體制實際運作的過程,伴隨著維護儒家倫理規范和封建等級制度,如此以來,對成文的法典的規定則會出現違背的情況,并且案件的處理會或多或少的存在現不公平現象。
3 結語
司法審判官員作為定案的負責人,倘若一旦心理失衡,就會產生無法估量和難以預計的后果,“出格”的判決會使國家的司法審判和社會公德缺乏公信力。中國古代司法審判時,地方乃至中央官吏既是行政長官,也是司法長官,他們在處理刑事或者民事案件時,調查取證是其重要環節。沈衍慶指出“錢債之案必以券約為憑”[5]。但是晚清時由于司法制度的破壞,導致實際運行過程中出現了憑空想象、羅織罪名以定案的情況。刺馬案中的“尚屬可信”等實例,都在說明作為審判的司法人員缺乏公正力,對正常的司法程序進行了毀壞。
近年來,人們對于司法機關的案件的審判過程以及結果的關注越來越多,公正合理的司法秩序對于社會安定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參考文獻
[1][2][3][4]高尚舉.馬新貽文案集錄[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1.
[5]楊一凡.中國歷代判例判牘(第十冊)[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