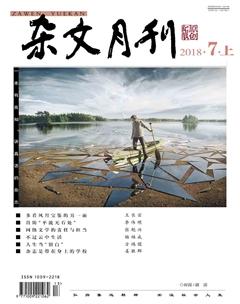雜文是大眾之文
相玉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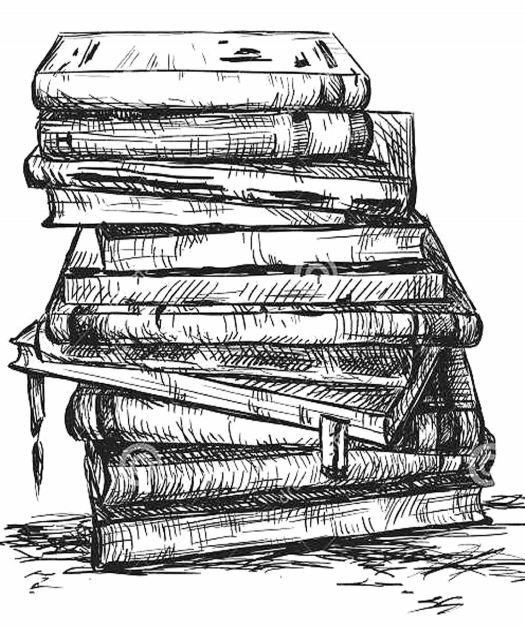
謹商榷彭友茂先生《雜文,應是文學家之文》(《雜文月刊·2018·3上》)。
我認為,雜文,不一定是文學家之文。
“研究文章的歷史或理論的,(才)是文學家、學者”(魯迅《而已集·讀書雜談》)。寫點雜文的人,絕大多數不是“研究文章的歷史或理論的”,也就不配“文學家”名號。就近看,《雜文月刊》的作者,稱得上“文學家”的有幾人?了了。其實,雜文作者并不在乎頭銜什么的,否則,就很可能歸于“空頭文學家”之流。魯迅曾在其遺囑中告誡兒子周海嬰,“千萬不要去做空頭文學家”。魯迅的這個告誡,于現在的雜文作者們也適用。
彭文說,雜文是“文藝性論文”,沒錯,但不全面。《中國大百科全書》:“一些小品文、隨筆、札記等,都可以叫做雜文。”彭文說,“雜文歸于散文類,那畢竟是一種粗分”。不,不是粗分,《文學概論自學輔導》肯定地講:“雜文屬于散文的一種。”
彭文認為雜文與科學著作有5個“根本的區別”。實際是,根本沒有區別。
“從內容來說”,雜文不也得如科學著作那樣“材料翔實、準確無誤”嗎?雜文是不可以憑空虛構的。“從形式來說”,雜文不也得如科學著作的語言那樣“貴在樸實明白”嗎?雜文是不可以玩弄辭藻佶屈聱牙的。“從作者來說”,雜文不也得如科學著作那樣“用判斷和推理說話”嗎?雜文之言豈可無須判斷且不經推理?豈可不過腦子蠻不講理?“從讀者來說”,雜文不也得如科學著作那樣“訴諸于讀者事實與理智”嗎?雜文豈可脫離事實喪失理智?“從功能來說”,雜文不也是如科學著作那樣是“傳遞信息的工具,重在實用”嗎?雜文豈可不傳遞正能量,不“為時而著”?
彭文講到的雜文的三個特點,也須商榷。
一是,實現“戰斗性與愉悅性和諧統一”,難。“戰斗性”一般來說是對敵人而言,這與雜文的功用不符。棄用“戰斗”改用“批評”更妥帖。批評和被批評,都是很嚴肅的事情,特別是被批評,很難“愉悅”。痛改前非就好,“痛”字當前,接受批評并愉悅著,那也太不嚴肅了吧。另外,需要明確的是,新時代的雜文除了“戰斗性”(實為“批評性”)也是可以贊揚的。贊揚,是對被批評對象的一種向上的推力,是一種正向的“比較性”引導,可收批評相同功效。
二是,雜文要實現“論辯性與形象性有機結合”,也難。雜文,將抽象的道理蘊含在具體可感的形象之中,自然好,但缺乏可廣泛操作性。既然雜文是“文藝性論文”,強調雜文“與形象性有機結合”,是強寫作者所難。閱讀發現,魯迅雜文“論辯性”的居多,“與形象性有機結合”的少。就近看,《雜文月刊》發表的文章,能做到“與形象性有機結合”者,亦寥寥。何況,讀者對此并無特別要求,他們主要還是“認理”,形象還在其次。
三是,“幽默、諷刺與文采巧妙運用”,當前語境下不合時宜,因為諷刺與挖苦、反諷同源。還是直來直去地批評的好,用不著拐彎抹角。自然,在批評中時不時地幽它一默也不錯。至于在雜文中要“與文采巧妙運用”,不具普適性,不是所有雜文作者都具有文采;此只可作為目標追求。事實上,只要把理說透了,令人心服口服,文采差點也算是好雜文。
十分贊同彭先生在文章結尾處所表達的觀點:“一個‘旱鴨子背會了《游泳大綱》也仍然可能會被淹死”。同理,一個雜文作者就算把“雜文作法”背得滾瓜爛熟,也是寫不出好雜文的。魯迅先生也說過“不相信‘小說作法之類的話”(魯迅《二心集》)。凡搦管擒章之時,都是由著自己的智商和情商毫無掛礙天馬行空地馳騁,鮮活接地氣。
本人悅讀雜文也寫點雜文,也就時刻在關注著雜文動態,因而有了這個商榷。此商榷如果對于在新時代新征程中的雜文創作有那么一丁點裨益的話,足矣。在商榷之中難免有誤謬,誠望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