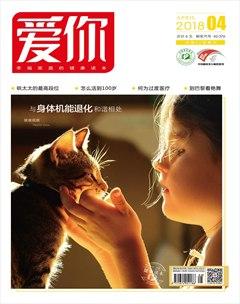我的貴重包包
2018-05-14 08:53:24劉西鴻
愛你·健康讀本 2018年4期
關鍵詞:醫院
劉西鴻
去年我在深圳,身體出現點狀況,連續兩晚半夜被心悸弄醒,第二天必須應約從羅湖搭火車趕去香港,一路恍惚,一路昏眩,到達朋友家時躺沙發上起不來。朋友讓我立即去醫院做個心電圖檢查。只是正逢周日,我懷里揣著兩張歐洲保險卡,沒細想就近入了港島半山的港安醫院。想只是拍個心電圖而已,我沒有先做一個規定動作:打電話給我的保險公司。我癱坐在走廊等醫生時,收費處姑娘過來要審我護照、保險卡,然后叫我掏出信用卡,當我面刷了個三萬港元的擔保,雖然滿心疑惑,我都依照做了,然后被遣去照心電圖,最后被告知要留醫觀察。第二天下樓結賬,姑娘打出一疊各種顏色、尺寸不同的收據,安慰我保險公司定會退還,然后又要信用卡刷刷,說:“給您退還一千港幣啦。”
我帶著港安醫院一疊五顏六色的收據回到法國,以掛號信把單子們寄往我的私立醫療保險和國家社會保險兩個部門,兩個月后,賬號上收到國家“社會保險”報銷的500歐元(合4600港元)。私立醫療保險呢,一分錢沒給報,在電話上耐心地教育我:“您去錯醫院了,我們的掛鉤醫院是瑪麗醫院,不是港安醫院!”
在港安醫院的那個晚上,姑娘入病房帶給我一樣禮品:一只新疆哈密瓜大小的洗漱包,杏皮色。這只包包我帶回來法國了。現在我出差旅行都帶上它,它滾動著活潑的幽默感,一分嘲諷,九分善意,對我來說比各種法國名牌包包更有看頭。這只包包里裝了一條簡單的道理:無論你買了啥保險,人生能遇得上一場險,叫僥幸;沒遇上險,叫慶幸;只是“萬幸”的事是不會常發生的。
(潘光賢 摘自《深圳商報》)
猜你喜歡
兒童繪本(2018年10期)2018-07-04 16:39:12
中國衛生(2016年10期)2016-11-13 01:07:44
中國衛生(2016年3期)2016-11-12 13:23:36
中國衛生(2016年3期)2016-11-12 13:23:20
中國衛生(2016年2期)2016-11-12 13:22:26
小朋友·快樂手工(2016年5期)2016-05-14 17:18:34
中國衛生(2015年8期)2015-11-12 13:15:20
中國衛生(2014年11期)2014-11-12 13:11:28
中國衛生(2014年8期)2014-11-12 13:00:54
中國衛生(2014年7期)2014-11-10 02:3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