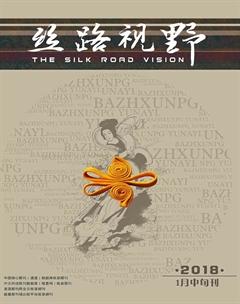農村集市分布和社區布局研究
【摘要】農村居民在日常交流中形成了各種各樣的“生活共同體”,這就構成了一個社區。集市、小學或活動中心都是今天農村社區重要的交流平臺和結點。以湖南為例,這樣的生活共同體所覆蓋的區域大致包括4000—10000的人口。未來的社區治理中,可引導地方將農村社區的范圍以集市為中心進行轄區范圍調整。
【關鍵詞】社區;芷江侗族自治縣;農村集市
一、農村中生活共同體的存在
農村居民的生活,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生活共同體”,或者稱為“社區”。人們在該生活共同體中,完成日常處理的事務。以湖南省目前農村居民實際情況來看,主要包括經濟生活共同體、行政生活共同體、教育生活共同體和文化生活共同體等。本文僅僅對農村中的經濟生活共同體進行研究。
經濟生活共同體,以日常經濟生產和商品交換活動為代表。它的核心設施是農村傳統市場,湖南農村通常每隔五天或三天有一次大規模的趕場。這個小小的貿易交換點,正是中國廣大農村商品經濟的高度體現,人們在這里完成市場交換。通常每個“場”,都有自己較為固定的農戶作為服務對象,每個農民都會選擇到鄰近的一個集散中心趕場。農村小型生活共同體,就是所有到一個農村集市趕場的農戶構成的集合。這個共同體的邊界不一定如行政村般清晰,那些地處兩個集市邊緣的農戶,常常會兩頭趕,或者說他們同時屬于兩個共同體。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現在各場所在地,大都有固定的店鋪,主要有南北雜貨商鋪、小餐館、種子化肥賣售點和榨油廠等小型加工廠,以及一些公共和公營機構,如工商管理站、郵局、農村信用合作社等,規模大的集市更有一些跨鄉鎮的機構,如工商所、稅務分局等。
每一種生活共同體覆蓋的農戶和村落范圍可能有所出入,但也呈現出大體一致性。具體而言,其人口規模4000—10000人不等,大的城鎮周圍則可能更多。調查顯示,農村居民對生活共同體仍舊具有高度的認同。這種內部趨同的生活共同體,將來還將進一步發育成熟,行政力應借助生活共同體來促進農村社區的全面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在表現上,則應鼓勵各村按照農村小型“生活共同體”的范圍進行合并。
二、以生活共同體進行農村社區調整的個案分析——芷江侗族自治縣為例
在經濟生活方面,每一個“鄉村小型生活共同體”多有自己的商品貿易點,所有經常性定期到這個地方趕場(趕集)的農戶就構成了“鄉村小型生活共同體”。鄉村中的集市并不都是天天有市開,現在最多的是開五日市,也有的開三日市(其實是十日三市,即每逢農歷一四七或二五八或三六九開市),十日市。這種鄉村經濟活動情況在中國廣大中西部農村非常普遍 。
為研究方便,本文選取了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縣作為研究的對象。芷江侗族自治縣位于湖南省西部,緊鄰貴州省,隸屬懷化市。潕水河、320國道、G60高速公路、湘黔鐵路和滬昆高鐵幾乎呈平行狀東西向穿越該縣,并有民航芷江機場。芷江縣清代是沅州府所在地,為當時湖南西部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之一。
目前芷江侗族自治縣一共有27個定期趕場的農村集市(當地俗稱“場”)。除縣城芷江鎮外,21個定期趕場的農村集市同時也是鄉鎮政府所在地,5個集市位于非鄉鎮政府所在地的村,1個位于縣城邊緣。禾梨坳鄉、大龍鄉、冷水溪鄉、大樹坳鄉、艾頭坪鄉和竹坪鋪鄉的政府所在地沒有定期趕場的習慣,但是它們的鄉政府駐地也有一些固定的商業網點。其中羅舊、新店坪、碧涌分別是該縣東部、西部、南部的中心集市,集市規模較大。芷江的農村集市均為五日市。
村一級組織中,合并前芷江侗族自治縣共有299個村,另外縣城內還有7個居民委員會。2000年時縣城內7個居民委員會合計為32910人,其余301村人口為301319,平均每個行政村的人口為1001人。2010年普查時,各村的平均人口跌破1000人。
以土橋鄉合并前的13個村為例,可以鄉鎮政府駐地或傳統集市所在地為核心,聯合附近村莊組成3個農村“生活共同體(社區)”。
第一個是土橋生活共同體(社區),包括土橋村、向家莊村、富家團村、洞下村、麥園村共5村,總人口約6000。集中了土橋鄉人民政府、土橋鄉中學、土橋鄉中心小學、土橋醫院、土橋集市和高速公路土橋出口等重要機構和生活設施。其中向家莊村、麥園村是小村,有縣道穿過此兩村和土橋村。富家團村是中村,但是村民居住分散沒有自己的中心。洞下村是人口大村,有小水電站,經濟條件相對較好,但是可建設平地少,也無法形成自己的中心。土橋集市平地面積相對較大,有足夠空地建設公共設施。2016年,麥園村、向家莊村并入土橋村。
第二個是冷水鋪—兩戶村生活共同體(社區),包括哨路口村、冷水鋪村、兩戶村村、肖家田村、草鞋坳村共5村,總人口約6000。這個共同體中,經濟中心在冷水鋪村,冷水鋪集市逢農歷一、六趕場,同時冷水鋪還有鐵路貨運站,又處在320國道之上,交通便利。共同體的文化教育中心在兩戶村村,兩戶村小學是希望工程援建小學,目前已經建設成為冷水鋪村、兩戶村村、肖家田村、草鞋坳村4村聯校。其余3村均為小村。2016年,最偏遠的草鞋坳村、肖家田村合并為草肖新村。
第三個是分水坳—巖田沖生活共同體(社區),包括分水坳村和巖田沖村,總人口約4000人。這個小單元中沒有定期趕場的集市。但是分水坳村有湘黔鐵路巖田鋪火車站,在火車站周圍也形成了一些商鋪。原岔溪村是土橋鄉一個獨立的非中心村,它位置偏遠,地處該鄉最北部的潕水河南岸。從農村生活圈上來講,它更屬于北岸的“木葉溪生活共同體”。村民有很多是渡河到木葉溪集市趕集。只是由于潕水河的隔離,岔溪村目前在行政上歸屬于土橋鄉管轄。2016年該村并入鄉內距離最近的分水坳村。
由此推之,芷江縣除縣城外,廣大農村地區大體是4000~10000人組成一個“農村小型生活共同體”,范圍覆蓋目前的2~10村不等。芷江縣城則可以視為一個規模更大的“生活共同體”,一個功能更加齊全,發育更加完善人口聚集5萬人的“生活共同體”。據此推斷,芷江縣農村地區,應該可以分成有40個左右這樣的生活共同體(社區)。
三、營造新的“村民綜合活動中心”和推進農村社區治理的專業化
2016年芷江全面完成建制村合并工作,由原來的299個建制村合并調整為202個建制村,減幅32.4%。筆者認為,行政村合并的空間仍有,因為仍沒有超越生活共同體的范圍。在未合并之前,縣政府行政時,應當以生活共同體(社區),而不是目前的村為單位來行政。也就是將村的社會行政功能剝離,同時實施兩項配套措施,即營造新的“村民綜合活動中心”和推進農村社會服務的專業化。
以農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政策為例。目前是以村為單位,對農村貧民進行救助。我們認為為了給貧困居民提供的社會福利更專業,應當以生活共同體(社區)為單位進行,聘請專人(農村低保專干)負責全社區的貧民登記和救助工作,并能為貧困居民提供救濟以外的社會輔導。農村低保專干直接向縣民政局農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管理部門負責,并作為該部門的正式員工。
擔心這樣做是否會增加人員開支的擔心是多余的。因為在鄉鎮廢除以后,每個鄉鎮有足夠多的人手轉移到為老百姓提供更具體的社會服務中來。即使這些工作人員此前沒有學習過“社會工作”和“社會福利”的知識,也可以通過培訓實現人力資源轉移。又或者,可以逐步招聘受過專業訓練的大學生。
同樣的,各村的婦女工作,也可以由縣婦聯派駐生活共同體(社區)的代表統一負責。
農村低保專干、婦女工作專干等,都作為縣政府職能部門在該社區的派出人員。縣政府應當為每個生活共同體(社區)建造一個“村民綜合活動中心”,每個專干的固定辦公點即在該綜合活動中心內。以前述土橋鄉為例,土橋生活共同體(社區)的村民綜合活動中心,就可以由現在的未來廢除的鄉人民政府所在地的房子改造而成。不但不會增加額外的行政成本,還可以大大改善政府的親民形象。而其他非鄉鎮政府所在地的生活共同體(社區)的村民綜合活動中心,則可以1995年前小鄉制時代的鄉政府駐地,或其他公共設施,或租賃民房所成。
農村地區情況復雜,鄉、村行政區劃的調整又涉及農民切身利益。所以在這一層面的行政區劃調整,必須結合民生政策共同推行。而營造新的“村民綜合活動中心”和推進農村社會服務的專業化,無疑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大有裨益。
參考文獻
[1]曹啟挺.湖南省社會工作機構存在的主要問題和發展建議[J].長江叢刊,2016(03).
[2]曹啟挺.涼山彝族社區公益慈善行動項目分析[J].現代營銷,2014(06).
[3]曹啟挺.市制和社區比較研究[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7.
作者簡介:曹啟挺(1978.06—),男,漢族,浙江岱山人,碩士,講師,研究方向:社區工作和社區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