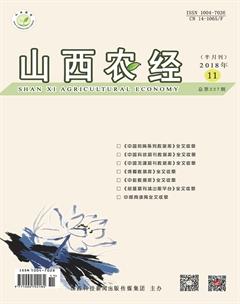遞延所得稅資產對盈余管理的影響研究
高喜蘭
摘 要:通過闡述盈余管理的內涵及動機,對盈余管理和遞延所得資產計量確認之間的關系進行必要的分析。進一步地,以T公司為實證研究對象,考查其2015和2015年度的部分財務報表,詳細論證了T公司利用從可抵扣虧損中進行遞延所得稅資產計提以調節利潤的手段來完成盈余管理的過程。
關鍵詞:盈余管理;遞延所得稅資產;遞延所得稅負債
文章編號:1004-7026(2018)11-0090-03 中國圖書分類號:F275 文獻標志碼:A
1 盈余管理的內涵和動機
1.1 盈余管理的內涵
盡管,國內外學者對于盈余管理的研究已有較長的時間,但因為考慮問題的視角和問題研究的本身目的性差異,尚未對盈余管理的認識形成普遍的通說觀點。我國學者對于盈余管理的關注始于上世紀90年代,在歷經三十多年的研究中,我國學者在盈余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通過對國內有代表性學者觀點的梳理,筆者將盈余管理的定義總結為三類:
第一種觀點是基于經濟收益觀的盈余管理,持有這類觀點的學者認為,本質上,盈余管理并不能改變企業的實際經營活動和運行效率,只是對特定會計信息和數據的適當性調整。所以,他們對盈余管理做出這樣的定義,在既定會計準則的約束之下,企業管理者為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廣義上的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僅僅局限于管理者的薪酬設計和企業利潤核算),進行的一種特定的會計工具選擇。
第二種觀點是基于信息觀的盈余管理,持這類觀點的學者認為,出于個人利益的實現,或者說是為了某種契約所要求的目標實現,在財務報告等公開數據的編制中,非法進行真實數據的美化和粉飾,誤導投資者以使得他們進行會計信息的錯誤判斷。
第三種觀點是基于制度觀的盈余管理,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企業管理者在會計準則的框架之下,按照合規性和合法性的要求,最大限度的利用現有會計準則的不足和漏洞,靈活變動某些特定的會計準則,利用會計手段進行會計數據的合法性操作,達到既定的事先設定目標。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三種觀點不論是消極的,還是積極的,更加側重于盈余管理的目的性討論,制度觀之下的盈余管理設定前提更加要求嚴格,但信息觀之下的盈余管理則是從信息不對稱的視角進行非法操作的討論。所以,筆者認為,簡而言之,從客觀實際的角度出發,盈余管理就是企業管理者利用各種操作手段以達到操縱會計信息的目的。
1.2 從盈余管理的動機方面考慮,國內外重點從資本市場動機、契約動機、政治成本和避稅動機等方面進行了考查
第一,資本市場的動機有多個方面,首先,通過盈余管理示以投資者前景看好的信息以引導投資者進行市場買入操作,這樣一來,就能通過股票市場價格的提高來提升融資額度;其次,為了IPO進行前期的企業優化經營,通過財務報告中會計信息的操作達到順利上市的目的;再次,很多已經戴上ST帽子的上市公司,為了防止其退市的風險進行必要的盈余管理以優化利潤結構;最后,在特定相關者利益的驅使之下,調整盈余數據以迎合分析師或管理部門等相關利益者的要求。
第二,契約動機分為報酬型契約動機和債務型契約動機。前者是指,企業管理者為了迎合績效考核目標以便于確保自身的預期報酬目標實現而進行會計信息調節的動機,而后者是指,企業管理者為了達到債權人既約的盈余數據,避免債務人行使基于自身利益的保護性條款權力而對進行財務數據調節的動機。
第三,避稅動機。對于很多大型企業而言,其所得稅是一項巨大的現金支出一般來講,應征稅負是根據企業的利潤進行的,所以,從會計核算出發,從會計利潤入手,是容易進行所得稅調節的手段之一。很多企業,特別是大型的非公有企業,為了減少所得稅的應繳數額支出,通過調節應稅的收入或可以抵扣的成本費用進行避稅,在實務中較為常用的措施之一。
第四,政治成本動機。政治成本動機主要是壟斷性或能源型企業常常關注的問題。當特定的壟斷性企業利潤達到一定水平時,更容易被國家監管部門關注,就會對其進行必要的介入調查,采取必要的措施手段對其進行生產經營性限制,產生負面的影響。因此,很多這類型的企業就會有意進行利潤的沖抵,使得賬面利潤額大幅下降,以免監管部門介入調查。
2 遞延所得稅資產對盈余管理的影響
2.1 遞延所得稅資產對盈余調節產生影響的路徑
一般而言,在一個會計年度結束之后進行數據的賬面核算時,在科目確認核算上,對于遞延所得稅資產的確認和計量也不是例外,同樣需要進行相應的費額確認和計量,不考慮未來預期僅基于當期的會計核算,會計分錄表示如下:
借:遞延所得稅資產
貸:所得稅費用
從借貸關系可以看出,計提的遞延所得稅能夠對所得稅費用進行遞減,而凈利潤為利潤總額與所得稅費用之間的差額。所以,計提的遞延所得稅越多,賬面體現的所得稅費用就會越少,從而,凈利潤數值因為所得稅費用的減低就會變大,能夠對盈余起到適當的調整效果。
2.2 遞延所得稅資產對盈余管理的影響依據
在我國最新修訂的2017年企業所得稅法第二章應納稅額中第十八條做出這樣規定,“企業納稅年度發生的虧損,準予向以后年度結轉,用以后年度的所得彌補,但結轉年限最長不得超過五年。”本質上來看,向后續年度的進行稅額結轉,產生了抵減未來期間的應稅所得額以及應交企業所得稅的效果,同時,相應抵減所得稅費用,起到調整利潤的作用。并且,依據我國最新會計準則和稅法的有關條款,在計量和確認遞延所得稅時,因為遞延所得稅資產和遞延所得稅負債對于盈余調節的影響作用相互反方向作用,應當分別進行遞延所得稅資產和遞延所得稅負債的計量和確認。
3 實證分析
T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主營服裝家電餐飲娛樂等多元化經營的商貿服務公司。以T公司2015和2016兩個年度的財務報告為研究樣本進行分析,筆者發現,相對于本地區同行業經營規模相近的其他公司而言,T公司的所得稅繳納金額較低,是利用所得稅資產進行盈余管理的成功范例。T公司2015年度和2016年度的所得稅數據表比較如表3-1所示:
從上表3-1可以看出,2015年度,T公司在遞延所得稅的計量確認為2.18億元,而遞延所得稅負債為0.04億元,相對于遞延所得稅資產而言,約為其1.835%,所占比例微乎其微;2016年度,T公司在遞延所得稅的計量確認為1.71億元,而遞延所得稅負債為0.07億元,盡管,遞延所得稅資產相對于上一年度有所下降,而遞延所得稅負債相對于上一年度有所上升,但遞延所得稅負債約為遞延所得稅資產的3.867%,比例所占甚小。在相鄰的兩個年度中,遞延所得稅資產遠遠都低于遞延所得稅負債。為了問題研究的必要性,進一步地,挖掘遞延所得稅資產的產生原因,如表3-2所示:
從表3-2可以看出,T公司在2016年度期初的遞延所得稅資產最主要的來源是可抵扣的虧損,總共2.18億元的遞延所得稅資產,就有1.87億元來源于可抵扣的虧損,占到了總量的85.78%之多。即使到了2016年度期末,T公司的遞延所得稅資產計提有所下降,但在1.71億元中,仍有1.24億元來源于可抵扣虧損,可抵扣虧損的占比約為72.51%。簡言之,T公司采取將虧損認定為可抵扣虧損的計提方法,將其中的部分虧損計提為遞延所得稅資產。這樣一來,就使得所得稅稅費減少,相應地,賬面凈利潤體現為增加,達到了盈余調節的目的。
如果進一步的進行問題的討論,為什么T公司只將可抵扣虧損中其中的一小部分計提為遞延所得稅資產,沒有將大部分可抵扣虧損進行計提而進一步的推高賬面體現的凈利潤。筆者認為,可能存在兩方面的原因:第一,T公司按照高層管理者的既定預期目標,已經實現了本年度的利潤預期,預留可抵扣虧損為未來的年度調整做準備;第二,財務管理人員出于審計謹慎的原則考慮問題,可能對于未來的虧損回轉前景預期并不是十分的看好,為未來年度的利潤增長預留一定的空間。
參考文獻:
[1]許太誼.企業會計準則及相關法規應用指南2018[M].中國市場出版社,2018.01.
[2]吳秋生,郭檬楠,張小芳.實盈余管理與應計盈余管理關系研究——基于現階段我國企業所處環境的互動效應視角[J].南京審計大學學報,2018(01):87-96.
[3]許文靜,王君彩.應計盈余管理動機、方向與公司未來業績——來自滬市A股經驗證據[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8(01):68-76.
[4]吳媛媛.交叉上市對企業盈余質量的影響——基于應計盈余管理和真實盈余管理的研究[J].財會月刊,2018(02):32-38.
[5]楊攀,劉宇寧.遞延所得稅資產與盈余管理——基于*ST鞍鋼扭虧的案例分析[J]財會月刊,2014(02):9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