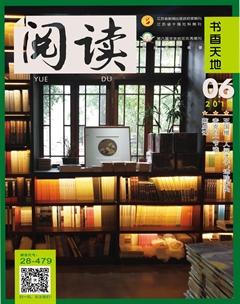一個90后歷史老師的自我修養
楊夢蝶
2015年夏天,1994年出生的魏祺成了自己的母校——北京中醫學院附屬中學高中部的歷史老師,這位全校最年輕的老師,同時還擔任了高一(2)班的班主任。
第一天上課,魏祺指了指前排學生身上的校服:“我是老師,也是你們學長,你們現在穿在身上覺得難看的校服也是6年前我穿在身上覺得難看的衣服!所以,請大家千萬不要見外。”學生們笑成了一團,覺得這個老師“挺對胃口”。
“喂,你再這樣上課我給你開手機直播!”
9月軍訓,魏祺和高一(2)班的學生第一次見面。留著鍋蓋頭發型、戴著一副圓框眼鏡的魏祺看著斯文安靜。他在走道里幫學生看校服,身上穿一件、手里拿兩件。大號的校服,還算是熨帖。
自己班的學生從門口走過,勾肩搭背,隨聲問一句:“學長,你知道食堂怎么去嗎?”
魏祺篤定地糾正了一句:“我可能是你們的班主任。”
“啊?怎么會?”幾個學生狐疑地看看角落里這個高瘦的大男孩。
突破這幫學生想象的,除了人本身以外,還有他的課堂。
開頭幾分鐘,魏祺要和學生們討論一番與歷史書格格不入的“國際上的事兒”。英國脫歐的后一天,好幾個學生拿來了厚厚的一沓資料湊到講臺前要發言。一個女生告訴小魏老師:“八月,我要趁假期去看看現在的英國!”放了暑假,魏祺又接到了這個女生家長的電話:“孩子快要出發了!”
小魏老師斷言,在他這個教室里的青年,面對脫歐,甚至比英國本土青年還要熱忱敏感。
每一節歷史課上,任何學生可以隨時打斷。只要是和課本相關的歷史事件和人物,不用避諱什么教師權威,所有人都依據手邊找來的史料堅持爭論下去,雙頰漲得通紅、起身拍桌子、把筆直接往桌面上一甩。只要是為了爭鳴學術,魏祺覺得“怎么表達都是正常”。
小魏老師說:“課上,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有什么絕對權威。現在學生和老師獲取信息的渠道幾乎是平等的,你憑什么搞知識壟斷?”
講起高中課堂應該有的“規矩”,這個21歲的大男孩兒搖搖頭說:“我這樣的課堂,可能就是個非主流。那我也得這么做,我讀過很多歷史書,太知道那些御人之術了,但是我不那樣對待自己的學生!”
一次,一個家長支支吾吾地來查自家孩子是否有“早戀傾向”。家長含蓄地說:“我就怕這個孩子做什么過火的事情。”
小魏老師一板一眼做起了家長的工作:“您覺得在他們這代人中,在高中階段對一個女孩兒產生一種情愫,能算是早戀嗎?”家長被問住了。
青春期的女生愛美,有時在鏡子前一打扮就是半個小時。家長來找小魏老師訴苦,魏祺卻說:“注意自己的形象管理,這沒有什么不好呀!”
不過有時候,這個嘻嘻哈哈、處處“偏袒”學生的的小魏老師卻也要用流行的辦法“做做規矩”。
下午的課堂,魏祺見學生們像是打蔫兒的花草,他突然在教室提高嗓門兒喊了一句:“你們要是再不認真,就開手機給你們錄直播,實時傳給你們家長看。”學生們樂得前仆后仰,急忙坐得挺拔了起來,嘖嘖道:“這就是我們這個90后老師最惡毒的地方!”
“摸一摸歷史,別老想著做完美主義者!”
“嘿,這兒講到軍機處了,你們還記得我帶你們看的軍機處嗎?”
“特別味兒,一排小矮房,很破……它也是清朝最高國家機關。”學生們特別踴躍地回憶著。
“所以,你們看,不是所有朝廷要事,都是要放到臺面上來說的。”
這組課堂上的對話,出自魏祺帶著班上同學參觀過故宮的軍機處之后。學生們記住了那一排氣味嗆人、低低矮矮的房子。
“摸一摸歷史”,這是魏祺一直教學生的理念,他有些驚喜地說:“你們看,學生說起軍機處,首先想到的終究是自己直觀感受到的那些東西,味兒!”魏祺計劃著,要在高中三年里,帶學生們去北京城里盡可能多的博物館轉轉。魏祺覺得,只有一個人聽的、看的、經歷的多了,才能不變成一個可怕的“完美主義者”。
魏祺評價自己的中學時代,直言:“我當時就是這樣一個完美主義者呀,思緒萬千,愛記日記針砭時事,堅信這個世界應該變得完美無缺。”魏祺突然誠懇地搖搖頭,補充了一句:“如果一味做一個完美主義者,就不會懂得同情別人,只會一味縱容和寬待自己。”
這種完美主義的習慣,終于在魏祺高中的一次歷史課上的研究性學習中有點松動了。
那一次,魏祺和他的同學研究的是武則天,魏祺發現:在唐朝這個大鳴大放的時代備受推崇的武后,到了內斂、講究理學章法和人倫綱常的宋朝遭到貶斥,而到了近代女權運動興起之后,武后甚至還加上了“則天”二字,以表征女性亦可以能力脫俗。
歷史上唯一的一個女皇帝,讓他學著在歷史的語境中“同情之理解”的力量。“學會了包容歷史的不完美,也就能夠逐漸學會包容社會的不完美了。”
現在,魏祺會把學生們對于完美主義的期待,放到自己的身上進行疏導。
他指著自己有點歪歪扭扭的板書告訴學生:“我寫的板書不好看,請盡情批判,但是我希望你們的批判精神最好盡可能只集中向我開炮,因為你們還沒進入社會,所以你們應該先學著去觀察社會。”
“留步,我想和您聊會兒中國!”
2017年的6月19日,魏祺參加了一個德高望重的老朋友——前駐法大使、資深外交家吳建民的追思會。坐在86歲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資中筠的后面,他在朋友圈寫下一句話:“一會兒我也有一個簡短的發言。”
魏祺第一回和吳大使聊天的時候,還是個高中生。一次講座的末尾,魏祺對吳大使說:“留步,我想和您聊會兒中國!”因為吳大使的一句“給小朋友一個機會!”魏祺獲得了提問權:“對中日關系未來的走向,您的預判是什么樣子的?”那次,魏祺覺得,他面前的就是一個穿著灰色西服的老頭兒。
吳大使被這個思緒昂揚的小孩兒吸引了,反過來追著魏祺,了解他作為一個青年人對諸多問題的看法。兩個人常常像是遛彎兒一樣找地方走走、喝喝茶。
2015年,魏祺做了老師,吳大使的問題重心漸漸從魏祺轉移到了他的學生身上:“你的學生怎么看待中國現在的外交?你教歷史的時候又是怎么跟他們講述的呢?”日子久了,魏祺明白了吳大使對于年輕人看待國家問題的建議:“多聽多看,準確認知世界,不要錯判了發展的機遇。”
這兩年里,魏祺常收到吳大使親手寄來的書,扉頁上端正寫著:“請魏老師指正!”最近收到的一本,是吳建民大使編寫的《吳建明談外交》。吳大使告訴魏祺:“你看一看,從歷史的角度能不能有什么修改的地方?”
“我要去再讀一遍歷史系研究生了”
教師辦公室不大,連魏祺一共坐了四個老師。
除了批改作業和備課,魏祺大部分時間都端正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看歷史書。時而興起就站著擺弄當天的報紙,把報紙上的新聞一塊塊剪下來,貼在一個白本子上。“故宮大修的新聞我剪過,北大歷史老師發的文章,也要剪,有時候,一道歷史考題的解析,覺得好也捋下來。”
剪來剪去的,聽著像是個老派人,就像是他的微信名字一樣,叫做“魏某某”。
看著埋頭讀書剪報的小魏,辦公室里的其他老師經過,都會說一句:“小孩兒,多讀點書挺好的。”
“多讀點書挺好的。”這句話,其實魏祺好多的大學老師都和他說過。
魏祺2017年9月份又入學了,在職碩士研究生,就讀人大歷史系,看著像沒有什么必要的“炒冷飯”。魏祺只灑脫解釋了一句:“其實我就想找個正當理由聽那些課,我要那個文憑來做什么?”
除了人大,北大歷史系的課堂也是他常常“挑著去”的。這個身高有些出眾的年輕人經常坐在最后幾排,盡量不引起別人的注意力,卻終究會在散場時分,因為一兩個出眾的提問,讓北大的老師把他記得比自己的學生還要牢。就這樣,他認識了北大歷史系的鄧小南、閻步克。
按照魏祺導師們的建議,這個頗有天賦的年輕人應該繼續深造并且進入高校成為研究者。然而在做大學老師還是高中老師這道選擇題中,魏祺還是選擇了后者。
魏祺說,他覺得只有在基礎教育的時候,老師才能和學生真正因為考試捆綁在一起。作為一個老師,他就是想把自己和學生“綁”在一起。
魏祺曾經想著給中學老師下一個定義,他最后的初步結論就是:中學老師應該是知識人,但是算不上是知識分子,因為在基礎教育階段對于學生的習慣培養,讓老師很難具有自由的批判意識和流動精神。
現在,每個月要花掉3000元收入買書的魏祺覺得:“無論如何,做老師的都應該是個讀書人。”書再買下去,他的房間就要沒地方落腳了,魏祺現在開始向客廳進軍。
“學生老師傻傻分不清!”魏祺得意地發來一張他保存的經典照片:一群20來歲的孩子滿滿地擠在畫面里,魏祺穿著一條連帽衫,拼命在兩個學生中間擠出了一個腦袋。這個也偶爾逛夜店、經常看足球的歷史老師強調自己“畢竟還是時代中人”。他不止一次告誡過自己的學生:“畢業出了這個校門,就趕緊把我是你們老師這個事兒忘了。把學了的條目也都忘了!只留下思考這個世界的方法。”
為什么?
魏祺的回答得很歡脫:“難得有了第一屆還沒啥代溝的,以后可不得當哥們兒好好處著?”
(摘自“搜狐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