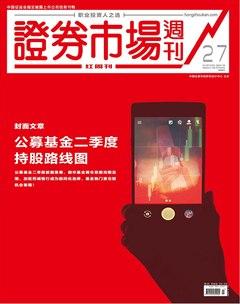銀行業出現歷史性錯誤定價
董寶珍
我們綜合統計了A股所有上市公司過去幾年的經營數據,并把它作為我國經濟的整體進行研究,然后得出結論:我國的銀行業出現了歷史性錯誤定價和誤判,它是人類金融發展史上的最有個性的錯誤定價和投資機會。銀行股持續6年的低估,且達到50%以上的低估幅度,令人驚嘆。2013年在茅臺跌到一百多塊錢的時候,筆者在否極泰年報中發出吶喊:“這是千年不遇的機會,錢多人傻速來。”今天,筆者又找到了那一年的感覺。
因為長期跟蹤銀行業發展情況,筆者研究認為,銀行業的未來有一半是銀行業自身的經營規律決定的。銀行受宏觀經濟影響的主要是資產質量。在這個情況下,分析銀行一方面要立足于它自身內在的凈息差、資產質量、放貸規模,另一方面也要研究宏觀經濟。在《否極泰2018年半年報》中,筆者將思考主要集中在銀行自身內部的變量上,本文將對銀行業依托的宏觀經濟進行分析。
筆者做了一些關于我國整體經濟的分析,這些分析中引用了大量的數據,基于數據按照常識性邏輯推出了結論:“我國經濟基本上已經走出了調整進入了新周期,只不過是這種新周期比較緩慢。由于銀行業的基礎經營背景進入好的變化趨勢中,這樣就使得我國銀行業出現大的衰退的可能性被抑制和消除了。”這些分析發布之后,有一些業內人士認為,真正的問題并不是分析的邏輯過程和結果,真正的問題是數據的可靠性。
鑒于此,在這一次研究分析銀行業的過程中,筆者決定換一種思路。因為我國上市公司無論規模和質量基本上代表了我國經濟的主干和主流,又因為上市公司的數據都是經過會計師、審計師專門審計和投資人、甚至他的同行的監督或監視——不能想象幾千家公司都一致性財務造假,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上市公司數據的真實性。在這兩大前提下,我們作出一個假設,就是所有上市公司經營總和代表我國經濟基本面。
經濟進入新周期 銀行業觸底回暖
筆者把所有上市公司歷年收入數據、利潤數據進行加總統計來代表我國整體經濟,并且筆者把上市公司分成三類統計:一類是全部上市公司總的數據;第二類是非金融企業加總數據,可把它理解為實體經濟;第三類是金融的數據,金融數據又包括金融總的數據和銀行業的數據。統計后,得到了一些獨特的結果。(見數據75頁)
全部上市公司整體經營數據和GDP數據有差異。過去十年我國GDP的波動幅度很小,比較穩定,但我國所有上市公司的營收和利潤波動非常大。
全部上市公司整體經營數據有這樣幾個特點:
第一、實體經濟——上市公司的經營數據一波三折。
2008年金融危機后,我國的上市公司經營數據發生了深V走勢:先急速下跌,后經過了4萬億的刺激,到2010年快速到達一個高點;而在2010年高點之后又持續下滑到2012年,出現了一個階段性低點;2012年出現小幅反彈到2013年,再之后反彈結束開始衰退到2015年;2015年創造了歷史上的最低數據;2016年營收數據重新開始上升。上市公司一波三折的數據和GDP的穩定存在巨大差異(因此筆者越發覺得用全部上市公司的營收和凈利潤數據應該更客觀一些)。
實體經濟波動過程至少有三個低點,兩個半高點。2015年是一個重要的時點,實體經濟的營收和凈利潤增速在2015年創下了歷史低點,其中凈利潤增長率出現了18%的負增長,幾乎接近2008年金融危機時的水平。過去十年,我國實體經濟很困難,2010年非銀行業的凈利潤達到階段性高點8619億元,從此開始波動下滑到2015年,到2016年恢復上升到10657億元,上漲的規模和速度都有限,而且有些乏力。
第二、金融業企業以及銀行業的營收和凈利潤增速單邊下跌。
金融以及銀行業凈利潤增速從2010年見頂后走出穩步單邊下跌。從2010年到2016年,金融和銀行的凈利潤增長率持續下跌由正轉負。2016年是金融業和銀行業凈利潤增速的歷史低點,也是一個轉折點,此后金融業和銀行業的凈利潤增速開始回升。
第三、金融銀行企業周期滯后于實體經濟一年左右。
金融、銀行波動周期都是晚于實體經濟的。在實體經濟于2015年創下歷史最大負增長,于2016年快速大幅明顯上升的時候,銀行業金融業的凈利潤實現了首次負增長,晚于實體經濟一年。2017年,實體經濟維持高位向好,金融業才開始緩慢上升。這個現象在多個指標上都出現了。這是銀行和實體經濟的本質關系決定的。金融銀行業周期落后實體經濟是普遍經濟規律決定,金融銀行業是后周期產業。
第四、在我國所有上市公司整體的營收和利潤數據中,非金融業的數據一波三折,而金融業營業收入和利潤的增速單邊下跌,為什么出現了一波三折和單邊下跌的差異?筆者對此進行思考后得出這樣一個觀點。非金融業的金融數據反映了我國整體經濟的現象,在我國經濟的現象層面體現出一波三折波動向下的特點。
第五、我們要特別注意2015年這個時間點,在2015年前和后,我國經濟有明顯的差異,這一年可能是以十年為一個經濟周期的戰略拐點。因為在這一年,非金融業、金融業次第好轉,之后,所有上市公司整體經營數據,無論是營收還是利潤、利潤率都出現了好轉。2015年之后,各項指標出現了較長周期的持續好轉。從2008年開始到2015年,上市公司整體經營數據表明我國經濟陷入困難期;從2016年開始,上市公司整體經營數據表明我國經濟已經開始了新周期,只不過人們還不敢相信這是新周期。
經濟新老轉換不可逆 銀行正全面轉向新經濟
這里筆者向大家介紹一下自己的研究公司和問題的研究模式,一共分四步:第一步,統計所研究對象的基礎數據。第二步,對基礎數據中所包含的特征進行觀察和總結,提煉出這些基礎數據中表現出來的變化特點。第三步,分析思考為什么在數據上會有某些特定的特征?尋找背后的邏輯原理。第四步,用所找到的決定數據特征的邏輯原理預判未來走向。
我們已經完成了收集數據,觀察數據的特征,現在進入第三階段,研究一下這個數據特征產生的深層原因。
實體經濟一波三折的深層次原因?
從2008年金融危機到2010年,在4萬億的強刺激作用下,各項指標數據立即V型反轉。2010年到2012年,強刺激的效應結束了,而且沒有安排新的刺激,于是由強刺激所推動起來的經濟高增長不能維持,公司營收數據開始持續下滑,行業利潤開始出現負增長。2012年當所有的數據都出現困難表現的時候,我國政府進行了微刺激,微刺激推動了2012年到2013年的一個小幅反彈。這種小幅反彈仍是刺激決定的,只不過這次刺激不是大水漫灌,刺激的程度弱,所以反彈的力度也小、持續時間也短,到2013年數據又見頂,并開始回落。2015年,實體經濟的凈利潤增長率出現了18%的負增長,各項指標都很困難。
2015年后,去產能、供給側改革等新政策出現,并很快見效,使得2016年、2017年實體經濟的凈利潤增長速度達到了27%左右,接近30%。這次復蘇持續的時間比較長,到目前已經兩年半了,幅度也很大,而且經濟政策沒有搞刺激。去產能、供給側改革和此前的刺激有質的差別,強刺激、微刺激是在不改變結構的情況下放水行為。實際上是“打激素”,因此總是不能治本。
在2016年之后我國的實體經濟效益就很明顯地開始上升,這個持續的復蘇的時間和幅度在我國過去十年是沒有的。
去杠桿完成最后的去產能,加杠桿創造新產能
回到我國經濟。筆者匯總2007年以來的幾乎所有經濟數據、經濟政策分析發現,我國經濟政策和實體經濟狀態,大體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15年之前的刺激需求階段,有了刺激經濟馬上就像打了雞血往上沖,沒刺激過一年半載經濟就掉下來。第二階段是,2015年后經濟轉向了供給側改革,供給側改革一方面強調去產能,另一方面強調鼓勵新業態、新模式、新經營主體。現在看來,2015年后的經濟政策是對路的,實體經濟已經有了自然復蘇,迎來了2016年、2017年實體經濟的較好成長。
過去十年,我國經濟政策經歷了一個試錯的過程,一開始想通過傳統的刺激需求的方法推動經濟發展,后來發現根本不是需求不足,而是舊產能過剩,必須去除舊產能建設新的產能,創造新的需求。
目前,我國政府力度空前地對某些領域進行定向去杠桿。去杠桿以來的客觀數據反映社會總融資增量大幅減少,與此同時,銀行信貸的增量持續創新高。去杠桿讓委托貸款,信托貸款以及小貸公司P2P紛紛受到抑制,從而使得那些依賴于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小貸公司P2P等非銀行渠道融資的企業,立即陷入了資金鏈緊張甚至斷裂,也曝出了一些企業出危機的情況。為什么有很多企業依賴非銀行機構的貸款?為什么監管層堅決讓這些依賴非銀行貸款的企業死掉?答案是,早在幾年前我國的產業政策就明文規定,高耗能、高污染、房地產以及落后的產能不能從銀行獲得貸款。
但是這些高耗能、高排放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不想退出市場,所以從非銀行金融渠道獲得貸款,當時因為經濟不好,監管層對這種情況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去杠桿是向那些落后產能定向收縮金融資源,以金融手段逼迫他們退出。這是去杠桿的一個本質意圖,去杠桿和去產能是一脈相承的。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我國去產能政策已經成功了,煤炭鋼鐵的價格回升,相關企業盈利好轉,與去產能一脈相承的去杠桿,不可能危害我國宏觀整體經濟,它只是快速地以金融手段把那些該退出的企業清理掉,從本質上去產能、去杠桿都是為了經濟進一步健康向前發展。很多人對為什么這一次去杠桿政策意志如此堅決,并不在意市場的不適應,也不回應有人對去杠桿兒的批判。不幸的是,我國資本市場和經濟界很多權威卻不能對此正確理解,誤判了形勢。
銀監會的政策是支持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融資向他們寬松的放貸款,這是為什么?這是在去產能的同時創產能。去掉落后產能只是第一步,還要創造出新的產能,只去產能而不創造新產能也不行。去產能和創產能是一體兩面內在關聯的,把落后的產能去掉,把新產能培養造就出來,這時經濟才能持續穩定健康。去產能是基礎,創產能是關鍵,創造出新的產能經濟才有新動力、新活力。當前銀保監會加大對民營和小微企業貸款的政策,是鼓勵創產能。四大國有銀行,沒有人搞出支付寶,沒有人搞出微信支付。阿里巴巴和騰訊公司以它們內在的創新活力,創新出了移動支付,移動支付促進了實體經濟,也創造了企業發展的動力。這就是銀監會加大對民營和小微企業信貸投放的深層次原因,這個不是放水,這個是鼓勵創新,其深層意思是鼓勵創產能推動經濟升級。推動經濟結構轉型,經濟升級形成新產能的主力是市場化程度高的民營企業和小微創新企業。這些企業如果給予足夠的金融資源和其他資源的支持,那么它就會創造出很多根本沒有的新供給,從而拉動新的需求。比如說智能手機在沒有被發明創造出來前,消費者不會產生這個需求,所以只有供給端的創新才能創造需求,那么創新的主體顯然不可能是國有大型企業,創新推動我國進步的是民營企業和小企業,新產能的創造就落到了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上,于是你就得加大對他的支持,這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業升級的思想,不是什么經濟刺激。
定向緊縮去杠桿是去產能,對民營企業和小企業的貸款寬松是創產能。但是市場理解為去杠桿引起的是全面危機,這是錯誤的甚至是可笑的。
未來我國經濟的命運決定于產業結構是否能夠有效的升級,決定于拋棄落后的產能,建設出真正有市場、有需求的新產能。目前我國正采用金融去杠桿的手段推動最后的去產能,同時通過金融和其他一系列綜合手段推動扶持新的產能提升和產能出現。2016年之后的復蘇正是這樣政策成功的反應!
銀行業被錯誤定價 銀行股嚴重低估預示大機會
總而言之,有以下結論。
第一、以上市公司的營收和凈利潤作為統計數據,數據反映出過去十年我國實體經濟其實并不是特別強勁。與單邊上升的GDP數據相比較,我國上市企業的盈利其實沒有那么大的增長。
第二、我國經濟的拐點發生在2015年,那一年的數據全面負增長,監管層在困境下啟動了供給側和去產能改革,這個改革已經見效,經濟持續復蘇且已經進入新周期。
第三、資本市場對新周期視而不見,卻沉溺于表面現象中,對經濟形勢和未來方向產生錯誤判斷。
去杠桿是一個以金融手段淘汰落后產能的政策,它跟去產能是一脈相承的,其最終的政策效果是讓我國經濟更健康,絕對不是像市場人士所分析的會引發一場全面金融危機。這種悲觀論調已經到了荒謬不堪的程度。筆者還記得,2005年股權分置改革時流行一種觀點,即一旦大小非獲得流通權,就會因為自身只有幾分錢的成本而進行瘋狂減持,這種認識促使上證指數被一路打到了900多點。事實證明,這種觀點是謬誤,產業資本不僅沒減倉,甚至在幾次估值水平很低的時候大規模回購。
今天,我國政府在經濟已經相對復蘇情況下推動去杠桿,結果所有人都說這是在玩火,會引發全面危機,這種觀點是現在股市下跌、銀行股下跌的關鍵因素。歷史會再次證明這種沒有邏輯的議論是錯的,這種議論是因恐懼而產生的。這也導致背離情況的發生,基本面復蘇向上,資本市場背離恐慌向下,這樣的背離可能導致一個歷史性的投資機會的出現。
筆者認為,大的投資機會都是市場錯誤造就的,或者是用悲觀情緒造就的,就像2013年的茅臺和白酒產業。尋找投資機會其實在相當程度上是尋找市場錯誤尋找悲觀情緒。客觀的基本面的增長是財富的來源,但市場情緒和認知的錯誤會導致價值低估和財富轉移。
我國的銀行業出現的是歷史性錯誤定價和誤判,它是人類金融發展史上的最有個性的錯誤定價和投資機會。銀行股持續6年的低估,且達到50%以上的低估幅度,令人驚嘆。2013年在茅臺跌到一百多塊錢的時候,筆者在否極泰年報中發出吶喊:“這是千年不遇的機會,錢多人傻速來。”今天,筆者又找到了那一年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