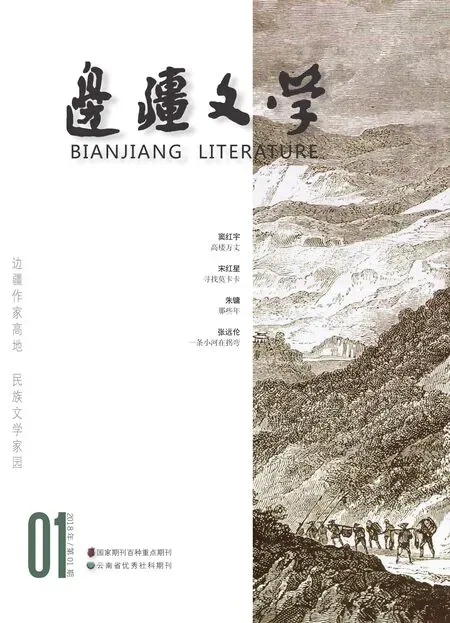那些年
泥土的光
仿佛一出惡作劇,勞力虛空,莊稼偏偏熟得如此誘人。許多年都要盼著的好收成,許多年都在土地上揮汗如雨,還許多年想著要是土地寬一點,再寬一點,包谷洋芋就可以多種下一排。許多年,從沒有感覺到最令人動情的秋收季節(jié),莊稼地卻像一張死床,枯黃的草葉,像莊稼壽終正寢的壽衣。
對不起,故鄉(xiāng),恕我不敬。在這個所有植物都把豐足的頭垂向大地的季節(jié),大地上到處的果實,它所奉獻的崇高,令任何人都感動!可我實在無法贊美!秋收的喜悅?滿倉的糧食?敬祝和感激。我相信,這一切是存在的,所有的勞動力都值得欣慰,甚至興奮。在遼闊的莊稼地上,果實閃閃發(fā)亮。
我以為土地養(yǎng)育所求有度的莊稼人,每個人在豐收的時候除了喜悅那還會有什么?我從來就沒想過這個問題,但是,它真的還有。還有絕望。這真讓人不可理解。而我在這里,只想忠實地記錄一個年邁的生命。她雖然只是個體的生命,但她與中國的鄉(xiāng)土水乳難分。我記下她,或許正是我不能忘記村莊的生活方式,也或許,只是心甘情愿地承認了生命的衰老。更何況,誰又能肯定,我記下的衰老,不是每個人的未來?八十多年了,她在這塊土地上早出晚歸,也曾在無知無覺的年齡,她感到自己的生命和勞力,怎么也用不完。
這個八十多歲的老人,她就坐在我家門口,不住地嘆息:“那時力氣是個怪,今天用了明天在。”是啊,年輕氣盛時,力氣像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井。可是,今天呢,對自己的土地那份熱愛的感情,濃得像血,卻心有余力不足啊!土地養(yǎng)活了先祖,養(yǎng)活了自己,自己卻在土地的滋養(yǎng)下,逐漸衰弱如羊。她與她同時代的人,都一模一樣地只有一種形式的過去,和一模一樣地只有一種形式的現(xiàn)狀,就是再也沒有能力從曾經(jīng)的一貧如洗,再去完成勞作的苦楚和已經(jīng)完成勞作的成果之間的欣喜了。
“地里的莊稼黃啦!黃啦!全都黃完啦!再拿不起來,又要爛在地里了。”說這番話的時候,她和我母親坐在一堆包谷前,正在拿起手里的包谷一個一個地摸著它們。我站在那里,老人摸著摸著就無語了,摸著摸著就雙手顫抖,摸著摸著就淚流滿面。她撩起衣角,擦了一下淚水,和我的母親說,“要是天收了,也沒個盼頭。這么好的收成啊,反倒讓人扯心扯肝,讓人心死!”我的母親,耳已不太好使,只是模糊地聽見她在說話,也就對應說:“是呀是呀,今年包谷比哪年都大個,看著就惹人愛!土地好啊!哪里都埋人。人也好噢,活著地里有莊稼,死了天上也有個位置。”
兩個老人的對話,都在自己說自己聽。她們的交流,都不是用語言,就是坐在一起。因為老人的耳朵也背,她聽不見母親和她在說什么。她只是看見母親的嘴沒動了,她又說:“黃泥巴都捂到嘴了,就看得見點泥巴的顏色,活過今天不知明天,管它了。都秋天了,背時兒子也不回來收,它要爛,就讓它爛吧!沒指望了!”說著,老人就站起身,也不和母親打招呼,弓著腰走了。
我喊她,她聽不見。頭也不回,把手背在身后,一碎步一搓地地向前走。這個情景,我想起了朦朧貧寒的記憶,滿目瘡痍的日子,再到今天一年到頭吃不完的糧食,我的心為之一顫。我無法理解豐收的絕望,在看著老人貓一樣弓起來的背,臉上和手上風雨割據(jù)出來的密密痕跡,我明白了這絕望的憂傷。是的,這黃,這焦黃,在她的生命里,成了難以抗拒的現(xiàn)實,成了她無法承擔的主宰。
多年前,老人的兒子,一個鄉(xiāng)村醫(yī)生,破產(chǎn)后,離開了這塊土地。他的破產(chǎn)是注定的。他不知道,醫(yī)者,仁心。醫(yī)者,仁術(shù)。而他的仁心和仁術(shù),全來自于他自己得了病,上山采藥吃好后,他就做起了草藥醫(yī)生。自己隨心所欲買書學習醫(yī)術(shù),沒人指導,沒人給他建議,他就大膽地自己開了一個診所,連同西醫(yī)一起給人看病。醫(yī)療的地方,本就是一個肉身病痛的避難所。但是,有一次,他在為一病人注射時,針水還沒抽完,病人眼皮已經(jīng)翻白。他立即顫抖著雙手現(xiàn)去書本里尋求答案,答案還沒尋到,病人已經(jīng)僵硬。就這樣,他賠償了一場醫(yī)療事故后,家里沒有了一粒細糧,院子里連一只雞都沒有了。一貧如洗倒還說不上,還有兩袋粗糠和半缸沙井水。多年的經(jīng)營,被一次性洗禮,他一氣之下,帶著妻兒離開了村莊。在我的印象里,我眼前的這個老人,在那些年他掙了點錢,老人也保持她的勤苦節(jié)儉,富貴誘惑不了她。在他沒落后,饑餓寒冷她也能堅守。她早出晚歸在土地里,無償翻挖別人家挖過的洋芋地,目的是尋找埋在土里撿漏的洋芋。在秋收后空曠的田野上,一穗一穗撿拾谷樁里落下的稻谷。為了生存,的確,那時她覺得有使不完的力氣,一天之中,要踏訪很多地方,仿佛腳下的土地,都是她的城池。也就在近幾年,她的兒子,在春耕的時候回來把她經(jīng)營的莊稼地點種上,秋收回來收秋。
現(xiàn)在,秋天來了,葉子肯定要黃,莊稼肯定要熟,萬物的自然規(guī)律,人類只有順應。然而,遇上有豐收,哪里不是一片歡笑?
就我眼前的這個老人,她或許也歡笑,也興奮,卻又在興奮中沉默。她的精疲力竭,面對豐碩的果實,她并不知道她是應該笑還是哭。可是最后,她哭了,老淚縱橫。
或許,這只是我的一閃之念記下的場景。我也希望僅僅是一閃之念,讓她在絕望中透出希望。原諒我的偏執(zhí),可能寫得用力過度,因為我不敢放松分寸。因為,她們這一代老人,寒冷,饑餓,土地猶如生活中的鹽,鍛打一生鐵一樣的寧靜,現(xiàn)實的存在里卻是滿心悲愴。在勞作一生的莊稼活計里,打交道最多的土地,已經(jīng)到了盡頭,再也不能事無巨細地全力以赴。
我不由得想到了老人說的話,“我看見了,泥土的顏色。”是的,人的一生,最后等待的,還是泥土。其實,她們說顏色,我想說成是光。光才讓人看見,活著或者死了,都在泥土里誕生。
關(guān)于泥土,我觀察多次了。它在秋天的季節(jié)里,是發(fā)亮的,光芒閃閃。
豬草
灰灰菜曾經(jīng)在我們的生活中,是一個不值一提的配角。在這里,我之所以突然想記敘下灰灰菜,是它在今天成為了人們最令人動情的野菜。它在飯桌上的存在有些像我們青春的經(jīng)典一樣,雖然不是主要的,卻特別亮眼,有種帶給人想下口的欲望。還讓我動情的,是回到老家煮豬食的煙火,讓我再次想到很久以前拔灰灰菜的場景。
從本質(zhì)上講,灰灰菜屬于一種生于路旁、荒地及田間,為很難除掉的雜草。但它卻可以長到一米多,它的莖直立,粗壯,會有很多枝條斜升或開展。它是野性的,我以為它卻有人性。它一年一年生長,重復又重復。你永遠別想鏟除它,因為它平靜地與大地共處。
我記得在上個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鄉(xiāng)村,莊稼地里到處都長有灰灰菜。那時物質(zhì)匱乏,灰灰菜卻從無人食用,只能成為一種豬草。在我上小學的時候,每天放學,母親都要求我背著小背簍去地里找回一籮豬草。在夏季,那時最多的就是灰灰菜。它又名藜,別名野灰菜、灰蓼頭草、鶴頂草、胭脂菜。在我的故鄉(xiāng)叫它灰椒菜,因為它在熱頭的照射下葉片卷起,像小辣椒。我以為灰椒菜是較科學的命名,它的葉柄與葉片近等長,或為葉片長度的一半,葉片上有白灰,卷起來的樣子更可愛。灰椒菜的叫法才與本質(zhì)親密無間地結(jié)合,有著血肉聯(lián)系的原始名稱,我更喜歡它自己土生土長這樣的俗名。我覺得它帶著活力,只要找到一塊生長的地方,很快就可以拔滿一背籮。那個時候,母親給豬和我都安排了任務。豬的任務是吃完食長肉,我的任務是每天完成一背籮豬草。在當時,灰椒菜無疑成為了我每天任務希望的附言。
既然母親把豬和我聯(lián)系在一起,日子也自然混搭在了一起。豬的日子是在吃食“嘭嘭嘭”的響聲中,我的日子就是標記在一背籮的豬草上。但我一直覺得豬的日子比我好過多了,它只管吃了睡,睡了吃,吃不起睡不起還可以在圈里左哼哼右哼哼轉(zhuǎn)去轉(zhuǎn)來地轉(zhuǎn)了玩,真是吃飽了撐的!它這樣其實很消耗體力,下頓吃食又要多吃一些。只要它多吃,我找的豬草就得不斷增加。這讓我極大的不舒服,所以只要我見它在圈里游走時,我就會拿棍子抽它,讓它乖乖睡著。結(jié)果恰恰適得其反,越抽它越跳,它肯定認為我不是在抽它,是在抽瘋!我只得進圈里給它撓癢癢,抓耳朵,抓肚皮,它才 “哼哼哼”地看著我,然后睡下。更讓我受不了的是,它們關(guān)在豬圈里,不僅每天要吃兩頓食,餓了一吵食,和我一樣高的豬欄,它們可以一躍而過,彈跳如同一只羊的輕便。
其實我很喜歡放牧它們,并樂此不疲。因為如果白天不關(guān)起來喂養(yǎng),放在曠野里,它們自由自在地閑逛,到處觸觸拱拱,青草,溪水,泥土,都可以進入它的食道。這樣對我來說就有很大的好處,可以減少一頓豬食,我就不用再去拔一背籮豬草。而我的父母不愿意我去放,對他們來說,放在外面糞草就流失了。把它們關(guān)起來喂養(yǎng),雖然每天兩頓豬食必不可少,但圈里卻有墊圈的土和草,糞草相對集中。那時的糞草是個寶,大人不識字也知道,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的諺語,小孩子從小受到的教育也知道,種地不上糞,等于瞎胡混的道理。無論什么糞,人們都如獲至寶,天不亮就有人起來到處去撿。特別是放牛出去的人,如果牛在路上屙糞,人們都會伸出雙手把冒著熱氣騰騰的牛糞接了捧回自家的糞堆上。這是人們生活中對動物,植物和土地飽含的一種情感因素。動物和人一同生活,都在大地的貯藏室。
那時,我的父母親應該還很年輕,只是在我的印象里,他們似乎從沒有年輕過。母親頭頂上從未脫下過的布包頭,皺紋,父親濃黑的胡子,患哮喘的黑鐵嘴臉,似乎從來都是以一副蒼老的面容在我的記憶里。特別是父親的模樣,自他離開了這個世界到現(xiàn)在,我夢里夢外出現(xiàn)的,永遠是我童年時候記憶里的蒼老。而我的母親,在我父親走后,盡管每次我回去她都會對我說,“你父親走了,覺得窄窄的屋子變得空蕩蕩”,但母親一直不愿意離開那間老屋。我只得常常回家,可是,見母親一次,心疼一次。不見時,又掛念和揪心。我記得當時,只要父母不在家的時候,我就經(jīng)常悄悄就把豬放出去。我那時是典型的應了鄉(xiāng)村的話,叫我讀書,我偏要去放豬。豬們當時有如此敏捷的身體,我想一方面來自于放牧對它們的鍛煉,一方面可能完全來自于食用野外的灰灰菜的緣故。
在我印象里,可能是那時的日子很長的原因還是其它因素,那時的豬似乎都不太肯長。一頭小豬幾乎都是從頭一年的舊歷八九月買回來,到次年的臘月里,最重的豬也不超過三百斤。我的父母親總結(jié),豬不長肉,是吃灰椒菜的緣故。他們說灰椒菜煮出來的豬食,死鐵干漿,所以喂出的豬也死鐵干漿的樣子,讓找豬草不準再找灰椒菜。但是,那時我就發(fā)現(xiàn),這樣的豬被宰殺后,豬肉才放入鍋里,肉味和煙火的味道就到處飄香,會讓人流下口水。那樣的肉,是吃得醉人的。
豬草不準再拔灰椒菜,我不服氣,卻也不敢頂撞。雖然那時其它的豬草也很多,植物的豐富,使它們的分類呈現(xiàn)多種角度,以此來識別物種和鑒定名稱。我不是植物學家,沒有資格來敘述植物界不同類群的起源,親緣關(guān)系和它的進化。它是一種最古老和最具綜合性的一門分支學科。我就是只對灰灰菜有著獨特的情感,每回去找豬草,我都會把灰椒菜同其它野菜混合,或者把其它的野菜,諸如小油菜,奶漿菜之類的蓋一層在灰椒菜表面背回來。因為怕他們發(fā)現(xiàn),為此,我得增加勞務,不得不連同煮食和喂養(yǎng)的事一起做掉。
主要的是,我對拔灰椒菜似乎上了癮。它的葉子上沾滿了灰,一拔就抹在手上。再稍微用力,把枝條拔斷,汁液滲出,帶著一股清清淡淡的芳香,我十分喜歡那種味道。還有一種因素是,我和一起去的小伙伴拔豬草,我只是到了地里就坐著,我的背籮里會自動滿上灰椒菜。因為灰椒菜是最好找的一種豬草,而他們都不敢違背父母的意愿,要找其它野菜。要命的是,每次他們的豬草里都會藏著幾個偷來的包谷,或者洋芋,他們讓我別告發(fā)他們,就無償?shù)叵劝盐业谋郴j裝滿。這顯得我小時候就很有心計。
但是,我又覺得有心計其實并不好。用我們老家的話說,有心計的人就如同心上有很多針眼,腦殼里按了彈子轱轆,或者是被上了潤滑油。其實,這是機械的功能,不是人的功能,人缺少心計還是要舒坦些。后來,我還是自食其力。由于每天去拔灰椒菜,導致手上的皮膚紅腫、發(fā)亮,有時還會渾身刺痛、刺癢。當時一直不知道原因,直到長大后才明白,它是一種含有卟啉類物質(zhì)的光感性植物,過多服食或接觸,并受數(shù)小時日曬后就會引起急性光毒性炎癥反應。
現(xiàn)在想來,大地就是如此生動。它就是為一切健康的生命,無論是莊稼,還是荒原蔓草,這本身就是一個真理。它不像今天,到處滲透著農(nóng)藥的劇毒。即使灰椒菜有種天然毒性,比起今天農(nóng)藥的毒,又算得了什么?老家有句俗語叫一物降一物,在今天,這句話應該改為一毒降一毒。農(nóng)藥噴灑過的蔬菜,豬在吃,人也在吃。豬吃了,人吃豬肉,一個循環(huán),也還是如此。我的母親現(xiàn)在也還在喂豬,但再也用不著去找豬草了。所以,想到灰椒菜這種當初連豬都不給吃的豬草,在今天成為餐桌上難得的野菜,已是自然。當然,在我的父母輩,它們很久以前也常吃,但那是吃糠咽菜的年代,只有野菜。
盡管,灰椒菜在鄉(xiāng)村的莊稼地上,依然不受歡迎。但是,它永不絕跡的崇高,令我感動。它生長著,似乎就是為了證明萬物復歸的自然軌跡,傳達著某種深邃偉大的教育。它們的蔓延,使大地上到處留有它們站立的身影。
耕牛

劉麗芬 湖 布面油畫 90x180cm 2017
毫無疑問,現(xiàn)代機器靠近時的歌聲就是牛的挽歌。只是我完全沒有想到,一頭水牛在村子里存在的價值會讓人們?nèi)绱瞬恍肌?/p>
曾經(jīng),人與動物,植物和土地生活在一起,如此地互惠互利,緊密相連。在朱家營村子里人們飼養(yǎng)的所有牲口中,我一直把牛看作是它們中卑微的“平民”。在我的印象里,牛的存在似乎就只干一件事情:耕田犁地。特別在耕種時期,牛必須完成了一天的任務,主人才會輕腳輕手為它卸下背上的重負,猶如對待一個遠途而歸的游子。這樣的場景近乎于與我的生命完全聯(lián)系在了一起,以至于我無論走到哪里,只要看見牛的身影,眼前浮現(xiàn)的就是我們遙遠的童年,故鄉(xiāng)與土地。
我回老家時,看見一老頭拉著一頭老水牛,遇見了另一老頭。我聽見他們的對話:“還把老伴拉出來走走?”
“嚯嚯!你老伴呢,你不拉我就拉出來走走啰!”
再接著說的是:“你閑著無事啦!還是吃飽了撐的?現(xiàn)在還喂牛?” 說這話的人已經(jīng)八十歲了,在村子里按輩分我該叫他爺。他們的對話讓我想起了一個詞語,時代進程。是的,在這個時代,農(nóng)事的變化的確非同一般,機器已經(jīng)早已把負重的牛替下了。牛的效益比之機器,毫無疑問滯于現(xiàn)代進程之外。我不知道人類是否都存有好了傷疤忘了疼的習性,但我卻知道物質(zhì)為王的時代,人類會對自己進行一次思想大屠殺。
這是2017年,秋天。人們的勞動已經(jīng)在莊稼地上完全呈現(xiàn)出來了,它們露出善良的面孔,沒有叫任何一種勞動落空。但是在這里,我要講述的不是大地上的果實,是兩頭牛的故事。一頭母水牛,一頭小水牛。兩頭牛都在我的其它作品中出現(xiàn)過,但我從沒有專門講過它們。我之所以單獨來敘述,是因為我以為牛有牛性,也有人性。
母水牛,是當時一個惡人喂養(yǎng)的。這個人在我們村子里是一個心腸歹毒的人,村人們都把他稱為惡人。
這件事說起來似乎有些匪夷所思。惡人喂養(yǎng)的那頭母牛,性格一向溫順,他從不把拴牛的繩索拉在手里,從來都是使用他吆喝的口令。走,停,朝左,朝右,后退。他在這頭牛的面前永遠像個指揮官,命令一向有效。唯有一次,他在一個山腰下的水塘里給牛洗身子的時候,一向溫順的牛,反抗了起來,跳起,奔跑。他發(fā)出的指令,牛充耳不聞。他不得不第一次拉上繩索把牛逮回來,然而,牛像和他較上了勁,朝著相反的方向拔河比賽似的使勁掙,把他像個肉團一樣甩了飛開。當他憤怒地起來準備去打牛時,山腰上一個巨石轟隆隆滾落而來,正好砸在他洗牛的地方。
從那以后,他對那頭牛無比關(guān)心和呵護,近乎于親人的情感。他雖然敢于命令,卻再也不會對它只有消費性而高高在上。為捍衛(wèi)牛的信條和公正,就是每天夜里,他也要給它上一回夜草。他對人的態(tài)度也從那件事情后,從此改變,非常和善。那頭母水牛后來生下了一頭小水牛,死去了。而那頭小水牛,他一直精心喂養(yǎng),從未放棄,與牛一同沐浴陽光和風雨。從他現(xiàn)在拉出來放牧的樣子可以看出,雖然他和牛都老了,但是牛和他看上去如同苞谷釀制的酒一樣,清純,寧靜。他和牛的老,完全是一種安然自得的老。
另一頭小水牛,曾經(jīng)是我家與別人家合喂的。關(guān)于那頭牛,對它的喂養(yǎng),我曾在我的長卷散文《依托之地》里寫朱家營村的鐵匠時,刻意為它寫過這樣的文字:
“那是在八十年代的時候,土地剛下戶沒得幾年,一個村子里的人家?guī)缀醵己茇毨ВB一家人獨自飼養(yǎng)一條耕牛都很困難。在我父親和鐵匠的共同協(xié)商下,他家與我們一起湊錢買了一頭耕牛回來,輪換著每家放牧一個月。在村子里,人人皆知,我父親做事就算一個十分認真仔細的人了,可鐵匠在對牛的照顧上,比我的父親還仔細得多。輪到鐵匠家放牧的時候,他發(fā)現(xiàn)牛踩在碎石子上跳了一下,回來后,他就用報廢了的車輪胎,做四只鞋子。只要拉出去放牧的時候,他就把它套在了牛的蹄子上,以防牛腳踩在小石子上腳疼。冬天的時候,他還用棕樹皮縫了四只套子,套在牛腿上。以至于那頭牛在村子里所有的牛中,仿佛也顯得有些尊貴。我一直記得,它在走路和吃草的時候,都得意地搖頭晃腦。脾氣也有些古怪和霸道,一同吃草的牛,只要吃到它吃著的地方,它低著頭就頂過去。最后那頭牛死了。在那個時代,一頭牛的死亡,對于一個家庭來說,除了是天大的一筆損失,還像是生活里失去了一份生機。為此,我的母親還哭過,父親永遠那么沉默。”
我之所以把這段現(xiàn)成的文字引用,是這頭牛在我的父輩們心里的地位,它是如此地重要。我記得在輪到我們家喂養(yǎng)時,我經(jīng)常拉出去放牧。我刻骨銘心的一次是,有一天我們幾個伙伴都把自家的牛一同放在山野上,突然狂風,雷電和暴雨襲來,讓我們無處躲藏。那時,每個人都騎在了牛背上,想趕著牛快走,但是其它所有的牛站著一動不動,用鞭子也打不走。唯有我們家的小水牛,它卻托著我,以從未有過的速度,向著家的方向奔跑。
在當時,喂養(yǎng)牛是一回事,使用牛是另一回事。村子里有專門使牛的人,對于一頭牛來說,他們不管牛脾氣如何,只看它是否愿意出力,溫順,不躲肩,不縮腳,是否會懂得犁溝的方向?的確,我們家的那頭小水牛,因為年輕和嬌慣,犁田耙地時它確實不會順著犁溝走。它任性,倔強,累了,它還會把前腳輕輕跪下,嬌滴滴的。因此很多使牛的人都說它是一頭笨牛,說我放牧不懂管教也笨得像頭牛。這樣的話,當時對我有著巨大的打擊,讓我萬分惱怒和沮喪。我以為,這是無端的恥辱。我以為,如果我有力氣,一定會沖過去把說這話的人干翻(但那只是如果有力氣的話,事實上是沒有力氣才那么想的)。因為等我長大有力氣的時候,我既不惱怒也不沮喪,想把人干翻的萬丈雄心和我的以為,全都跌落成了守護自己底線的秘密。因為這個世界上,牛被人說成笨牛,也就有人被說成笨得像頭牛的。人笨得像牛并不奇怪,因為人的經(jīng)驗,或者說人類的經(jīng)驗在有些時候其實根本無法獲取。比如人對生命的認識,生命不在,就是死亡。但是再聰明的人,也不可能獲取死亡的經(jīng)驗。何況我自認為自己不算笨牛,最多算作頭倔強的牛而已。其實井底之蛙,誰又能肯定沒有它的天地?我一直對這個成語故事的解釋存有偏見,都說井底的青蛙只看得見簸箕大的天空,可那天空是不是無限沒有人說得清?反過來說,如果人站在天空的背景下看井底之水,我敢保證看到的肯定還沒有簸箕大,看到的就只有自己的一個頭,或者一張臉那么大。
牛不一樣,不管人如何看如何說,牛似乎不會有絲毫的困惑與抗爭。我認真地觀察過它們的目光,永遠深邃,執(zhí)著和安靜。如果你要管理它們,一截木樁,一根繩,它就乖乖地在原地。在過去,因為它們的勞作,沒有誰家的牛有過體胖毛亮的時候。骨頭清晰,牛毛荒蕪。那不安分的骨頭,受苦的骨頭,似乎隨時可以戳穿那層枯皮。但是,它們永遠是那么平靜地接受。
我從地方的一些記載里,看見這塊先祖的土地,看見過對牛的說法,如此美好。看吧!“小馬生一歲,肚帶斷九根;小牛生一歲,犁頭斷九部;小羊生一歲,羊油有九捧;屋后有山能牧羊,屋前有壩能栽秧,壩上有坪能賽馬,又有沼澤地帶能放豬,寨內(nèi)又有青年玩耍處,院內(nèi)又有婦女閑坐處,門前還有待客處……屋后砍柴柴帶松脂來,屋前背水水帶魚兒來;趕著神仙牛,去到滋滋地里犁。”
噢!如此自然的水草豐美,沒有了,沒有了。玩耍,閑坐,待客,挑水就可以帶回的魚兒,沒有了。之后,人們?nèi)找婀陋殻≈螅f籟俱寂!這個過程仿佛化學的變幻莫測,仿佛在一個公共的合唱里。
看吧,牛。當時是趕著神仙牛。這種宗教看中的靈性,食草者,它守住自己內(nèi)心里的東西,守得很牢。它的存在,是人類與自然的一種古老的關(guān)系,在時間的某一點上,永遠保持平衡!
農(nóng)具
時代發(fā)展到了今天,誰能說農(nóng)活不是一部壯麗而深刻的書?認識,理解,經(jīng)驗,從春天泥土的芬芳到它最后沉重的果實的厚味,無一不在每一頁的內(nèi)容里。它有千姿百態(tài)的生命在里面,但是,它并不是一切時至就能產(chǎn)生。它需要人們在上面付出勞動,汗水,也需要人們的厚道和所求有度。
我記得在老家村莊里的人,他們干農(nóng)活經(jīng)常會說一句話,人強哪抵得家什硬?他們說誰家的鋤頭好使,鋒利,一鋤下去就挖到底。是的,鋤頭在手中掄起,挖下,掄起,再挖下。它在弧線里,與大地保持著勞動的關(guān)系。這個動作重復無數(shù)次,就可能會換回秋天的果實。我以為,這不是對家什強硬的贊美,完全是一種對待農(nóng)具的情感和依賴。
我想記敘的就是這些農(nóng)具,說起來或者都是些破銅爛鐵。我時常憶起一個情景,潔凈的藍天,破墻。莊稼地上的綠色在滿地蕩漾的時候,鋤頭之類的用具就靠在破墻邊,或者掛在墻上。如果放在天井里,一場雨水沖刷,農(nóng)具上就會掩映著黃銹的光澤。與廢棄之物,別無兩樣。就是這些如同廢棄的東西,在農(nóng)事中,卻不可缺少。
但是,我主要講述的兩樣農(nóng)具是,鐮刀和鋤頭。因為他們是農(nóng)具,也成為了我們村里兩個人的兇器和武器。這是我回老家時突然看見一個滿頭白發(fā)的老人,讓我想起了人們農(nóng)活中離不開的這些農(nóng)具。多年前,一把鐮刀,一把鋤頭,把他和另外一個小年輕人的人生,分了一個叉。他們本來可以用農(nóng)具,把日子過得平平靜靜,沒想到,他們卻因為手里的農(nóng)具走進了人生的深淵和黑暗。
真相。嘲弄。貧窮的傷害。尊嚴。在這里,我不想評判人性的善惡,也不想敘述事件的是非,我只想對它進行陳述和還原。兩個事件,我都是在場者。先說叫慶慶的人,這個人比我年長兩歲,在村子里與我同輩。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我們都還是孩子。那時,我們每個人身上都帶著一把小鐮刀。大人用來收割稻谷和砍包谷草,我們用鐮刀是每天都必須去田埂上割兩捆青草,喂牲口和墊圈。在出發(fā)之前,我們都喜歡先在他家門前的一堵破墻上,練膽子。玩各種比賽。比誰從墻上跳到地上的距離,誰遠誰近。比在墻上奔跑的速度,誰快誰穩(wěn)。比金雞獨立的時間,誰站得久。最后分出勝負,勝者可以在割草時優(yōu)先把最好的青草歸為己有。我記得在當時,那堵破墻上有幾個紅色的大字“春風吹戰(zhàn)鼓擂”。在那件事情發(fā)生后,我覺得那句標語口號,仿佛專門為他而寫,如同咒語一樣。
春風吹就不說了,我們每天在破墻上都玩得比春風吹更快樂。當時,慶慶是站在墻上跳得太遠了,一下就跳到了別人家的菜園子地里。剛好主人家路過,一個叫姜巴三的男人。他是我們的長輩,在我們心里長得十分粗大,結(jié)實。他的拳頭像個榔頭。他看見了,慶慶的腳下把兩顆白菜踩得稀耙爛。他快速過去,就在慶慶的背上擂了一拳頭,打得空聲氣響。本來高興得笑容滿面的慶慶,突然就“哇”地大哭了起來,嘴里罵出了“狗日的,日你媽”的臟話。哭聲和罵聲一串串噴出,拳腳也跟著在他身上如同戰(zhàn)鼓嘭嘭砰砰地響起。不知誰在旁邊喊:“鐮刀,砍他!用鐮刀,砍他!”
慶慶哭著爬起來就往墻邊跑。姜巴三也沒有追他,彎下腰去把他踩爛的菜扶起。他正在撿菜葉子,一把鐮刀從側(cè)面,插在了他的腰上。“冒血了!冒血了!”我們喊過后,就全都嚇得話也不敢說。慶慶在把鐮刀插在他腰上的時候,他就像有條狼在他后面追著一樣,失魂落魄的腳步聲很快就消失了。姜巴三后來被拉到了鄉(xiāng)衛(wèi)生院,聽說油都被帶了出來。
那個時候,慶慶才十五歲。為這件事,他家里喂著的一頭年豬也被強行賣掉。為此,他被他爹的棍棒逐出了門,東游西蕩了一段時間,也沒有再上學,后來進了城當三輪車夫。我掙學費的時候,就是去找他一起蹬過的三輪車。長大后,回來提過兩門親事,但都沒有人愿意嫁給他,說他殺過人。后來說成了一門,喊他賺夠禮錢就結(jié)婚,結(jié)果他還來不及賺錢,說好的親事就在別人的鞭炮聲,吹吹打打的嗩吶聲中抬起嫁妝,迎娶走了。
他也曾后悔過,就是那一把鐮刀,使他過早地失學在社會中立足。他現(xiàn)在都還遠在他鄉(xiāng),很多年了,我都沒有見到他。我每次回家路過他家門口,門都是緊鎖著,蜘蛛網(wǎng)在房檐門框之間,織起了好幾個。
另一件與鋤頭有關(guān)的事情,也是在多年前,因為守水。對于這個老頭子,我那時候其實非常不喜歡他的,因為我曾丟失過一把鋤頭,我一直認為是被他偷走了。甚至很多年,我只要見到他扛著鋤頭都覺得就是我丟失的那一把。但是,守水發(fā)生的事情,我對他一直內(nèi)疚,我覺得他卻是因我而起。我記得那一年,田里的秧苗剛剛活過來,就遇上了干旱。一個星期的時間不到,春天的秧苗就變得像秋天一樣的顏色了。每家都去守水,有的守白天,有的守守晚上。晚上還分上半夜和下半夜。我在半夜雞叫的時候就拿著鋤頭和手電筒去守水,在路上遇見了老頭。事實上一個夜晚都有人,只是我們一同順溝理水的人會在同一條心上。大家一同合作,到該分叉的時候挖開一個小口子。但每個人必須到村莊后面一條叫后河灣的地方,把水引下來后,然后與流水賽跑,跑到分叉處,各人守住一個口子。反正上面引下來的水,到了支流處的一個水口流點,越往下水就越來越小。我們都不能死守著自家田里的水口子,只有守著大股的水以防別人從中分走。他守最上面,有人守中間,我守下面,一條溝上排起的人像樁子一樣樹在那兒。快到天亮時,村里又來了一個年輕人,他從源頭理了下來,到了老頭守的口子旁,他要分一股水。老頭不讓,兩人起了爭執(zhí)后,年輕人扛著鋤頭走了。到了我這兒,他威逼我說分他一股水,不然就把我的全部堵掉。說著就直接來挖我守著的水口子,我當然也不讓。他挖開,我又挖了把它堵上。我和他正叮叮當當?shù)卦谙嗷嚢桎z頭,沒想到老頭過來二話沒說,掄起鋤頭就向他的頭上敲去。他倒在了溝里,老頭才說“大天光了才來,讓我們白球啦啦守大半夜?就球大點本事,欺負個小娃娃?”
出事。圍觀。熱鬧。很多人像是聞風就圍了來,七嘴八舌,同情的說“不就是一點水,鄉(xiāng)里相鄰為何下這樣的毒手?”咒罵的說“該打,這種人該打。勞力不出,就圖撿便宜!”可是老頭一口咬定說,“他打個小娃娃,人家既不回嘴也不還手,我咋看得過去?”
當有人把他從溝里扶起來,看見泥漿上的血,大家都沉默了。誰也不再抱怨,誰也不再爭論,有人背著把他送進了醫(yī)院。
老頭沒有想到,他勞動所用的那一把鋤頭工具,成為了罪犯的利器把他送進去了。因為他拿不出醫(yī)藥費的錢,這件事被報了公安,最后以確定為利器傷人,判了他十年。十年后出來,他依然還得扛著鋤頭,去到地里開墾生活。關(guān)于這件事,在我的生命里有著一縷陰深的苦惱。我一直在想,他究竟是一種狂野不羈的悲傷中爆發(fā),還是因為對我的關(guān)懷。后來,盡管我知道真實的原因是,他既不是一時的爆發(fā),也不是為了我,而是一場與那個人的父親過結(jié)的一場純粹的舊仇報復。但我愿意相信,他是因為我而惹出的事端。如果不是我,他可能不會用鋤頭把那個人干翻,這樣他就不會在牢房里蹲了十個年頭。給予我安慰的是,我回去經(jīng)常見到他,他的生活并不因為坐過牢暗淡。恰恰相反,他很陽光和安靜,對生活體察入微。我注意過幾次了,我發(fā)覺他有一副極其敏銳的耳朵,從人的腳步聲或者說話聲中,他就可以觸摸到一個人的面孔。
當然,鋤頭的作用在日常的農(nóng)活中,不可缺少,也不會當作更重要之物。人們用時,就拿起它,不用時就隨便放在一邊。鄉(xiāng)土的生活就是自然的,沒有遮遮掩掩。比如哺乳期的女人,在地里干活,孩子餓了哭了,女人鋤頭一丟,摟起衣服,露出半個圓實的乳房,就給孩子喂奶。誰也不會奇怪,因為那是神圣的哺乳的流程。年輕的小媳婦們,只要坐在一起,她們會把黑夜里的事情像滾豆一樣滾出來。現(xiàn)在我發(fā)現(xiàn)鄉(xiāng)村里的篩子很少見了,以前經(jīng)常看見在草垛旁,那些年輕的小媳婦會坐在一起,一邊用篩子篩豆子,一邊會相互說起兩腿間的故事。她們的生活教堂里,總是有煙火,有肉味,有火焰的焦香。
我之所以記述這些農(nóng)具,不是為了想說出它們對人類的價值。我只是為了想表達無論時代如何發(fā)展,或者在任何情況下,它始終具有其潛在的意義。
碓窩
時代發(fā)育快得驚人,很多新東西接連地出現(xiàn)在我們的眼前。它不得不讓一些過去的舊物,逐漸消隱。未來也正在等著我們,盡管未來誰也無法預知和決定,是惶恐,還是給人安慰?我頂上一代人,他們期許的未來,未來現(xiàn)身,他們現(xiàn)老。但是,無可厚非,人類都在相信和期許中。
那過去,難道就是虛擬的懷戀?真巧,我回老家時,看見村子后面一家人在收拾一塊地盤。他正在費力地把一大塊有菱有角的石頭,移朝一邊。我看見那塊石頭,是一個碓窩的半邊。準確說它應該叫石臼,只是在我們老家,人們都叫碓窩。我記得小時候我就問過識字的人,他們說,當時叫“隊窩”。理由是“隊窩”是公共的,曾經(jīng)放在隊里的大路邊,誰家需要舂什么東西拿去舂就是了,不需要和誰說,不需要他人同意,只有人與物的單純關(guān)系。
從存在的角度講,它把歷史埋在了土里,見證了過去的時光。哦,這時間的證物。在當時,是石匠用錘,用鑿子,用他認真而精湛的技藝,在一整塊石頭上,一錘一錘重復。重復。再重復。在不斷的重復中,給自己和別人帶來安慰,帶來驚喜。他刻下了時間,刻下了一個時代的生活,還刻下了,一副明媚的喜鵲登枝圖。它的寓意無疑表露出,喜慶。是的,喜慶,唯一的:來啊,美好的生活,谷物被碓棒慢慢地把皮舂脫后,亮閃閃的白米出現(xiàn)了。喜泣,慶幸,這神的恩賜啊!
自然之石和人工的疊加,它就成了物,成了器具。在那個時代,它是人們生活的加工廠,甚至上升為一種宗教。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記述的一件事情,人們都固執(zhí)地認為與碓窩有關(guān)系。
作孽。債務。報應。人們一向這么認為。這說起來有些神神叨叨,沒有什么邏輯和規(guī)律,沒有什么科學和迷信,更沒有,合乎常理的解釋。但是,人們都眾口一詞,三友成為瘋子,就是因為那個碓窩。“他為什么要把它劈開?劈成了兩半,不就一半變成陰,一半變成陽?分開啦,陰陽不結(jié)合,他腦殼咋個不亂套?”當然,他們的這個道理,近乎于上帝在創(chuàng)世之初,剖開混沌,被它一分為二的,就是白天和黑夜。所不同的是,三友不是上帝,分成陰陽后就無規(guī)律可尋。人的所謂敬畏,是相信一個石頭鑿成的碓窩也有魂,相信頭上三尺有神靈。
物或者器具,爛了,還原本身,又成為石頭。時間是何年何月,我已記不清了,記憶里存在的是,碓窩的一半,被人們推在了溝邊,墊著洗衣洗菜。另一半,不翼而飛。現(xiàn)在,我看見了,半邊碓窩上的喜鵲登枝,一截枝頭折斷,喜鵲剩下半個身子,兩只小腳緊抵在樹枝上。那個姿勢,讓我想到喜鵲哭泣的掙扎。我走近去看,隨便抽了一支煙給主人。他看著我嘿嘿笑說:“這塊爛碓窩,以前當作寶,埋在地里頭,現(xiàn)在送人都沒得人要。”是的,時間久了,這公共的東西也便成為己有。可已經(jīng)隸屬于他個人的東西,如今他覺得變得擋手擋腳。這種現(xiàn)象,是不是對物質(zhì)的態(tài)度決定精神的態(tài)度,是不是民間俗語里說的偷雞不成蝕把米的一個例證。
曾經(jīng),三友的狂熱,思維活躍,無知無畏,都被人們說成是因碓窩而起。他精神的亂套,是一把大錘制造的后果。當時,他提著一把大錘,從村子中擺放碓窩的地方路過,就有人和他打賭。賭注是一包一毛二分錢的春耕牌香煙,說路邊上的碓窩是整塊石頭的,如果他一錘可以齊展展打成兩半,那香煙歸他所有。他平日里本就是一個吊兒郎當?shù)娜耍鍪裁词露疾辉阜敗o論喝酒吃飯,誰和他賭誰輸,他的食量仿佛永遠在饑餓狀態(tài),大得驚人。
的確如此。只要他認真干的事情,在村子里同齡的人中,沒有人可以和他比。特別是在田里捉拿黃鱔,仿佛是他天生的技能。只要見到黃鱔,無一條可以逃脫。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他會帶著我們?nèi)ヌ锕∩希浅5靡獾啬钪恢撬麚靵磉€是他自編的順口溜。我至今還清晰地浮現(xiàn)著那樣的場景和他說話的神情,在熱辣辣的太陽下,他看著田埂邊的小洞,就彈一下響指,蹲下身把手指伸進洞里,嘴里念著:“先生教我人之初,我教先生爬母豬。先生教我性本善,我教先生捉黃鱔。出來!來!來!出來啰!”就只見一條黃鱔被他的手指緊緊夾住,在他的手上,麻花一樣,扭去扭來。
命運由此轉(zhuǎn)折,真就是褻瀆神靈?三友在人們和他說出賭注時,他話都沒說就掄起大錘,“砰嘭”鞭炮一樣的巨響,碓窩被一分為二。之后,他的種種行為失常。誰也沒有想過,是他與碓窩的對抗震動,還是其它原因。人們一致斷定,這就是作孽的報應。村里的老人們說,“那是磨糧食的地方,神靈看著哩!”其實,作為孽障的妖魔,瘋的人應該就不會是他,該是與他下賭注的人。但是,沒有,與他下賭注的人,不僅什么都沒發(fā)生,反倒悄悄收納了一半碓窩。難道,人類自滿且貪婪的弱點,是個蹺蹺板,突然失誤?或者,神在那一刻打了個盹,瞬間忽略了他。
生活唯命是從。在那個時代,一些難以解釋的事情,人們信賴于神,信賴于先祖留下的經(jīng)驗和遺訓。比如,請人幫忙做事遇上天氣不好,他們都會認為是上天的旨意,說窮人請?zhí)旃ぃ幌掠甓家物L。對于人的生命的亡失,更是非常注重。只要不屬于正常的生老病死,或者在外死于非命的,都不能停放于家里超度亡魂,一律統(tǒng)一在村子十字路口交叉處的一間碾房里。碾房在過去,是磨糧食的地方。在我記事的時候,已經(jīng)沒有人再在里面磨糧食了。我曾多次進去過,里面空間很大,幾根柱子成三角形支撐著屋頂,地面上有一塊石頭鑿過的大圓盤,被一根柱子直穿于中間,像是一支箭牢牢地釘住一塊盾一樣。石板上的紋路,一條一條,非常粗大,極其規(guī)則。在石板上,就是一個長形的石頭圓柱。完全可以看出,人們以前的生活,就是靠那盤巨大的石磨和碾子碾出來的。但是,它很多年沒有人使用了,廢棄在那里,落滿灰塵。當然,那間碾房現(xiàn)在早已拆除。人們當時選擇這樣的場所,是因為在房屋建筑前后墻上,有兩道直線對開的大門,人們說這樣的門是邪門,不僅裝不住財源,還會鬧鬼,因為鬼走直路,不會拐彎。死于非命的人,亡魂超度后,孤懸的亡靈和燭火,就不會給家里帶來外面的晦氣。其實,世界為何如此遼闊?不就是我們的過去和現(xiàn)在,它都能藏住?
當然,無論唯心還是唯物。我雖然不相信村人們的說法,但我覺得這樣很好,人類想象力的產(chǎn)物神明,妖魔鬼怪,住于人的肉身里。它會讓每個人都會看到自己的卑微,更何況,誰又能真正地,可以與神對弈?
三友成為人們眼里的瘋子后,穿著打扮奇特。手里會隨時帶著一根棍棒,或者,一把尖刀。人們都懼怕于他。我主動靠近過他,事實上,他的膽子比正常人還小。他更害怕,害怕傷害,你就是給他食物,他也膽怯。在后來,我曾認真觀察過流浪在不同地方的瘋子。我注意多次了,每一個瘋子的穿著都會非常明顯地有一樣舊時公安的標識。要么一頂綠色的帽子,要么一條軍褲,或者一件軍衣。特別是肩章,他們會用兩條紅布或者紅布。我沒有患過精神病,的確不知道他們?yōu)楹芜@樣打扮自己。或許,他們的那個世界,真的是像上帝剖開混沌一分為二的晝與夜?在漫長的黑夜中活著,無邊無際?
我只是猜測。如果我的猜測沒有錯,他們?nèi)绱藷釔酃仓锛褪窍胍酝獗淼耐姥陲椝麄兊哪懬樱謶郑澏兜膬?nèi)心和卑微的自己。他們只想守護脆弱乃至卑瑣的生活,因為害怕。害怕身邊的世界,身邊的每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