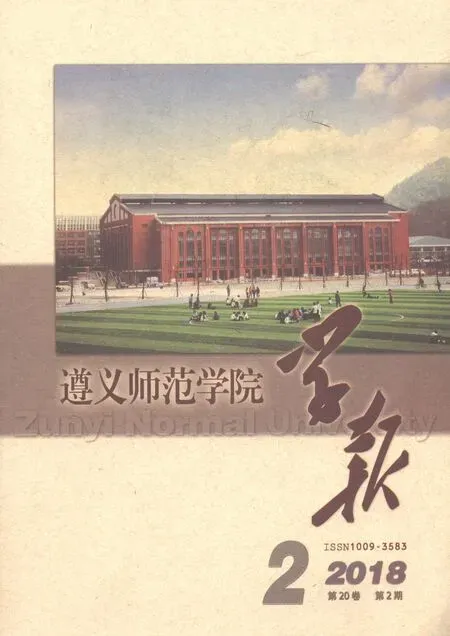湘西南民族雜居區語言生態與保護
熊及第
(吉首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湖南吉首416000)
語言生態概念最早由美籍語言學家豪根(1972)定義為:“特定語言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1]此后,經過不斷發展,涵義有所擴大。它要求我們以包容開放的態度去理解語言現象所處的人文系統,重視多種語言之間的和諧共存與多樣性發展,關注語言演變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之間的緊密關系。
移民、經濟一體化、訊息化、城鎮化給人們帶來經濟便利的同時,也悄然改變著我們的語言生活。“在民族雜居區強勢語言的威信相對較高,因而在語言競爭中,弱勢語言往往面臨使用區域逐漸縮小,功能衰減的艱難處境”。[2]因此建設民族雜居區和諧語言生態就顯得尤為迫切、重要。
一、湘西南地理范圍、民族及其語言分布
本文“湘西南”指湖南省懷化市,下轄2區、10縣(其中5個為自治縣),1縣級市。該市位于湖南省的西南,處沅水中、上游。東靠婁底、益陽、邵陽三市,北鄰常德、張家界和湘西州,西連貴州銅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南接廣西柳州、桂林二市。據2010年11月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懷化全市總人口4741948人,其中漢族 2909649人,占總人口的61.36%;少數民族1832289人,占總人口的38.54。[3]全市有漢、侗、苗、瑤等近50個民族,語言紛繁復雜。漢語方言有西南官話、湘語和鄉話。會同、溆浦、辰溪三縣說湘語。鄉話主要分布在沅陵西南部以及溆浦、辰溪與沅陵交界帶。其余方言為官話區,屬西南官話黔北小片。境內還夾雜著一些小土話,如“酸湯話(酸話)”“二里話”“四里話”“軍話”等。民族語中的“侗語主要分布在四個民族自治縣以及會同、洪江西部;苗語主要分布在麻陽,其次是靖州和沅陵;瑤語主要分布在洪江、通道、中方等地區的少數瑤族鄉。”[4]
二、湘西南民族雜居區民族語生態面貌
隨著改革開放,社會經濟水平不斷提高,“城是城,鄉是鄉”的局面被打破。以往閉塞的民族村寨打開大門,族人與外界交流密切,原有語言生態格局受到挑戰。筆者本次采取問卷與訪談結合的方式對通道、新晃、芷江四個侗族自治縣以及麻陽苗族自治縣進行了語言調查,發現湘西南民族雜居區語言生態日漸脆弱。
(1)民族語使用人數銳減,代際傳承斷裂嚴重
芷江、新晃、通道侗族人口和麻陽苗族人口與本縣漢族人口相比占優勢,但漢語卻仍為強勢語言。除部分由鄉入城的少數民族外,城區常駐居民基本不會說民族語,鄉村民族語使用人數也呈逐年下降趨勢。
芷江侗語屬侗語北部方言中的第二土語。芷江侗語使用人數下降趨勢明顯,在解放初期會說侗語的大約有80000人,到1980年時已不足10000人,而到2008年時侗語使用人數甚至不足1000人。現會會說侗語的人主要分布在羅巖、板山、梨溪口三個民族雜居鄉,主要是一些60歲以上的老人,部分中年人也會說。其它地區如麻纓塘、竹坪鋪、土橋等鄉的侗人絕大部分已轉用漢語。
新晃侗語也屬于侗語北部方言中的第二土語。現在會說侗語的人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區的一些侗族聚居鄉(鎮)如“中寨、貢溪、碧朗、李樹”等,其次是一些漢侗雜居鄉(鎮)如“興隆、波洲、方家屯”等。侗族聚居鄉(鎮)除部分長期外出求學、工作的年輕人外,大部分中老年會說侗語,而雜居區代際傳承斷裂明顯,年輕人不會說侗語,少數中老年會說。一些地方曾經會說侗語,現在基本轉為漢語方言,民族語瀕危衰亡,這些地方有涼傘、凳寨、新寨、黃雷、天堂、林沖、魚市、洞坪、晏家等。
通道侗語屬于侗語南部方言中的第一土語。現在會說侗語的人主要集中在通道縣的南部地區,如牙屯堡、坪坦、黃土、坪陽等鄉鎮。境內山峰連綿,位置封閉,族人抱團而居,形成天然的侗族小聚居。這些地方老中青三代人基本會說侗語,如牙屯堡外寨村雖與漢民僅一街之隔,但由于村內以侗族人為主,平時生活長期通行本民族語,使得侗語成為小區域強勢語得以傳承下來。村里老年人基本會說侗語,土生土長的中青年會說侗語和當地漢語方言。而通道縣北部鄉鎮靠近老縣城的縣溪口,與外界接觸密切,加之各鄉鎮語言復雜,語言交織影響,侗族鄉基本轉用漢語方言。
麻陽苗語,屬苗語支湘西苗族西部次方言。截止2013年末,麻陽苗族人占全縣總人口的78.8%,但是苗語使用人數卻少之又少。高村鎮(縣城中心)及其他大部分周邊鄉鎮苗族人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已大部分轉用漢語方言。現在會說苗語的人主要集中在緊臨鳳凰縣的譚家寨鄉楠木村以及石羊哨鄉的石羊哨村(原新田村和巒潭村合并)中,當地部分老中年人會哼唱完整的苗語歌。麻陽苗語地瀕危主要是由于歷史造成的。解放前,麻陽、會同、靖州等地的一部分苗民為躲避統治階級的驅趕、剝削,被迫逃遷至外縣、外省,剩下的苗人為隱瞞苗族身份,與漢族雜處學說漢語,已融為漢人。解放后,隨著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經濟生活水平的不斷改善,苗族人口雖迅速增加,但受城鄉經濟一體化影響,加之長期與漢人雜居,已完全喪失民族語。
總體看,湘西南民族雜居區大部分民族語已轉用為漢語方言或普通話,民族語老齡化,代際傳承斷裂嚴重。部分地區民族語雖目前使用人數較多,但在漢語方言大環境下仍處從屬地位,出于交際方便與功利追求,年輕人會逐漸放棄母語而改用漢語,民族語式微可能性較大。
(2)民族語功能削弱,使用場域縮小
各語言地位平等,但功能卻存在著差異。根據費希曼(Fishman)的語域理論,一個多語人,會依照不同的情境及活動范圍進行某種語言、方言或語體的選擇。常見語域有家庭、學校、工作地、菜市場和族內族外等。一種語言在不同場域的使用頻率是其語言功能高低的體現。
以侗語調查為例,筆者從至今會說侗語的新晃(中寨)、芷江(羅巖)、通道(牙屯堡外寨村)共抽取100人,對其常見語域中的語言選擇進行調查,詳見表1。
從表1可以看出,漢語方言在“菜市場”“與本族人”“與外族人”三項語域中使用比例最高,說明漢語方言已在民族雜居區語言中取得強勢地位。侗語在家庭中使用比例最高,其次是族內成員,而在其他語域使用人數較少。這也反應了侗語與漢語功能的不平等性,侗語使用場域縮小。普通話在學校中使用程度最高,其他語域使用程度小。據調查筆記,被試20人中19人為學生,1人為教師,他們因工作、學習及學校推普需要,在學校主要使用普通話。總之,民族語與漢語在不同交際場合的博弈中處于劣勢,使用場合減少,功能削弱。

表1 不同域語言選擇情況表
(3)語言態度“心行不一”
語言態度的“心行不一”最早是由王遠新(2009)提出的,他認為一個人對語言的主觀評價與行為傾向存在差異。[5]P16人們的語言態度與實際的語言行為常常有不一致的情況。筆者在對調查者進行一對一訪談調查時,也發現了被試語言情感與語言行為傾向存在著不一致性。大部分被試在被詢問“你喜歡自己的母語嗎?”“你覺得母語流失可惜嗎?”這兩個問題時都會表現出較為強烈的母語感情,情感態度積極。如調查合作人張雨飛父親(麻陽縣譚家寨鄉楠木村苗族人,鄉鎮教師,1969年出生)回答“我很喜歡苗語,它很親切,流失很可惜”。一些人雖然不會說民族語了,但是在調查中依然流露出對母語文化的熱愛。如調查合作人邱俊寧奶奶(芷江縣麻纓塘侗族人,農民,1948年生):“不清楚,我們這都不說侗語了,但是好東西還是要保護啊”。但當被試被詢問“如果你/子孫可以學習兩種語言你會選擇?”時 ,大部分被試會選擇“漢語方言和普通話”“英語和普通話”而不是“民族語和漢語方言”。這說明語言雖是一種身份認證,但人們更看重的還是在交際過程的實用性,功利性。由于民族語實用價值低,在大多數公共場所,如學校、公司、政府機關等派不上用場,即使人們對母語有濃厚的感情,為了交際需要被迫其他語言。
三、湘西南民族雜居區和諧語言生態建設芻議
(一)增強家庭教育對母語傳承的使命感
家庭既是母語習得的最佳場所,也是母語維系的最后堡壘。因此,家庭教育一旦不注重母語的學習,在其他地方就更難以學習了。通道牙屯堡、坪坦、黃土、坪陽等鄉鎮的侗族家庭至今還保留著說侗語的習慣,家庭語言氛圍濃厚,土生土長的小孩向父輩學習母語,母語傳承良好。因此在那些至今還說民族語尤其是有語言代際傳承斷裂趨勢的家庭里,父輩應鼓勵子女學習自己的民族語,教育他們了解自己的鄉音文化,增強子女的族群意識和民族語言文化意識,減少語言認同的功利性。
(二)學校應完善雙語教育,與時俱進
漢語方言、普通話成為強勢語言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民族語有自己的發展規律與意義,也不應隨社會的發展而被人遺忘。雙語教育則是穩定雙方和諧共生的重要因子,是促進民族特色教育發展的重要舉措。
然而縱觀湘西南雙語教育:起步晚,發展慢,以試點為主,缺乏連續性。貴州省、湘西州的雙語教育起步于上世紀50年代,而湘西南在1950年時,通道、靖州文盲率還在94%以上,新晃適齡兒童入學率也僅40%。因此這個時期雙語教育并未真正開展,而是發展掃盲教育。80年代中期為幫助少數民族兒童更好的學習漢語,部分地區曾開展“學前班+小學六年制”雙語教育,其中以通道純侗語區的雙語試點最為典型。黨和政府在坪坦鄉、隴城鄉等5個中心校開辦10個雙語班,參加實驗學生共計398人。這種雙語模式一直延續到二十一世紀初,此后由于民族語人的不斷漢化,雙語學校基本停辦。針對湘西南民族雜居區語言面貌與雙語教育現狀,筆者提出幾點拙見進行完善。
1.繼續開展雙語教育,重思教學出發點
部分地區民族語尚存活力,族人母語情感強烈,存在著繼續開展雙語教育的語言條件和感情需求。同時,語言不僅是一種交際工具,從本質上看還承載著某個民族和地區的風俗習慣、思維方式、傳統技藝等。因此可以說一種語言的消失就意味著一種文明的逝去。傳統的雙語教育主要是幫助純民族語區的孩子更好地學習漢語,這僅僅停留在語言的學習與保護上。如今的雙語教育還應以人為本,注重語言所體現的文化內涵。這是對少數民族同胞語言文化的尊重與語言權的捍衛。
2.與時俱進,開創教育新模式。
學校可開設校本課程,采取“過渡教育+文化附庸”的教學模式。在學前班和小學低年級階段采取“民主漢輔”的語言教學模式,與家庭的母語教育接軌,符合幼兒的語言學習規律。小學高年級階段“民漢并重”,能減小學生語言學習負擔的同時,還能為學好漢語打好基礎。中學階段學生已習得母語,智力得到較大開發,學校轉用普通話教學,能積極響應國家推普。另一方面學校在逐漸轉為漢語教學的過程中尤其是中學階段可進行“文化附庸”,利用課余時間和業余課為學生普及民族文化。這樣做不僅不會打亂學校正常的教學計劃,還能繼續培養和穩定學生對語言文化的學習興趣。通道坪坦中心學校開展“侗族文化進校園”就是范例,學校在進行普通話教學的同時也開設“侗族歌舞課程”,每天開展10分鐘的唱響校園活動,2015年8月還邀請侗文化傳承人石慶玉教學生唱《冠國保》《哆嘎堂》,并錄制光盤通過教育局將侗歌文化推廣至通道其他32所中小學校,引起了社會良好反響。
3.加大師資培養力度,提升教師待遇
由于雙語試點學校多選在鄉鎮中心完小,經濟設施相對較差,許多年輕教師不愿去。因此需要提高雙語教師的工資待遇,改善住宿設施。此外,“雙語教師肩負著培養少數民族地區未來社會主義建設接班人的重任,應不斷加強專業理論知識學習和教學技巧的培養,吸取科學的教學觀念,與時俱進”。[6]為此,可依托臨近高校做好定向雙語師資培訓工作,開設侗漢、苗漢雙語在職教師培訓班。而少數民族在校大學生具有母語與文化優勢,應鼓勵大學生學好文化知識,將來回家鄉工作。
(三)打造“民族文化合攏宴”,提升語言實用價值
文化旅游已成為當今世界旅游業的潮流,民俗文化作為透視社會的“廣角鏡”,以鮮明的地域特征而成為最具特色的旅游資源。[7]在市場經濟運作下,整合少數民族文化資源,發展旅游產業,使文化資源的擁有者獲取最關注的經濟利益,有利于提高他們母語的使用頻率,增強對母語的認同感,從而提高母語價值。2015年懷化全市旅游等級景區(點)增至34個、其中4A級景區(點)5個,人文景觀頗為豐富。通道有馬田鼓樓、芋頭古侗寨、坪坦風雨橋;芷江有龍津風雨橋、天后宮、抗日戰爭勝利受降紀念坊;洪江有古商城、芙蓉樓;會同有高椅古村、粟裕公園;新晃縣有大橋溪遺址。各族人民多才多藝,明間藝術紛繁多彩。如通道有侗族大歌、大戊梁歌會、蘆笙舞,靖州有苗族歌鼟,麻陽有花燈戲。但懷化人文景觀卻整體呈現出“中心無力,四周各自為政”的缺點,文化資源分散,缺乏頂層設計,加之懷化高鐵時代的到來,“過路文化”趨勢明顯,偏僻地區難以吸引外來游客,導致語言文化發展空間進一步縮小,活力不強。因此政府可借鑒云南打造的“七彩云南”“民族文化村”“傣族風情園”民族生態園模式,抓住懷化高鐵帶來的城區集聚功能,在市區開展“民族文化合攏宴”,進行文化“拼盤”。在文化拼盤過程中做到兩個“注重”:注重突出各民族的文化的差異性、突出性而不是各文化的簡單相加。注重突出民族語在各語言交織中的主體性,減小外來因素所帶來的民族語磨損。總之,這種文化組合的互動交流,有利于使本民族文化價值在不間斷的調適中進行有意識的動態再生產,滿足他者對少數民族語言文化的參與詮釋,從而提高民族語言的使用機會與價值。
(四)網絡媒介宣傳,提升民族語影響力
民族雜居區語言面貌復雜,信息交流活躍,各民族彼此間有更多了解外部世界的愿望。電視、手機、電腦、報紙是當今社會交換信息的重要工具,因此可在充分考慮各民族對母語的心理感情和精神需求的前提下,在少數民族自治縣開展喜聞樂見的方言節目,如將《貓和老鼠》配音成方言版,有利于增強語言的親和力和喜劇效果。在地方報刊定期開辟民族文化專欄,介紹有趣的民族風俗、民間傳說、趣詞來源等。針對青年網群,開發富有時代氣息、新鮮有趣的APP微信平臺等。當然在進行網絡媒介民族語言文化普及時應注意幾個問題。首先,應去粗取精,避免低俗。其次,要推廣適量,以不影響普通話的推廣為前提。最后,要尊重雜居區其他民族了解信息的平等權,為不影響雜居區其他民族的觀感,在少數民族語活力強的地區,方言節目可采用“民語漢文”的播放形式。
四、結語
湘西南雜居區語言生態脆弱而復雜,民族語活力減小、弱勢語言向瀕危語言轉變。充分發揮家庭、學校、政府、網絡的連動效應有利于促進雜居區多種語言和諧共生,延續弱勢語言活力。
參考文獻:
[1]Haugen,E.The ecology of language[J].In Fill&Mhlhusler(eds.).2001.
[2]王仲黎,王國旭.弱勢語言生態環境的自我建構——云南省鎮雄縣丁目術村苗族語言和諧研究[J].遵義師范學院學報.2011,(6):45-48.
[3]2010年湖南懷化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1號)[Z].懷化:懷化統計出版社,2011.
[4]胡萍.湘西南漢語方言語音研究[D].湖南:湖南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6.
[5]王遠新.語言田野調查實錄(三)[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
[6]王坤.少數民族雙語教師職后培訓面臨的困境及對策研究[J].遵義師范學院學報 .2012,(4):80-83.
[7]鐘金貴.論民俗文化與旅游[J].遵義師范學院學報,2008,(2):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