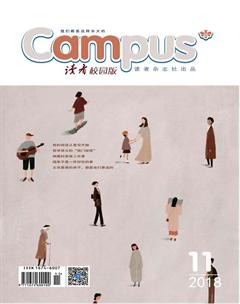了不起的少年感
劉慧凝
今天,我想講幾個少年的故事。
第一個“少年”是我老公,典型的理工男。
不管你給他提什么時尚建議,他的穿著都保持著大一新生的那種質樸感:前面戴一副黑框眼鏡,后面背一個雙肩包,左邊一個水壺,右邊一把雨傘。
他的衣服非常簡單:春天,文化衫;夏天,文化衫;秋天,文化衫;冬天,還是文化衫。但是有重要活動或重要節日時,他會選擇時尚格子襯衫加文化衫。
四年前,他向我求婚。
周圍的朋友給了好多建議:比如,買一個蛋糕,點一圈蠟燭,擺一個心形。他說:“我不用那些。”他讓我閉上眼睛,把我帶到一個小黑屋。我特別期待,覺得從小看的那些偶像劇的情節終于能在我身上發生一回了。
我一睜眼,什么都沒有。突然,他說:“起!”我再一看,滿屋子都是綠光。
哎呀,我有點蒙,我說:“哥們兒,這……什么意思……”
他說:“哥們兒這個綠光,波長是520納米,這樣到處都是我愛你了。厲害吧?”
對于這種“一根筋”的浪漫,我早就習以為常。他覺得對的事兒,就會特別堅持。
我要講的第二個“少年”是個北京男孩,他成績好、幫助后輩,是我的偶像。
但他特別犟,在國外工作時,只準自己和家人吃雞腿,因為雞腿比其他肉、蔬菜、水果都便宜,家人想吃一塊西瓜,他都不同意。
其實他不窮,在國外做教授,工資很高,但他就是不花。他把錢省下來交給金融機構打理,錢生錢,繼續吃雞腿。甚至后來查出肺癌,大夫推薦了500塊錢一粒的藥,他嫌貴就是不吃,找50塊錢一片的仿制藥,服用后全身過敏。
2012年,是這位“少年”人生的最后一年。面對絕癥,他對家人溫和、理性,又很犟地說了一句話:“停止治療。”他省下高昂的醫藥費,取出一輩子攢的1500多萬元,資助幾千名少年。剛才講的這個“少年”不是別人,就是清華大學1951級無線電系本科生、清華經管學院教授、中國金融學家、享年78歲的趙家和老師。
去世前三個月,他簽訂遺體捐贈手續,把自己捐給了醫學研究等事業。這個摳門的、很犟的“少年”,最終連自己都沒給自己留下。
他和他那1500多萬元的助學金從北京走向遠方,走進了更多少年的生命里。我為什么叫趙老師“少年”?因為少年不是按照年齡劃分的,而是有沒有少年感。
什么是少年感?是沖動魯莽、三分鐘熱度?不,那只是表面。
少年感是明知不敢為、不能為、不必為而為之。
做任何事情,首先考慮的不是成本——我賺了還是虧了,也不是結果——我成了還是敗了,而是這件事應該不應該做。
社會和國家最有活力的地方就在于少年。社會和國家沒有活力的時候,不是人口老齡化的時候,而是這里的人失去了少年感的時候。大家都安于現狀,停止創新,害怕挑戰,害怕改變,害怕付出。
我們每個人的心里都有一個少年,對嗎?那是屬于我們的英雄夢想。我們心底最害怕的事情,是怕辜負了那個少年的自己。
但是哪怕我們自我懷疑、自我否定到近乎絕望的時候,就是不想死心啊!不想放棄,在一無所有的時候,心里只有那份扎心的熱愛!
我終于知道什么是少年感,是理工男一根筋地用他的方式喜歡你;是趙老師不計成本、不圖結果地去守護少年、守護未來;更是我們想改變自己時,哪怕內心害怕,害怕到手腳發抖,也要履行承諾勇敢出發。
所以,以后若有人問你:“少年,你圖什么?”你告訴他:“我不圖什么。我是少年,從來不想長大,卻已經長大。但如果我不想變老,就可以不必變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