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部以一手史料見(jiàn)長(zhǎng)的《丁玲傳》
——李向東、王增如版與蔣祖林版《丁玲傳》對(duì)讀
閻浩崗
河北大學(xué)文學(xué)院
從2015年5月到2016年10月的一年多中,先后又有兩部重要的丁玲傳記出版,即李向東、王增如夫婦的《丁玲傳》(以下簡(jiǎn)稱“李傳”)和蔣祖林的《丁玲傳》(以下簡(jiǎn)稱“蔣傳”)。這兩部傳記與迄今為止出版的其他丁玲傳記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所披露的一手資料多、信息量大。這一特點(diǎn)的形成,與作者的特殊身份或位置有關(guān):蔣祖林是丁玲的兒子,王增如是丁玲晚年的秘書。他們憑著自己與丁玲的零距離接觸,獲取了一些別人難以得到的資料。因此,盡管已有二十種左右丁玲傳記行世,其中有些已寫得相當(dāng)好,但李傳與蔣傳的出版仍引起丁玲作品愛(ài)好者與丁玲研究者的濃厚興趣。
那么,這兩部丁玲傳記究竟給讀者哪些新的史料、新的理解?其獨(dú)特價(jià)值具體何在?我們可以圍繞丁玲一生中的一些關(guān)鍵問(wèn)題,將這兩部著作對(duì)照閱讀,看它們是如何解答、如何表達(dá)的。
關(guān)于丁玲的婚戀
丁玲一生感情經(jīng)歷曲折,其婚戀生活較有傳奇性,她的選擇反映了其鮮明獨(dú)特的個(gè)性,并與其人生追求密切相關(guān),因而是一般丁傳不會(huì)忽略的問(wèn)題。只不過(guò)以往丁玲傳記大多突出表現(xiàn)她與胡也頻以及陳明的戀愛(ài)婚姻經(jīng)歷,重點(diǎn)突出革命愛(ài)情的純真高尚,有些則捎帶提到馮雪峰。而在這方面,李傳和蔣傳各有新的發(fā)現(xiàn)或“爆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蔣傳對(duì)丁玲、瞿秋白之戀的披露與李傳對(duì)丁玲、陳明與席平三角戀情的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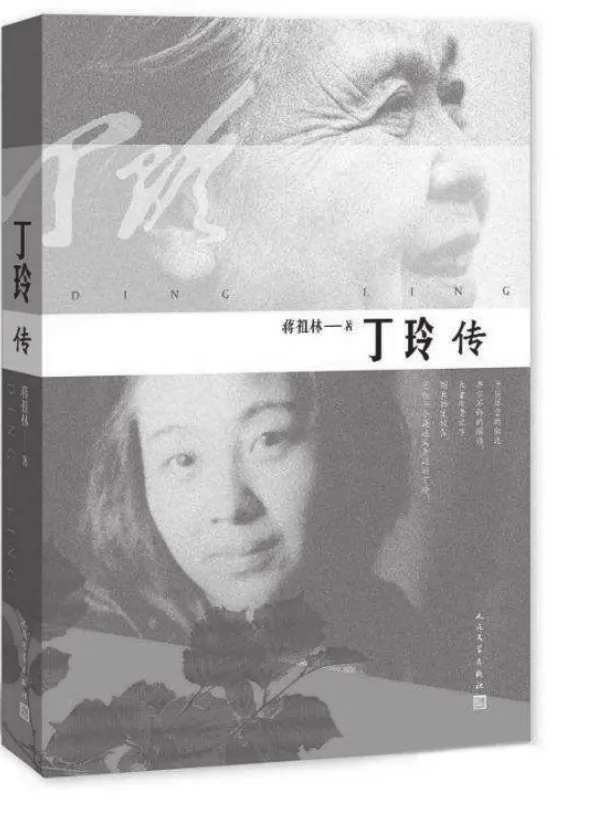
蔣祖林著《丁玲傳》
直到李傳出版,各種丁玲傳記在述及丁玲與瞿秋白的交往時(shí),只寫丁玲對(duì)瞿秋白與王劍虹戀情的成全,而丁與瞿之間的感情,則被寫成一般的友情。蔣傳卻依據(jù)作者與傳主的私人談話(母子夜談),直承丁與瞿之間的感情已超越了普通的朋友之情,而屬于純粹的戀情:
有一天談到她和瞿秋白之間的事,她若有所思地稍稍停頓了一下,隨之說(shuō)道:“其實(shí),那時(shí)瞿秋白是更鐘情于我,我只要表示我對(duì)他是在乎的,他就不會(huì)接受王劍虹。”她又說(shuō),“我看到王劍虹的詩(shī)稿,發(fā)現(xiàn)她也愛(ài)上瞿秋白時(shí),心里很是矛盾,最終決定讓,成全她。”
母親向我說(shuō)到她把詩(shī)稿拿給瞿秋白看時(shí)的情景:“瞿秋白問(wèn):‘這是誰(shuí)寫的?’我說(shuō):‘這還看不出來(lái)嗎?自然是劍虹。’他無(wú)言走開(kāi)去,并且躺在床上,半天沒(méi)說(shuō)出一句話來(lái)。他問(wèn)我:‘你說(shuō),我該怎樣?’我說(shuō):‘我年紀(jì)還小,還無(wú)意愛(ài)情與婚姻的事。劍虹很好。你要知道,劍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忍心她回老家去。你該走,到我們宿舍去……你們將是一對(duì)最好的愛(ài)人。’我更向他表示:‘我愿意將你讓給她,實(shí)在是下了很大的決心的啊!’他沉默了許久,最后站起來(lái),握了一下我的手,說(shuō)道:‘我聽(tīng)你的。’”
我聽(tīng)后,實(shí)在覺(jué)得這是一個(gè)純潔、高尚而又凄婉的愛(ài)情故事。
蔣傳特別指出,丁玲1980年寫的回憶文章《我所認(rèn)識(shí)的瞿秋白同志》中的有關(guān)描述并不完全符合實(shí)情,丁玲在這里有所掩飾。這件事起碼說(shuō)明,作家回憶錄之類不可在沒(méi)有旁證的情況下作為唯一的史實(shí)依據(jù)。對(duì)于自己所披露這件史實(shí)的可靠性,蔣祖林提出的旁證,一是其妻李靈源也曾聽(tīng)丁玲本人講過(guò)一次,二是從丁玲那篇回憶文章中可以發(fā)現(xiàn)一些蛛絲馬跡。筆者以為蔣傳的說(shuō)法是可信的:從丁玲角度說(shuō),母子之間的談話應(yīng)該最掏心,從蔣祖林角度說(shuō),對(duì)這件事也沒(méi)有必要虛構(gòu)或隱瞞。但是,讀者或許會(huì)產(chǎn)生另一種疑問(wèn),即作為兒子為母親撰寫的傳記,蔣傳為何要披露這一史實(shí)?這不是為本來(lái)就有各種猜測(cè)和傳聞的丁玲戀愛(ài)故事,又多了一個(gè)談資?不能認(rèn)為作者只是為了還原史實(shí),盡可能多地為讀者提供傳主信息,因?yàn)樵谕徊總饔浝铮髡邔?duì)丁玲最后一次戀愛(ài),也是持續(xù)時(shí)間最久的一段婚姻——丁玲與陳明的相關(guān)交往與經(jīng)歷,涉及就很少。而在此前不久出版的李傳中,丁玲和陳明的故事卻是被突出呈現(xiàn)的。筆者認(rèn)為,蔣傳如此處理,恰與李傳有關(guān),即出于與李傳“對(duì)話”的需要!二者的互文關(guān)系很明顯。
在寫到丁玲與王劍虹及瞿秋白的交往時(shí),李傳的說(shuō)法與丁玲那篇回憶文章基本一致。李傳寫到丁玲婚戀經(jīng)歷時(shí)的最引人矚目之處,是延安時(shí)期丁玲與陳明交往及戀愛(ài)和婚姻的經(jīng)過(guò)。在這段書寫中,李傳揭示并凸顯了戀愛(ài)時(shí)的丁玲性格強(qiáng)勢(shì)的一面,而蔣傳是為凸顯丁玲戀愛(ài)時(shí)的無(wú)私與對(duì)友情的看重。
李傳所敘,也是依據(jù)一手資料——當(dāng)事人當(dāng)面主動(dòng)對(duì)其所談,或?qū)Ξ?dāng)事人的當(dāng)面采訪:
陳明2007年夏天在上海參加丁玲國(guó)際研討會(huì)時(shí)對(duì)筆者說(shuō):“在西戰(zhàn)團(tuán)時(shí),有一次在一個(gè)小飯館里吃飯,我們都坐在炕上,我跟丁玲說(shuō),主任,你該有個(gè)終身伴侶了。她說(shuō),你看我們兩個(gè)怎么樣?我嚇了一跳。后來(lái)我還在日記里說(shuō),讓這種關(guān)系從此結(jié)束吧!丁玲看到我的日記,說(shuō),我們才剛開(kāi)始嘛,為什么要結(jié)束呢?”
這只是其中一說(shuō),即丁陳之戀中,丁玲是主動(dòng)的,陳明開(kāi)始并未愛(ài)上丁玲。但接著李傳又講到了另一種說(shuō)法,所據(jù)史料是丁玲當(dāng)年的“小姐們”羅蘭的相關(guān)講述:
2003年1月13日,陳明帶李向東去北京和平里,看望84歲的羅蘭老太太,當(dāng)著陳明的面,羅蘭對(duì)李向東說(shuō)起一些往事,其中說(shuō)到:“三八年在西戰(zhàn)團(tuán),陳明告訴我,說(shuō)愛(ài)上丁玲了。我說(shuō)那不行,第一丁玲是作家,第二她比你大。塞克在旁邊看到我們兩個(gè)說(shuō)悄悄話,還問(wèn),你們倆嘀咕什么呢?”
兩種說(shuō)法看上去矛盾。按常理推斷,應(yīng)該是兩人互相都有意,但面對(duì)年齡和地位的差異及傳統(tǒng)觀念、周圍輿論造成的壓力,陳明抗壓能力較差,所以選擇了退卻。為了疏遠(yuǎn)丁玲,他主動(dòng)提出調(diào)離。“丁玲卻緊追不舍,不肯放棄。”李傳說(shuō):“在這場(chǎng)頗受非議的婚姻中,我們看到了丁玲不畏人言、不達(dá)目的不罷休的倔強(qiáng)個(gè)性”,這一判斷應(yīng)該是基于曾經(jīng)與丁玲近距離接觸而獲得的對(duì)丁玲性格的了解。李傳還披露,后來(lái)陳明愛(ài)上了劇社一個(gè)搞音樂(lè)的姑娘席平,二人在隴東的慶陽(yáng)結(jié)婚。羅蘭親口告訴李向東,丁玲得知陳明另娶他人后非常痛苦。丁玲對(duì)羅蘭說(shuō)是席平先找的陳明,陳明一聽(tīng)好話就心軟了。羅蘭為丁玲不平,跑去找陳明吵了一架,并把席平罵了一頓,要求席平離開(kāi)陳明。第二天她就把陳明帶回了延安。席平是彭真的姑姑的干女兒,筆者揣測(cè),后來(lái)彭真對(duì)丁玲似乎有一種先入為主的不好印象,除了倫理與審美觀念所致對(duì)文學(xué)作品理解的差異以及周揚(yáng)的影響,也許還與此事有關(guān)。李傳作者雖然更親近丁玲,但對(duì)悲劇人物席平也寄予很大的同情與敬意,并寫到了陳明晚年表露的對(duì)席平的愧疚之情。另一方面,李傳又肯定丁玲對(duì)陳明的選擇是正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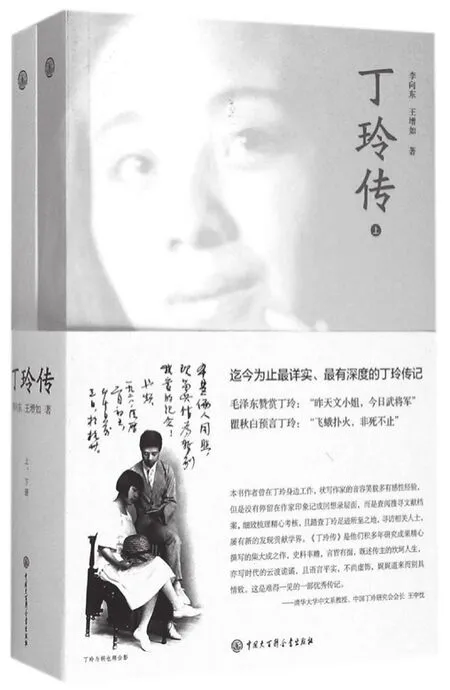
李向東、王增如著《丁玲傳》
后來(lái)的發(fā)展說(shuō)明,丁玲的眼睛真是“毒”得很,從她選定了陳明那一刻起,就把后半生的幸福緊緊攥在了手里。
此可謂持平之論。我們都知道丁玲后來(lái)的諸多不幸,但是她與陳明的關(guān)系幾十年如一日,起碼保證了家庭的和諧幸福。
相比之下,蔣傳對(duì)丁玲與陳明之戀的交代,卻非常簡(jiǎn)略,只在第287頁(yè)用三個(gè)小自然段帶過(guò),未加任何有感情色彩的評(píng)論,只訂正了一個(gè)史實(shí)記述訛誤:丁玲與陳明結(jié)婚的日期是1942年11月7日,而非那年的春節(jié)(2月15日),并以自己當(dāng)時(shí)的親歷為證。李傳依據(jù)黎辛的回憶并旁證以蔣祖林的說(shuō)法,也持此說(shuō)。兩部傳記共同糾正了陳明本人的記憶。蔣傳對(duì)丁陳情感經(jīng)歷的淡化,應(yīng)該與傳記作者本人的情感態(tài)度有直接關(guān)系——這從最后敘述丁玲晚年辦《中國(guó)》時(shí),寫陳明“夫人干政”之事可以看出。
如果說(shuō)在丁玲、胡也頻之愛(ài)中,丁玲已顯示出其強(qiáng)勢(shì)一面,但仍有一定“小女人”氣,丁玲找馮達(dá)為伴是為“娶個(gè)太太”,那么,丁陳之愛(ài)既顯示了丁玲非同尋常的“丈夫氣”,又是雙方情感的對(duì)等互動(dòng)。蔣傳爆料丁瞿之愛(ài),除了還原歷史真相,估計(jì)也為“矯正”李傳所披露的丁陳之戀中丁玲因“愛(ài)情的自私”所造成的過(guò)于強(qiáng)勢(shì)的形象。不論意圖為何,蔣傳對(duì)丁玲瞿秋白情感的揭示,給我們提供了一段新的可貴而可信的史料,其價(jià)值正如李傳所“爆”丁玲與陳明之戀緣起之“料”。綜合來(lái)看,能讓我們看到比以往丁玲傳記更為豐滿的丁玲形象:她早年初戀時(shí)對(duì)王劍虹的“讓”,既是因?yàn)殚|蜜摯情,也因她可能直感到,以自己的強(qiáng)烈個(gè)性與強(qiáng)勢(shì)性格,也許與瞿秋白這樣的人物生活在一起不太合適——作為重要?dú)v史人物的瞿秋白,是不會(huì)成為一個(gè)男性“太太”、“賢內(nèi)助”的,而胡也頻、馮達(dá)和陳明都是唯丁玲馬首是瞻的“賢內(nèi)助”型男人。
明白了這一點(diǎn),也可解釋為何丁玲最終沒(méi)有與她“最懷念的”馮雪峰走到一起:馮雪峰其實(shí)也是個(gè)比較強(qiáng)勢(shì)的人物。盡管丁玲與馮雪峰之間關(guān)系非同一般,但當(dāng)1955年風(fēng)暴來(lái)臨時(shí),他們之間的關(guān)系也一度出現(xiàn)隔閡。蔣傳揭示:
十幾年過(guò)去了,這些年里丁玲與馮雪峰各自生活、工作的環(huán)境不同,各自都有所變化,地位也發(fā)生了變化。那些年,丁玲在文藝界的地位,緊排在周揚(yáng)之后,似乎是文藝界黨內(nèi)第二號(hào)人物,略高于馮雪峰。可能馮雪峰多少還有一點(diǎn)適應(yīng)不了這一變化,因此,在相互關(guān)系上也就有了一些微妙的嫌隙。
蔣傳還寫到馮雪峰當(dāng)年所寫檢討中說(shuō)感到丁玲驕傲了,在批判丁玲的發(fā)言中說(shuō)丁玲“像家長(zhǎng),像賈母”,雖然這是特定形勢(shì)下的事情,但蔣傳認(rèn)為“應(yīng)該說(shuō)馮說(shuō)的是真話”,是“心里話”。而丁玲這時(shí)對(duì)馮雪峰也有了一些看法:她對(duì)蔣祖林說(shuō),馮雪峰擔(dān)任《文藝報(bào)》主編后曾有情緒,認(rèn)為丁玲雖然不在《文藝報(bào)》了,但影響還在,使他不好工作,“言下之意,馮雪峰這個(gè)人也不是怎么好相處的”。
然而,李傳關(guān)于丁玲與馮雪峰愛(ài)情的敘述,卻是另外一種面貌。據(jù)李傳,胡也頻犧牲后,丁玲曾很狂熱地追求過(guò)馮雪峰,說(shuō)“丁玲與馮雪峰的戀愛(ài),是一生中情感最熾烈的一次”。當(dāng)初胡也頻追求丁玲很狂熱,丁玲被感動(dòng)后,與之過(guò)起并無(wú)肉體關(guān)系的同居生活。馮雪峰是在這種情況下闖入他們生活的。馮雪峰對(duì)丁玲的吸引力超過(guò)胡也頻,是因她感到馮雪峰能完全理解他,而胡也頻不能;馮雪峰已是黨員和革命者,而胡也頻尚且不是。不過(guò),胡也頻發(fā)現(xiàn)他們的感情關(guān)系后反應(yīng)激烈,曾大打出手。丁玲與馮雪峰這才決定中止交往。胡也頻犧牲四五個(gè)月后,丁玲開(kāi)始對(duì)馮雪峰發(fā)起熱烈的愛(ài)情攻勢(shì)。“雪峰則理智、矜持得多,家庭的責(zé)任、左聯(lián)領(lǐng)導(dǎo)者的身份都約束著這個(gè)共產(chǎn)黨員”,他們之間這段時(shí)間的這些通信現(xiàn)存上海魯迅紀(jì)念館(不曾收入《丁玲全集》)。李傳上述敘述,除了據(jù)丁玲與他人的通信,還有丁玲晚年談話錄音記錄稿為證,也屬一手資料。
蔣傳的敘述與此有所不同——在“四人幫”剛被粉碎的時(shí)候,蔣祖林夫婦去山西嶂頭村看望母親時(shí),曾問(wèn)丁玲,在胡也頻犧牲后有沒(méi)有想過(guò)與馮雪峰結(jié)合的事,丁玲予以否認(rèn),并說(shuō):“如果我想的話,我相信我可以把他搶過(guò)來(lái),但我不愿意欺負(fù)弱者。”蔣傳又以丁玲1985年3月1日致白濱裕美的信為旁證。筆者認(rèn)為,蔣傳與李傳的敘述都有依據(jù),都是可信的。丁玲晚年的說(shuō)法,是因談話對(duì)象關(guān)系,加上多年后人事的變化及個(gè)人理性反思,她有了新的感受和認(rèn)識(shí)。但她也并未對(duì)兒子和兒媳明確否認(rèn)自己那時(shí)對(duì)馮雪峰追求的主動(dòng)和熱烈;她只是暗示,如果她執(zhí)意追求,不顧其他,她是有辦法成功的。而蔣傳強(qiáng)調(diào)丁玲“不愿意欺負(fù)弱者”(奪人之愛(ài)),同樣是與李傳關(guān)于丁玲在愛(ài)情追求方面比較強(qiáng)勢(shì)的敘述及觀點(diǎn)的“對(duì)話”。
丁玲和沈從文的早年友情與晚年糾葛
丁玲與沈從文的恩怨,是晚年丁玲研究者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問(wèn)題之一。兩人交往密切時(shí)是20世紀(jì)20年代后期與30年代初期,而最密切一段,是胡也頻被捕至犧牲不久。李傳較具體地寫到了胡也頻被捕前后沈從文對(duì)丁玲一家的關(guān)心和幫助。胡也頻被捕前,雖然雙方在政治上開(kāi)始漸行漸遠(yuǎn),沈從文在生活上仍然關(guān)心胡也頻夫婦,主動(dòng)把一件新海虎絨袍子借給胡也頻穿;胡也頻被捕后,沈從文很著急地找了徐志摩、胡適、蔡元培等人,試圖營(yíng)救,又陪丁玲一起去探監(jiān),陪丁玲去南京找邵力子,獨(dú)自去找陳立夫、邵洵美。胡也頻犧牲后,沈從文陪丁玲將四個(gè)月大的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寫完這些后,特地加上一句評(píng)論:“在丁玲最困難時(shí),沈從文挺身而出,全力相助,豪俠仗義,患難中見(jiàn)真情。”
蔣傳寫這段時(shí),先寫馮乃超曾答應(yīng)幫助胡也頻夫婦帶孩子,寫胡也頻夫婦為此“感動(dòng)得一夜沒(méi)睡”,并引用丁玲回憶文章中的一句話“第一次感到同志的友情,階級(jí)的友情,我也才更明白我過(guò)去所追求的很多東西,在舊社會(huì)中永遠(yuǎn)追求不到,而在革命隊(duì)伍里,到處都有我所想象的偉大的感情”予以贊美。接著,也寫到胡也頻被捕那天“穿上暖和的海虎絨袍子就走了。這袍子是沈從文借給他穿的”,寫到胡也頻失蹤后沈從文為之不安。
沈從文老友、曾任中宣部副部長(zhǎng)的劉祖春曾撰文說(shuō),1949年前后丁玲不念舊友情而冷淡沈從文,寫得很具體:
大約是三月上旬一天,從文帶著虎雛到北池子中段面對(duì)路東騎河樓那個(gè)大鐵門去見(jiàn)丁玲。從文去找丁玲的目的,并不想向她祈求什么,還是想弄清楚心中那個(gè)不明白的問(wèn)題: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和人民政府對(duì)他到底是個(gè)什么態(tài)度,是不是如郭沫若文章那樣把他看作“反動(dòng)派”。
從文帶著微笑,走進(jìn)鐵門內(nèi)那間充滿陽(yáng)光的二樓。從文原以為丁玲與他有多年友誼,能夠推心置腹地對(duì)他說(shuō)幾句真心話,說(shuō)明白人民政府的政策,向他交個(gè)底,讓他放心。誰(shuí)知道見(jiàn)了面,從文大失所望,受到的是一種非同尋常的冷淡。站在他面前的已非昔日故舊,而是一位穿上人民解放軍棉軍裝的儼然身居要津的人物。從文是個(gè)倔強(qiáng)的人,只好默默地帶著小兒子走出那個(gè)大鐵門。
對(duì)此,陳明迅即撰文澄清事實(shí)真相,說(shuō)明劉文所說(shuō)沈從文去見(jiàn)丁玲的1949年“三月上旬”丁玲根本不在北京,丁玲也從未住過(guò)劉文所說(shuō)的那所房子。陳漱渝也曾于2007年撰文予以反駁。涂紹鈞2012年出版的《圖本丁玲傳》則在引用陳明文章予以否認(rèn)之后,用公開(kāi)出版的丁玲日記和書信作為旁證。
李傳和蔣傳同樣用可靠資料與嚴(yán)密邏輯反駁了劉文說(shuō)法,說(shuō)明直至丁玲被批判的1955年,丁沈二人仍保持聯(lián)系,沈從文還曾向丁玲借錢,交情未斷;二人產(chǎn)生隔閡,是在丁玲1979年讀到沈從文寫于1930年代的《記丁玲》并發(fā)表《也頻與革命》一文以后。但在此之外,在對(duì)丁沈晚年交惡一事的評(píng)價(jià)及態(tài)度上,蔣傳與李傳卻有明顯差異:蔣傳在指出了許多研究者“在立論所依據(jù)的材料上,取其所需,摒棄于己不利”,“甚至有些已被證明并非事實(shí)的事,卻仍采取避而不見(jiàn),一而再地引用論定”的錯(cuò)誤做法之后,特別說(shuō)明丁玲與沈從文的交往“在丁玲的整個(gè)歷史長(zhǎng)河中,不過(guò)是幾個(gè)點(diǎn)滴而已”,即對(duì)二人關(guān)系予以淡化,對(duì)“過(guò)分地渲染所謂沈、丁的‘友誼’,為之‘惋惜’,并將這‘友誼’終結(jié)的原因歸之于丁玲”,表示大不以為然。李傳則站在更超脫、更理性的位置,客觀梳理了二人交惡的社會(huì)因素與心理因素——一方面指出沈從文當(dāng)年寫《記丁玲》完全出于好意,“既為宣傳丁玲也為教育青年”,又根據(jù)丁玲對(duì)《記丁玲》的批注文字,指出丁玲是憤慨該作寫胡也頻丁玲夫婦與革命的關(guān)系時(shí)的態(tài)度,“沈從文固然好心,但他那種高高在上的姿態(tài)”以及“自以為是的評(píng)說(shuō)且不乏譏諷的態(tài)度激怒了丁玲”,丁玲“因此反應(yīng)不免過(guò)于激烈”。并且指出,沈文提到馮達(dá),這也是丁玲所忌諱的。對(duì)此,沈從文本人也有知覺(jué)。李傳認(rèn)為,沈從文《記丁玲》中對(duì)馮達(dá)的描述與評(píng)價(jià),其實(shí)與丁玲自己在《魍魎世界》里所寫“極其相似”;而關(guān)于胡也頻,李傳說(shuō)沈從文“真是最理解丁玲與胡也頻感情的一個(gè)人”。這與蔣傳所說(shuō)“沈從文也實(shí)在是算不上是胡也頻的知己”之說(shuō)似有矛盾,其實(shí)二者只是著眼點(diǎn)不同:蔣傳側(cè)重從沈從文對(duì)革命以及胡也頻夫婦參加革命的理解來(lái)說(shuō),李傳則是從沈從文對(duì)丁玲與胡也頻、馮達(dá)為人性格的認(rèn)識(shí)來(lái)說(shuō)。李傳又指出丁玲忌諱馮達(dá),對(duì)于沈從文對(duì)革命的“庸俗”解讀大為光火,也與她當(dāng)時(shí)正為歷史問(wèn)題所困的處境有關(guān)。秦林芳的《丁玲評(píng)傳》也曾表達(dá)過(guò)類似看法,只是秦著完全將丁沈的“相輕”歸結(jié)為“政治功利”,完全不承認(rèn)丁玲政治信仰的真誠(chéng)性,這與李傳有所不同。
蔣傳還講到一個(gè)細(xì)節(jié)——丁玲曾對(duì)蔣祖林說(shuō)過(guò)她寫《也頻與革命》一文時(shí)的想法:當(dāng)時(shí)她也是一再猶豫的,因?yàn)樗病邦櫦吧驈奈牡慕】岛颓榫w”。但她又認(rèn)為,還是趁沈從文健在的時(shí)候發(fā)表好,因?yàn)檫@能給沈從文發(fā)表不同意見(jiàn)的機(jī)會(huì)。此事有丁玲1980年致趙家璧的信為證。蔣傳還引用陳明1991年發(fā)表于《新文學(xué)史料》上的文章——美國(guó)漢學(xué)家艾勃向沈從文探問(wèn)他與丁玲的這段公案,當(dāng)時(shí)沈從文回答:“過(guò)去的事已隔多年,我記不清了。如果我和丁玲說(shuō)得有不一致的地方,以丁玲說(shuō)的為準(zhǔn)。”蔣傳與陳明文章一樣,對(duì)沈從文當(dāng)時(shí)不作公開(kāi)回應(yīng),只在私人信件里表達(dá)不滿,而在丁玲、沈從文都已去世后的1990年,沈從文的兩封信被公開(kāi)發(fā)表,表示遺憾,因?yàn)樗廊艘褵o(wú)法作答。
筆者對(duì)讀沈從文給金介甫和康楚楚的信與丁玲給趙家璧的信,發(fā)現(xiàn)其實(shí)兩人當(dāng)時(shí)都還是有所顧忌,對(duì)對(duì)方都是既有不屑、不滿乃至怨氣,又有所憐憫的——丁玲覺(jué)得沈從文“近三十年來(lái)還是倒霉的”,想到“我的文章的發(fā)表對(duì)他是一個(gè)打擊,也許有點(diǎn)不人道”,并說(shuō)“我是以一種惻隱之心強(qiáng)制住我的禿筆的”;沈從文說(shuō)“她廿年受了些委屈,值得同情”,想到“她健康不大好,必然影響到情緒”,決定不與之爭(zhēng)辯。在1979年丁玲首次讀到《記丁玲》之前,1949年后二人再度相見(jiàn)時(shí),沈從文為何一直不曾對(duì)丁玲提及這篇作品?丁玲發(fā)表《也頻與革命》之后沈從文為何不直接作答?筆者以為,沈從文不愿提此作品,肯定不是把它忘了,而是他也覺(jué)得在新的環(huán)境下此文有些不合時(shí)宜,而且自己用了許多虛構(gòu),這些虛構(gòu)丁玲肯定不會(huì)喜歡;他不對(duì)丁玲的文章直接作答,是因它涉及“革命”這個(gè)敏感問(wèn)題,作為黨外人士且一直積極要求入黨的他來(lái)說(shuō),也確實(shí)不好回答。即使兩人公開(kāi)交鋒,也辯不出什么結(jié)果,因?yàn)閺亩×帷白筠D(zhuǎn)”開(kāi)始,雙方的世界觀、人生觀就開(kāi)始南轅北轍。沈從文認(rèn)為丁玲與丈夫介入政治是由于幼稚無(wú)知,是“誤入歧途”,丁玲則私下里認(rèn)為老友沈從文庸俗、想做紳士,乃至有些“市儈氣”。但過(guò)去友情尚在,政治觀、藝術(shù)觀的分歧尚不影響到生活上的互相關(guān)心和幫助。而這些不以為然,沈從文在《記丁玲》里確有明顯流露。他當(dāng)時(shí)以為丁玲已死,就無(wú)所顧忌,而在丁玲復(fù)出、并正奔波于歷史問(wèn)題平反的1980年,沈從文已知關(guān)于丁玲夫婦參加革命的動(dòng)機(jī)及對(duì)革命的態(tài)度之事,對(duì)她來(lái)說(shuō)非同小可,他即使有委屈,也只有對(duì)朋友私下發(fā)發(fā)牢騷了。而作為女性且多年蒙冤的丁玲,雖然盡力“強(qiáng)制住”自己,言辭還是過(guò)激了些,失去了分寸,這一點(diǎn)連陳明也承認(rèn)。李傳也直言丁玲“反應(yīng)不免過(guò)于激烈”。在后革命年代,一些不曾親歷革命、投身革命的學(xué)者,在評(píng)論丁沈之間是非時(shí),則不免傾向沈從文一些,因?yàn)樗麄儗?duì)革命與文學(xué)的看法與沈從文更接近。
丁玲與沈從文圍繞《記丁玲》的爭(zhēng)議,若拋卻個(gè)人意氣之爭(zhēng)及其他現(xiàn)實(shí)因素,其實(shí)也是一個(gè)有關(guān)傳記、回憶錄等紀(jì)實(shí)類文體寫作中是否可以虛構(gòu),傳記寫作者如何表達(dá)自己對(duì)傳主行狀看法的一個(gè)理論性、專業(yè)性的問(wèn)題。丁玲對(duì)沈作最大的不滿,一是來(lái)自沈作中的虛構(gòu)成分,二是其居高臨下的議論顯示的對(duì)革命者思維與行事邏輯的隔膜。由于前者,丁玲說(shuō)沈作是“小說(shuō)”;由于后者,丁玲罵沈從文是“市儈”。前述劉祖春《憂傷的遐思——懷念沈從文》一文寫沈從文拜訪丁玲受到冷遇一段之所以引起當(dāng)事人親屬的不滿,也是因?yàn)檫@段描述其實(shí)并無(wú)可靠的史料依據(jù),作者并未對(duì)之進(jìn)行學(xué)術(shù)性的核實(shí)查證。涉及傳主人際關(guān)系與性格品質(zhì)的重要史實(shí)不能虛構(gòu),這正是傳記與歷史小說(shuō)的重要區(qū)別。沈從文自己也承認(rèn)《記丁玲》有小說(shuō)成分。所以丁玲研究者可以將其作為參考,但不可作為純粹的史料不加旁證地使用。筆者認(rèn)為,《記丁玲》中對(duì)丁玲、胡也頻的議論無(wú)可厚非,因?yàn)樽x者明顯可以看出它代表的僅是沈從文的觀點(diǎn)。革命者與非革命者思維和行為邏輯不同,革命倫理與日常倫理迥異,所以,沈從文與胡也頻丁玲夫婦這對(duì)原先的摯友在思想與事業(yè)上分道揚(yáng)鑣之后,竟都互相覺(jué)得對(duì)方可笑又可憐。感到“可笑”,是從自己的邏輯出發(fā)看對(duì)方;覺(jué)得“可憐”,則既有居高臨下姿態(tài),也與昔日友情分不開(kāi)。
再說(shuō)作者與傳主的關(guān)系與距離
在為涂紹鈞、秦林芳2012年分別撰著的丁玲傳記所寫書評(píng)中,筆者已談及傳記作者與傳主的關(guān)系問(wèn)題。而蔣傳和李傳在這方面較之前二者更具典型性。
作為兒子為母親寫的傳記,作為傳主生平許多重要事件的親歷者乃至直接參與者,蔣傳在史料提供方面具有其他作者所不具備的優(yōu)勢(shì)。它有多處指出其他丁玲傳記或相關(guān)研究論著的史料錯(cuò)誤,甚至包括丁玲自己文章中與史實(shí)不盡符合之處。前述丁玲與瞿秋白關(guān)系即其一例。蔣傳所指證的丁玲本人回憶文章或訪談中與史實(shí)不合之處,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為避免引起猜疑和議論,丁玲故意為之,例如,蔣傳指出《新文學(xué)史料》上的一篇訪談《丁玲談早年生活二三事》中“瞿秋白說(shuō)只有兩個(gè)女子最了解他,能批評(píng)他,一個(gè)是天上的女子王劍虹,一個(gè)是世上的女子楊之華”一句實(shí)際應(yīng)是“只有天上的夢(mèng)可和地上的冰之才有資格批評(píng)他”。這種修改應(yīng)該是丁玲本人的意思。此外,丁玲在散文《冀村之夜》中隱去她自己當(dāng)時(shí)的坦然勇敢行為,則是出于謙虛。蔣傳一概予以還原。另有一些,是丁玲自己記錯(cuò)了,蔣祖林根據(jù)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并尋找旁證(比如相關(guān)的有據(jù)可查的標(biāo)志性事件)予以糾正。這種糾正有的有一定目的,例如蔣傳糾正了丁玲回憶文章中關(guān)于搬到文抗的時(shí)間的說(shuō)法,是因認(rèn)為“可能對(duì)澄清關(guān)于發(fā)表《野百合花》的責(zé)任這一歷史問(wèn)題有點(diǎn)兒意義”;有些則只為澄清史實(shí),并無(wú)他意,例如關(guān)于胡也頻一家三口唯一一張合影上的題字,蔣傳以自己作為照片唯一保存者的身份,說(shuō)明照片背面并無(wú)許多相關(guān)文章中所說(shuō)的題字。
蔣傳在史料方面另外一些值得重視之處,是作者作為丁玲唯一的兒子、作為傳中與傳主相關(guān)的重要人物之一,對(duì)一些重要?dú)v史關(guān)頭個(gè)人見(jiàn)聞與心理的細(xì)致描述。比如丁玲被軟禁在南京時(shí),自己作為一個(gè)剛剛記事的兒童眼中的母親。書中多次出現(xiàn)的母子夜話,很有史料價(jià)值,例如第244頁(yè)寫丁玲告訴兒子當(dāng)年與彭德懷是否有戀情,自己為何沒(méi)有選擇彭德懷。第435頁(yè)寫1955年黨組擴(kuò)大會(huì)首次批判丁玲時(shí)陳明的表現(xiàn),丁玲對(duì)兒子說(shuō)“叔叔黨性強(qiáng)著呢,知道是開(kāi)斗爭(zhēng)我的會(huì)后,他就向電影局黨委提出,他是不是從多福巷搬到電影局去住。后來(lái)沒(méi)有搬出去,但是對(duì)我的情況也不聞不問(wèn),更別說(shuō)出什么主意了”,這雖然不能顛覆此前與此后丁玲與陳明之間的恩愛(ài)關(guān)系,卻從歷史一瞬看出當(dāng)時(shí)壓力之大,以及人的微妙復(fù)雜心理。再結(jié)合后面寫丁玲晚年辦刊時(shí)陳明的“夫人干政”,客觀上投射出繼子與繼父(祖林兄妹一直稱陳明為“叔叔”)之間時(shí)親時(shí)疏的關(guān)系。蔣傳還有一處,寫到丁玲與兒子談及胡家親屬時(shí),“極少用你祖父、你祖母、你幾叔這樣的措辭”,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丁玲對(duì)家族血緣關(guān)系的西方式觀念。有些段落,則可以與李傳相關(guān)段落相互參照來(lái)讀,讓人看到這對(duì)特殊的母與子在特殊年代里的獨(dú)特經(jīng)歷與心路歷程。特別是1957年丁玲被調(diào)查時(shí)蔣祖林被詢問(wèn)的經(jīng)過(guò)及被詢問(wèn)時(shí)的見(jiàn)聞與心理,丁玲被打倒后蔣祖林去蘇聯(lián)前母子告別時(shí)的情景及兒子的心理。第456頁(yè)還寫到自己當(dāng)時(shí)壓下不曾揭發(fā)的母親的一些事。李傳則寫到1958年丁玲在北大荒收到蔣祖林寄自列寧格勒的關(guān)于暫時(shí)斷絕與母親聯(lián)系的信件時(shí),所受到的沉重精神打擊,寫到在絕望中是陳明又給了她溫暖。李傳既寫到了丁玲此時(shí)的感受,又表示了對(duì)蔣祖林的理解。上述這些都是其他不含虛構(gòu)與想象的丁玲傳記所難以寫到并寫好的。
李傳作者之一王增如為丁玲晚年秘書,除了文字資料,她也是丁玲晚年一些事件的親歷者、見(jiàn)證者,同樣具備別人所不具備的位置與距離優(yōu)勢(shì)。然而,與蔣傳相比,李傳具有另外一些特點(diǎn):如果說(shuō)蔣傳采取的是傳中事件親歷者或參與者視角,個(gè)別段落(例如涉及傳記作者蔣祖林本人與母親的關(guān)系部分)甚至有回憶錄的特征,始終洋溢著歌頌革命、懷念母親的濃郁情感,那么李傳的特點(diǎn)是以后來(lái)者眼光審視歷史,既同情地理解革命,又反思革命,以人性視角切入傳中相關(guān)人物與事件,剖析事件來(lái)龍去脈及相互關(guān)系,廣收當(dāng)事各方(包括對(duì)立一方)的資料,盡力作“平情如實(shí)之論”。
以對(duì)丁玲與王實(shí)味及胡風(fēng)關(guān)系的敘述為例。王實(shí)味和胡風(fēng)是20世紀(jì)四五十年代文藝界大批判中受沖擊最大、蒙冤最重的人,總體而言與丁玲冤案不相上下,也可說(shuō)有過(guò)之而無(wú)不及。蔣傳作者也許出于多年政治運(yùn)動(dòng)的陰影以及革命戰(zhàn)士的一貫立場(chǎng)與思維定勢(shì),在述及王、胡二人與丁玲關(guān)系時(shí),給人以盡力淡化的印象。比如通過(guò)糾正丁玲對(duì)搬家到文抗時(shí)間的記憶錯(cuò)誤,說(shuō)明“《野百合花》不是丁玲組稿組來(lái)的,而是王實(shí)味自己送來(lái)的。丁玲與王實(shí)味毫無(wú)交往,而且在丁玲眼里王實(shí)味還算不上是作家”,以求減少其對(duì)發(fā)表王實(shí)味《野百合花》的責(zé)任。而對(duì)于胡風(fēng),則說(shuō)“丁玲與胡風(fēng),也可說(shuō)算是朋友,但不知心,主要是文藝思想方面有較多分歧的緣故”,“丁玲只好同他保持一定的距離”,“胡風(fēng)把她劃為周揚(yáng)一派了”。對(duì)丁玲與蕭軍的關(guān)系,則很少涉及。李傳則說(shuō):“仔細(xì)閱讀就會(huì)發(fā)現(xiàn),丁玲的一些重要觀點(diǎn)與王實(shí)味是相通的”,并通過(guò)對(duì)丁玲當(dāng)時(shí)觀點(diǎn)的分析得出結(jié)論:“這也就不難理解丁玲為什么要簽發(fā)《野百合花》了。”李傳引用黎辛和黃昌勇的文章,說(shuō)明丁玲將發(fā)表此文的全部責(zé)任擔(dān)起來(lái),自有其道理。對(duì)于丁玲與胡風(fēng)的關(guān)系,李傳專列一節(jié),說(shuō)二人友誼可追溯到1932年底,說(shuō)1949年1月28日“胡風(fēng)在丁玲家談了一天”,后來(lái)“胡風(fēng)在沈陽(yáng)停留不到30天,與丁玲長(zhǎng)談近10次,每次少則兩三小時(shí),多則整日長(zhǎng)談”,“他們一定是深層次的談話,丁玲會(huì)把不輕易示人的意見(jiàn)也和盤托出”,“正是這些談話,確定了二人的密切關(guān)系”。李傳還引用在胡風(fēng)被整、丁玲走紅,二人開(kāi)始分道揚(yáng)鑣的1950年元旦胡風(fēng)致妻子梅志的信:“在這當(dāng)局文壇,她還是一個(gè)可以不存戒心談?wù)劦娜恕!痹谕砟辏×徇€在與習(xí)仲勛談話時(shí)為胡風(fēng)徹底平反呼吁。李傳寫延安時(shí)期丁玲與蕭軍的交往用墨頗多,并引用蕭軍日記,寫出了兩人非同一般的友誼以及后來(lái)的分歧絕交、絕交之后又互相同情。
李傳的史料來(lái)源,除了丁玲自己的文章、晚年談話錄音、作者親眼見(jiàn)證,也有許多別的一手資料,包括當(dāng)事各方的日記、書信、回憶文章,以及對(duì)各方人物的訪談。這樣,給人的感覺(jué)是盡量對(duì)矛盾各方予以“同情之理解”,認(rèn)識(shí)到歷史的復(fù)雜性、事件的復(fù)雜性、人的復(fù)雜性。然而,李傳也并非沒(méi)有立場(chǎng)、沒(méi)有價(jià)值判斷。在對(duì)各種丁玲傳記都會(huì)大書特書的丁玲與周揚(yáng)恩怨方面,李傳不同于其他傳記,不僅寫到周揚(yáng)偶爾也流露出一點(diǎn)歉意,還特別寫到,1979年11月6日下午,在丁玲大會(huì)發(fā)言的前兩天,周揚(yáng)曾去木樨地丁玲家中拜訪,但不巧丁玲不在家。李傳認(rèn)為“他一定是為丁玲而來(lái)”,“此來(lái)很可能是遵照胡耀邦講話精神,想取得丁玲諒解”,感嘆“歷史不給他們一個(gè)機(jī)會(huì),否則可能就沒(méi)有丁玲兩天后鋒利潑辣的大會(huì)發(fā)言,可能他們后來(lái)的關(guān)系就是另外一個(gè)樣子”,但又認(rèn)為:“但如果周揚(yáng)事先打個(gè)電話,丁玲決不會(huì)不在,所以,周揚(yáng)究竟有幾分誠(chéng)意又值得懷疑。”個(gè)人與歷史、與社會(huì)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問(wèn)題,一直是哲學(xué)和歷史學(xué)界關(guān)注的問(wèn)題。個(gè)人固然受環(huán)境制約,但人的個(gè)性和品格,還是有很大不同。這也會(huì)或多或少影響歷史的走向與進(jìn)程。
李傳寫到了丁玲對(duì)革命邏輯、革命倫理的理解,他引用丁玲給兒子的信:“一個(gè)大的運(yùn)動(dòng),一個(gè)大革命的進(jìn)程中,總會(huì)有某些人吃了一點(diǎn)苦頭,某些人沾了一點(diǎn)便宜”,“把這些作為革命,特別是革命前進(jìn)中的不可避免的現(xiàn)象去看,就沒(méi)有什么憤憤不平,就沒(méi)有什么可以埋怨的了。”由于采取了人性視角,李傳給人的感覺(jué)是既同情地理解革命,又反思革命中的人性變異。關(guān)于丁玲晚年的表現(xiàn),李傳既寫出丁玲革命信仰的真誠(chéng)性、堅(jiān)定性,也揭示其個(gè)人切身處境的因素,說(shuō)明丁玲令外國(guó)人失望的訪美言論,雖然不是“表演”,確也有“防身”考慮,并引用丁玲致宋謀玚的信予以佐證。此外,李傳還以作者之一王增如的親歷,寫到晚年丁玲面對(duì)死亡時(shí)各種細(xì)膩的生命感受與體驗(yàn),這些也是其他丁玲傳記所不太涉及的。
蔣祖林與李向東、王增如夫婦所寫的兩部丁玲傳記,都是以一手材料見(jiàn)長(zhǎng)、且互不可取代的著作。參照來(lái)讀,當(dāng)有更多收獲。

晚年丁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