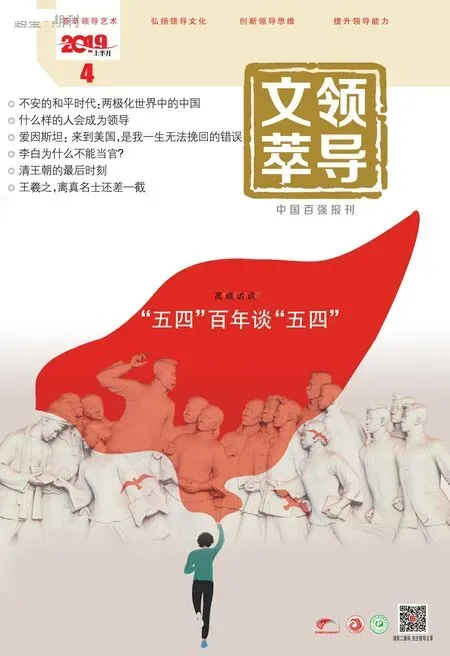智伯的覆亡
張國剛
誰來接班

晉國是春秋時的大國,晉獻公(前677年—前651年在位)時崛起,晉文公重耳(前636年—前628年在位)時稱霸,其霸主地位一直延續到了晉悼公(前573年一前558年在位)時期。事實上,自從晉文公作三軍設六卿起,六卿一直把握著晉國的軍政大權。隨著晉國的國君平庸、六卿(即范氏、中行氏、智氏、趙氏、魏氏、韓氏六家)坐大,晉國內部的分裂日趨嚴重。到了晉定公(前511年—前474年在位)時,六卿中的范氏、中行氏已被瓜分消滅,晉國還剩下智氏、趙氏、魏氏、韓氏四卿。
這就是三家分晉的歷史背景。《資治通鑒》從此講起,說的第一件事就是選拔接班人的問題。
“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后。”《資治通鑒》習慣用“初”這個字開頭,交代背景。智氏家族說一不二的大家長智宣子,決定選嫡子智瑤為嗣卿。族人智果反對說,智瑤雖有“美鬢高大,騎射兼通,才藝超群,善辯能文,強毅果決”這“五賢”,卻有一個最大的弱點“不仁”——為人刻薄寡恩,不懂籠絡人心。智果認為,如果不能施政以仁,而是自恃“五賢”強勢治國,就不可能獲得臣民心悅誠服的擁戴。但智宣子根本聽不進勸,因為立嫡以長,是周公滅商后定下的宗法制度。這個制度違背“選賢與能”的原則,但是有利于政局穩定。
與此同時,趙氏家族也在考慮嗣卿人選。趙簡子兩個兒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究竟立誰為后?趙簡子打算考考他們。他把兩支寫著“訓誡之辭”的竹簡,分別交到兩個兒子手上,叮囑他們保管好竹簡并把上面的話牢記在心。3年后,趙簡子問他們,是否還記得竹簡上的話。大兒子伯魯忘得精光,竹簡也找不到了。小兒子無恤卻背得滾瓜爛熟,竹簡就藏在隨身的衣袖里。“于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后。”顯然,趙無恤的謹慎、謙卑、細心,讓父親決定立他為接班人。趙無恤就是趙襄子。
這個故事說明,趙簡子在立嫡和立賢問題上,選擇了后者,沒有拘泥于周制中選立嫡長子的傳統做法。
何物可依靠
公元前475年,晉定公和正卿趙簡子先后去世,按照晉國的制度,智瑤登上了第一執政的寶座,世稱智襄子或智伯。
智伯處事強霸,多次想入侵他國。據《戰國策·宋衛》記載,智伯想吞并衛國,就先贈以“駿馬四、白壁一”來麻痹對方,但未能見效;后來又假裝太子出逃,盛兵護衛著太子向衛國方向馳去,也沒能得逞。
不久,智伯以攻打越國的名義籌措軍費,率先將智氏的一個萬戶城邑獻與晉國國君后,也要韓氏家族獻出一座城邑。韓康子不同意,輔臣段規卻建議他答應智伯的要求,把禍水外引。段規認為,倘若智伯得寸進尺,再把矛頭指向他人,我們就可以靜觀其變。韓康子覺得有道理,就給了智伯一座萬戶的城邑。
智伯繼而向魏桓子索要土地。魏桓子第一反應也是覺得智氏欺人太甚,想要拒絕。可他的輔臣任章建議采用“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的驕兵之策,麻痹智氏,并暗中結交利害攸關的盟友,共同對付智伯。老謀深算的魏桓子明白了任章的意思,痛快地給智氏送了一座萬戶之邑。
志得意滿的智伯,進而又逼迫趙襄子獻出蔡、高狼等封地。這次他終于踢到了鐵板,遭到了趙氏的堅決抵制。于是智伯帶上韓、魏的軍隊一起攻打趙氏。
面對氣勢洶洶的智氏聯軍,趙襄子有3個戰略要地可以避難:長子、邯鄲、晉陽。長子城高池深,邯鄲糧草豐足,但是趙襄子都不去——城高池深,說明老百姓的徭役繁重;糧草豐足,說明老百姓的賦稅沉重。這些有什么可依恃的?只有尹鐸治理的晉陽輕徭薄賦,百姓的人心最可依賴。思索再三,趙襄子最終選擇了晉陽作為自己抗擊聯軍的根據地。
當趙襄子逃奔晉陽后,智伯率領三家聯軍把晉陽城圍得水泄不通,甚至決汾水以灌城。晉陽 城被圍了兩年,但晉陽軍民始終同仇敵愾,毫不動搖,“沉灶產蛙,民無叛意”。而就在此時,智伯犯了兩個致命的錯誤:傲慢霸道和剛愎自用。
一天,智伯與魏恒子、韓康子一起乘車巡視攻城。智伯坐在最尊貴的左側位置,魏桓子在中間駕車,韓康子在右側拿著武器護衛。三位卿大夫都是主君,關系卻如此不平等。不僅如此,威風十足的智伯還傲慢地說:“我今日才知大水足以亡人國。”這話引起了兩個盟友的憂慮,“汾水可以灌(魏都)安邑,絳水可以灌(韓都)平陽也”。貪婪的智伯滅了趙氏后,能放過韓魏嗎?
魏、韓二子的憂慮,很快被智伯的謀士絺(音同吃)疵察覺到了。他提醒主公,魏韓必反!智伯疑惑地問,你是怎么知道的?絺疵回答,從人情事理即可推知!晉陽城破在即,二子不僅沒有喜色,反而憂心忡忡,不就是擔心唇亡齒寒,趙氏亡,下必及于韓魏嗎?
次日,智伯以此質問魏桓子和韓康子。二子矢口否認,說一定是有人充當趙氏的說客,離間我們的關系,想讓您懷疑我們而放松了對趙氏的攻擊。我們都盼望早日分享趙氏的田土呢,怎么會去做危險的傻事冒犯您呢?智伯相信了二子的辯解,沒有絲毫戒備。
事后,絺疵質問智伯,主公怎么把我的話告訴二子了?智伯說,先生怎么知道?絺疵說,剛才他們出去的時候,迎面狠盯了我一眼,就匆匆離去,我猜一定是他們發現我讀懂了他們的心思。智伯聽后并未理會絺疵的分析。
此時,坐困圍城的趙襄子決定反擊。他秘密派人出城,游說韓魏兩家。三家一拍即合,約定日期,采取聯合行動,反攻智氏。
公元前453年的一天夜里,趙襄子突然對岸上軍隊發動反擊,并掘開水壩,倒灌智氏駐軍營地。智伯的軍隊因為救水而大亂。韓魏兩軍趁機從側翼進擊,趙軍從正面猛攻,大敗智氏軍隊。智伯被殺,智氏家族滅亡,三家盡分其田土。50年后,周天子正式封魏趙韓三家為諸侯。此后,三家又瓜分了晉國公室,春秋五霸之一的晉國滅亡,戰國七雄中的韓、趙、魏三國產生。“三家分晉”成了中國春秋時代與戰國時代的分界點。
警示誰來聽
司馬光結合智伯之死,對領導人的德和才的問題發了一通議論。他認為領導人的德比才重要,甚至認為寧可用無德無才的愚人,也不能用有才無德的小人。這里不無激憤之詞。從今天的角度來看,與領導者個人的道德修養相比,制度對權力的約束才更為根本。但在制度約束的前提下,選擇什么人當接班人,其人品高下仍舊至關重要。
司馬光對于領導者的修煉有過很系統的看法。宋神宗治平四年(1067年),司馬光上疏提到“人君修心治國之要”,把“仁”排在了第一位。“仁”就是要講政治,并善于把政治理想濡化為社會共識,同時還得發展生產,重視民生,這樣才能得到百姓的擁戴。智伯利令智昏,貪得無厭,不仁之名,當之無愧!如果進一步追問,是否魏趙韓三家就不貪婪,比智氏更“仁德”?恐怕也不盡然。但趙襄子懂得,與城池、物資等條件相比,人心擁戴才是最可靠的保障。他比智伯更懂政治。
智伯的問題,在他被選為接班人時,就已經暴露出來了。他的“五賢”在古人看來并不是人君最重要的本事。《荀子·王霸篇》說:“人主者,以官人(即用人,安排好人才的職官)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智伯的本事屬于“自能”。唐人趙蕤的《反經》在引用荀卿這段話時,提升到人君“大體”的高度。領導者關鍵的本事在于識大體(懂政治),善用人。智伯狂妄霸道,誤判形勢,輕視對手;決策上不明是非,不聽謀士正確的諫言,都是領導者的大忌。與智伯的粗疏相反,趙襄子在被父親選為接班人時,就表現出過人的精明和細致。此外,智伯外交上也犯了錯誤。言語不謹慎,行為太張揚,引起盟友的疑忌,致使“統一戰線”霎時解體,把三對一的優勢,變成了一比三的劣勢,焉能不敗!
《資治通鑒》是給領導者看的書。以三家分晉為開始,作者是想要提醒讀者必須重視一個問題:怎么帶隊伍,怎么管理團隊。智伯就是一個典型的反面例證。
(摘自《環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