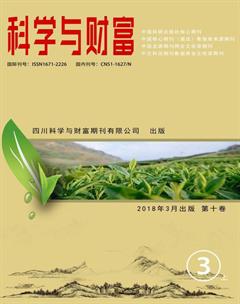滑稽與崇高的統一
王霜
摘 要:《堂吉訶德》是一部世界級的經典小說,其主要人物堂吉訶德具有雙重性,既是滑稽的,又是崇高的。滑稽與崇高是兩個對立的美學概念,在《堂吉訶德》中它們相互統一,這部作品同樣具有雙重性,本文從下面幾個方面進行論述:一、語言造就的喜劇性;二、喜劇中展現的悲劇性;三、悲、喜的統一。
關鍵詞:《堂吉訶德》;悲劇性;喜劇性
《堂吉訶德》被譽為歐洲“近代小說的開山之作”,小說主要描寫了西班牙拉曼·卻的一個窮鄉紳吉哈諾與農民桑丘?潘沙的游俠史。它塑造了一個看似荒誕不經的騎士形象,但它并不僅僅是一部諷刺騎士文學的小說,騎士堂吉訶德擁有滑稽與崇高的統一特性,而作品本身同樣具有喜劇性和悲劇性這樣的雙重特性。
一、語言造就的喜劇性
《堂吉訶德》中的語言具有鮮明的特點,既有古典藝術的審美,又吸取民間藝術的養分,形成了它獨有的時而莊重時而詼諧的語言風格。
小說語言有著陌生化的特點,“陌生化”強調的是在內容與形式上違反常規常識,產生語言理解與感受上的陌生感,同時在藝術上超越常規常識。小說語言的陌生化,就是小說語言在使用時換了一種說法,用陌生來展示熟悉,不采用大多數人熟悉的固定模式,突破常規語法規范的限制和束縛,重新構造語言的表現形式,給人以審美上新穎、強烈的刺激,引起人們深入的思考與探究,促使人們充分領略作品主題。《堂吉訶德》中占據大量篇幅的騎士小說的對話就給人帶來這樣陌生化的感受,堂吉訶德將騎士小說里的對白放入與故事情節不相符的現實環境,語言與現實的不相符形成一種荒謬感,比如堂吉訶德受傷后的自我安慰,想起他書上讀過的情景,“他覺得那情節與自己的處境恰好相似,就在地上打滾,好像疼痛得厲害,一邊有氣無力地背誦那位綠林騎士受傷的話” 。他讓自己的行為符合騎士小說里的情節,以此認可自己的所作的是騎士行為。堂吉訶德在故事中經常以騎士小說的語言來進行對話,對話雙方牛頭不對馬嘴,這種不對等的語言給人帶來陌生化的感受,達到一種荒誕喜劇的效果。
小說語言對人物行為細致的展現,尤其是當人物行為不能達到有效的結果時,形成的反差帶來喜劇效果。在堂吉訶德第一次出游到達旅店他吃飯時的細節,“他吃東西的樣子實在令人發笑。他戴著頭盔,掀起護眼罩,拿了東西吃不到嘴,得別人把東西送進他嘴里去。一個姑娘就在干這件事。可是要喂他喝卻沒辦法。這還多虧店主,他通了一根蘆葦,把一頭插在他的嘴里,從另一頭灌酒進去。種種麻煩他都能耐心忍受,只要不隔斷他系住頭盔的帶子。” 這將吃飯時的繁瑣展現,可是堂吉訶德仍愿意忍受,只要維持住他騎士的“外表”。
堂吉訶德的行為充滿著夸張化,他就像是舞臺上的表演者,一舉一動都有著喜劇的效果。他想要成為一名游俠騎士,他裝備上作為一名騎士應有的東西,但盔甲是祖傳的,頭盔是鐵皮做的,馬是瘦弱的,名字是新取的,情人是幻想的。在小說中這段出游前的準備有著細致的描寫,精心的準備與簡陋的成果形成鮮明的對比,更是增加了喜劇的效果。
二、喜劇中展現悲劇性
《堂吉訶德》的悲劇性是通過喜劇性展現的,亞里士多德對悲劇的定義是“悲劇是對于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語言,具有各種悅耳之音,分別在劇中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動作來表達,而不是采取敘述法;借引起憐憫與恐懼來使這種情感得到陶冶。” 堂吉訶德的行動是有著“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模仿”和“引起憐憫與恐懼”這兩個特性,他對于騎士小說的模仿,他的行動引人發笑的同時令人可悲。
拜倫有過這樣的評論“《堂吉訶德》是一個令人傷感的故事,它越是令人發笑,則越使人感到難過。這位英雄是主持正義的,制伏惡棍是他的唯一宗旨。而正是那些美德使他發了瘋!”堂吉訶德踐行著騎士道的準則,主動救助牧童,呵斥他的主人,卻導致了牧童被再次抽打。他想要商人承認他的意中人是絕世美人,雙方產生矛盾,導致他被打,他的“正義”行為為他人、為自己帶來的災難,到最后他悔悟,告訴他的侄女不要嫁給看騎士小說的人。
整部小說中堂吉訶德可以分為不清醒與清醒這兩個狀態。在不清醒的狀態下,他以騎士道的形式展現人文主義的關懷,他的行為、語言模仿著騎士小說所宣揚的東西,在二次出游中堂吉訶德與風車對戰,在他的眼中那不是風車,而是巨人,這是可笑的。堂吉訶德與巨人對抗,他被卷到空中,摔倒地上,可是他勇敢地站起來繼續戰斗,他的英勇由此展現,在文中有許多這樣的橋段,在喜劇的場景里,他荒誕行為中暗含著騎士精神的本質。他是瘋癲的,他看到的是他幻想中產物;他是清醒的,他看到的是世人看不見場景。他看到許多的社會現狀,對于這些現狀世人習以為常,而堂吉訶德勇敢地站出來,反抗斗爭,因此在世人眼中他的行為是荒誕的,語言是癲狂的,從而形成了喜劇的效果,悲劇的內涵。清醒狀態的他,宣揚先進的人文主義思想,“他的頭腦各方面都很清楚、穩健,所以只要不提騎士道,誰都認為他的見識高明”。他對人的自由價值和尊嚴予以充分的肯定,“認為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的人當奴隸未免殘酷”;強調人都應當“一心向往美德,以品行高尚為榮”,因為“血統是從上代傳襲的,美德是自己培養的,美德有本身的價值”;肯定人的感情,認為每個人都具有追求純潔愛情和幸福生活的權利。 他向往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在三次出游中,他從貧窮凄寒的鄉村到賬亂的城市,從偏僻的小客店到豪華的公爵城堡,從人流不息的大路到幽靜的森林,接觸不同階層人物,也觸及到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法律、道德、文化和風尚習俗等方面。
他清醒時行為中含有騎士精神,宣揚平等的思想,渴望建立新的疆土;不清醒時踐行著騎士精神的形式。他的兩種狀態都是社會中所不接受的存在,他受到人文主義的影響,與社會現實的思想相背離,超前的精神與落后環境之間的產生沖突,產生了喜劇的行為,造就了整部作品的悲劇性。
三、悲、喜的統一
小說中有大量的對比,個人的,如堂吉訶德年老的身軀里與年輕的思維的對比;人與人之間的,堂吉訶德與桑丘?潘沙,他們的外表形象和思想性格都是鮮明的對比;各種因素間的對比,理智與癲狂、幻想與現實、悲劇與喜劇等。它們緊密的交織在一起,形成矛盾與對立,在對立中統一于一人或一物上。正因為喜劇和悲劇、滑稽和崇高、可笑和可愛存在于堂吉訶德身上,他所引發的笑,成為一種“含淚的笑”,一種發人深省的笑。當主體的崇高受到主體的滑稽的沖擊和否定時,喜劇中就不可避免地滲透了悲劇因素,《堂吉訶德》就是如此。
塞萬提斯將堂吉訶德性格中悲劇性用喜劇形式表現出來,使情理之中的悲劇結果在意料之外的喜劇狀態中逐步完成。《堂吉訶德》整部作品是悲劇性與喜劇性的交融,獨特的語言將喜劇效果展現,而在喜劇中凸顯其悲劇色彩。
參考文獻:
[1] [西班牙]塞萬提斯:《堂吉訶德》,楊絳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第2版。
[2] 鄭克魯,蔣承勇:《外國文學史(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3] 姬文紅:《悲劇與喜劇的完美結合——論<堂吉訶德>》人物性格的塑造,《電影文學》2011年第11期。
[4] 張方方,張維青:《喜劇姿態與悲劇精神——<阿Q正傳>與<堂吉訶德>之分析比較》,《濟寧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03年第06期。
[5] 王驍勇:《透過<堂?吉訶德>看<慳吝人>——莫里哀喜劇人物悲劇化手法探源》,《甘肅高師學報》2000年第6期。
[6] 趙淼:《英雄堂吉訶德的隕落——<堂吉訶德>中悲劇與滑稽的對立統一》,《名作欣賞》2015年第24期。
[7] 邱紫華,《<堂吉訶德>的喜劇美學特征》,《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