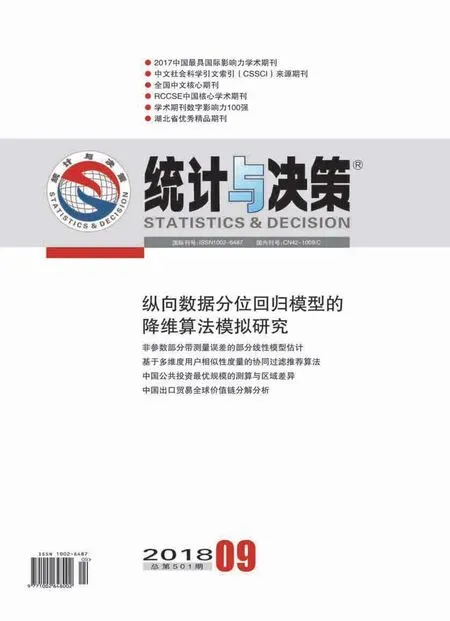市場轉移與經濟地理:一般化的要素流動空間經濟模型
梁 涵
(中國政法大學 商學院,北京100088)
0 引言
收入遣返是要素流動過程中極為常見的現象。現實經濟中,勞動力和資本流動是最主要的要素流動現象,源于這兩類要素流動的收入遣返現象在區域和國際經濟層面上都備受關注。其中,遷移勞動力的收入遣返現象在國內外都十分普遍。在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流動過程中,收入遣返過程會引發市場的后向關聯作用,對空間經濟演化產生重要的影響。但是,在空間經濟學中,由克魯格曼“中心-外圍”模型[1]發展出的要素流動系列模型[2]只研究了收入遣返的兩種極端情形,即完全不存在收入遣返的自由企業家模型[3]和收入完全遣返的自由資本模型[4],該理論至今仍未能系統揭示收入遣返的作用機制。從空間經濟的角度,廣泛存在的收入遣返現象顯示,伴隨要素流動的市場轉移往往很不完全。這種源自于市場轉移的不完全性引發的空間經濟效應是本文分析的重點。
強調異質性的“新新貿易理論”[5]由于僅設定了空間不能流動的勞動力為唯一要素,難以揭示基于要素及其受益主體空間流動所產生的空間影響機制。在新貿易理論領域,Takahashi等(2013)[6]構建的單部門FC模型重新審視空間可流動的資本因素對空間經濟的重大影響。該模型在單個制造業部門的經濟設定下,引入國際間可自由流動的資本要素,演繹了與貿易成本呈倒U形關系的內生決定的均衡工資,并得出Helpman等(1985)[7]所揭示的三類本地市場效應能夠在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下共存的重要結論,然而,該研究設定可流動的資本要素將收入完全遣返,仍然沒有脫離傳統自由資本模型忽視收入遣返的空間影響機制的局限。本文不僅系統闡釋了收入遣返與空間經濟的相互作用機制,還揭示了空間貿易成本和收入遣返程度在促成空間經濟形成集聚或分散格局方面具有替代性,即空間經濟維持在集聚格局或突破對稱格局的條件,既可以是貿易成本很低,也可以是收入遣返程度很低。這一結論為空間經濟理論框架中的“空間經濟一體化”提供了新的機制。
1 流動要素模型
空間經濟體由兩區域、兩部門和兩要素構成。兩區域(地區1和地區2)對稱,即兩地居民偏好、生產技術、要素稟賦、區際貿易開放度等屬性相同,本地和異地流動要素的市場進入性無差異。兩部門按習慣采用農業部門(A)和制造業部門(M),農業部門指代生產均質產品,采用規模報酬不變技術,面臨完全競爭市場的部門;制造業部門指代生產水平差別化產品,采用規模報酬遞增技術,面臨壟斷競爭市場的部門。除了制成品區際貿易存在成本外,各地區內部貿易及農產品區際貿易成本均為零。兩要素指生產中的固定投入要素和可變投入要素,固定投入要素也是區際自由流動要素(F),僅運用于制造業部門,模型為流動要素增加了“來源地”/“注冊地”屬性;可變投入要素假定不能區際流動,可在兩部門間自由轉換,按空間經濟學習慣稱其為普通勞動力(L)。設Fw為兩地區流動要素總量,F1和F2分別表示注冊地在地區1和地區2的流動要素量;Lw,L1和L2分別表示全局,地區1和地區2的普通勞動力稟賦。兩地區要素對稱,因此F1=F2=Fw2,L1=L2=Lw2。此外,為了區別流動要素的注冊地和使用地,設n1和n2分別為地區1和地區2的產品種類數。
1.1 經濟主體行為
(1)消費者。兩地區居民偏好無差異,地區r(r=1,2)的代表性消費者的效用為:

其中,Ar為農產品消費量;Mr為制成品的復合消費集,由不變替代彈性子效用函數表示,顯示了居民對制成品具有Dixit-Stiglitz形式的多樣化偏好[5];mr()i為對第i種制成品的消費量。居民消費支出中制成品所占的比重由常數μ表示;任意兩類制成品之間的替代彈性均相同,由常數σ表示。
設農產品價格為,第i種制成品的價格為pr(i)。當消費者在地區r的支出為er時,其預算約束為·Ar+效用最大化下,其消費束為A=r中,價格指數為:

這一支出額產生的消費者間接效用值為:

制成品存在區際貿易成本,且區際對稱。本模型采用“冰山”交易成本,即為了確保將1單位產品運抵異地,需要從本地出廠τ單位(τ>1)。τ越大,貿易成本越高。因此,地區r的產品在異地市場的價格為τpr(i)。設?≡τ1-σ∈(0 ,1],因其與衡量貿易成本的指標τ負相關,被定義為貿易自由度[2]。產品i的市場總需求為兩地區居民消費量mr(i)之和,即:

其中,Er和Ek分別為地區r和k的消費支出總額。
(2)生產者。生產主體包括農業部門和制造業部門的生產者。假定兩地區農業生產均滿足非專業化條件①非專業化(NFS,non-full-specialization),指每個地區的最大農業產能都小于兩地區對農產品總需求,由此確保兩個地區總存在農業部門。,最優化決策下,農產品價格等于邊際成本,即=aA,其中aA為單位產出的普通勞動力投入量,為地區r的勞動力工資。通過選擇產出單位可將aA標準化為1。將農產品選為計價物,且其貿易成本已假定為零,可以得到====1。
制成品部門廠商完全對稱。單個廠商規模經濟足夠大,使得每種產品只會在一個地區的一家廠商生產。通過選擇固定投入單位,將廠商投入的固定要素量標準化為1單位,因此n1+n2=Fw。普通勞動力可以在部門間自由轉換,制成品部門勞動力工資與農業部門相同,均為=1。地區r廠商i的成本函數可表示為π(i)+x(i)·rr,其中aM為勞動力邊際投入系數,πr(i)為支付固定投入的費用,也即流動要素價格,xr(i)為產量。
1.2 市場轉移指數
現實經濟中,流動要素的收入流與其支出流往往存在空間不匹配,例如流動要素的部分所有者并未隨要素流動而遷移時,會出現“收入遣返”現象,需求市場轉移程度低于要素流動程度。對此,本文設定“市場轉移指數”θ,即流動要素利得者將收入用于要素投產地(相對于要素注冊地或遷出地而言)的比重,以此衡量要素流動帶動的市場轉移程度,或者說空間經濟中市場轉移與產業遷移的同步程度。該指數對市場的空間分布具有重要影響。本文假定兩地區市場轉移指數完全對稱。
θ值越大,說明市場隨要素流動的轉移程度越顯著。當要素流動到異地時,該要素收入中的θ部分在要素投產地支出,只有1-θ部分“遣返”回到注冊地支出。空間經濟理論中的FC和FE模型是本模型的兩個特例。FC模型中自由流動的金融資本無論投入哪個地方,其收益總是完全“遣返”回資本“注冊”地,即θ=0。FE模型中,自由流動的企業家在要素投產地居住,其收入全部在投產地支出,即θ=1。考慮到現實中流動要素所有者的支出空間分布可以是以上兩種極端之間的任意情形,有必要在空間經濟模型中納入能夠連續變化的市場轉移指數,而此后的分析結構將顯示市場轉移程度同樣能夠引發空間經濟格局的“災變性”突變,由此反映出該指標對于空間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價值。
模型假定了兩地區流動要素稟賦和投資準入性完全對稱,即兩地區注冊的流動要素規模相同,對流動要素所有者的信息公開和可進入性都是完全相同的,使本地和外地投資者的機會可得性無差異。因此可以推斷每個地區投產的流動要素中,注冊地為本地和外地的將各占一半。通過選擇制成品連續統單位,標準化N=1,由此得到n1+n2=1和F1=F2=1 2。
2 短期均衡
空間經濟學一般假定各地區內部市場的調整節奏遠遠快于區際要素市場的調整節奏,由此將均衡分析劃分為短期和長期。本文首先進行短期均衡分析,著眼于廠商區域分布給定,即n1和n2固定不變的情況下,兩地區內部的經濟均衡。然后在長期均衡分析中將進一步納入流動要素市場,從而得到完整的空間一般均衡結果。
因為廠商完全對稱,均衡分析中不妨采用代表性廠商,省略表示類型的標記“(i)”,同時此后的內生變量均指經濟主體的最優化結果。壟斷競爭市場結構下,單個廠商對制成品行業價格指數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②空間經濟模型默認廠商數量眾多,使得單個廠商的定價無法影響地區價格指數。但實際上只要是廠商數量有限的情況下,單個廠商的定價仍然會對整個市場和其它廠商影響[6]。。由式(3)可得制成品需求的價格彈性為σ,廠商采用壟斷加成定價pr=σ·aM(σ-1),選擇制成品產出單位,使aM=(σ-1),從而標準化制成品價格pr=1;同時,廠商可自由進出使得每個廠商的經濟利潤耗散為零,即πr=(pr-aM)xr=。由此可知,代表性廠商固定投入費用占銷售額的比重為1σ。設全局總支出為Ew,制成品部門的銷售額為μEw,其中支付固定投入費用為;總支出中的剩余部分為普通勞動力要素的總收益,即(1 -)Ew=Lw。結合市場出清條件xr=Dr,以及式(1)和式(3),可以得到均衡時的價格指數Pr和流動要素價格πr:

空間經濟均衡本質上是支出分布與廠商分布相互作用的結果,從式(4)中流動要素價格表達式即可見一斑。本文引入的市場轉移指數θ,反映了支出市場與產業遷移的同步程度,對空間經濟均衡具有重要影響,也彌補了以往研究所忽略的支出市場分布隨產業移動變化(即廠商或要素區際分布變動)的影響機制。地區r的消費市場支出構成中除了普通勞動力的收入(1 -μ σ)Ew外,還包括三部分:為本地注冊和投產的可流動要素的收入;為本地注冊外地投產的外流要素遣返回來的收入;為外地注冊本地投產的要素在本地的支出。由此可得:

將式(5)中的E1和E2代入式(4)中的 π1和 π2,求解關于 π1和 π2的二元一次方程組,并利用Ew=Lw/(1 -得到:

進而得到兩地區流動要素名義收益的差值:

式(7)顯示了兩地區間流動要素價格差異與廠商數量差異存在以下兩個關聯關系:

式(8)說明當貿易自由度(?)或者市場轉移指數(θ)較高時,產業集聚區(廠商數量大的地區)流動要素的名義價格相對更高;反之,?或θ較低時,集聚區流動要素價格則相對較低。因此,市場轉移類似于貿易一體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空間經濟集聚。式(9)進一步顯示上述對空間集聚力的正向促進作用,即市場轉移程度的提升總是促進集聚區流動要素價格的相對上升。
3 長期均衡
流動要素的區位選擇最終決定于該要素所有者所獲得的間接效用水平。當要素流動到異地且收入轉移并不完全(即θ∈(0 ,1))時,可支配收入轉化成的消費支出將分布在兩個地區,需要對兩部分支出所產生的效用進行加總。對于注冊地為r,在本地投產的流動要素,其所有者間接效用值記為,在外地投產的則記為(r≠k)。由式(2)可得:

在滿足靜態預期(static expectations)和二次調整成本(quadratic adjustment cost)的空間經濟假設條件下,流動要素區位決策的中心目標是獲得最大的瞬時間接效用。長期均衡分析基于遷移方程確定流動要素的區位調整趨向和停止狀態。不妨將遷移方程設置如下:

其中,s˙r表示注冊地為r的流動要素在本地和異地生產的間接效用差。當s˙r>0時,r地的流動要素呈現出回流本地的態勢,反之,s˙r<0 時則出現要素外流。s˙r=0 時要素流動停止,空間經濟格局處于固定(steady state)均衡,在沒有外來擾動時,這一格局不再隨時間變遷而改變,本模型中均衡格局包括分散和完全集聚兩類。進一步還需要判斷上述均衡的穩定性。當較小的外來擾動使空間經濟偏離既定均衡后,能夠通過自反饋過程重新回歸原均衡的狀態稱為穩定(stable)均衡,否則,為不穩定均衡。具體而言,完全集聚格局為穩定均衡的充要條件是:對于地區r和k(r,k=1,2且r≠k),在nr=1和nk=0格局下:

分散格局為穩定均衡的充要條件是:在nr∈(0 ,1) 下,對地區r=1,2均滿足:

定義以下有關支撐點(均衡由完全集聚突變為分散的臨界點)的函數(13)和有關突破點(均衡由分散突變為完全集聚的臨界點)的函數(14):
利用均衡穩定條件(11)和(12),可以得到以下長期均衡結論:
定理1:初始完全對稱的兩區域空間經濟體的穩定均衡狀態包括完全集聚和對稱分散兩類,各自出現的條件如下:
(1)當?和θ均較大,使得B(?,θ)>0時,穩定均衡為完全集聚狀態;
(2)當?和θ均較小,使得S(?,θ)<0時,穩定均衡為對稱分散狀態;
(3)當?和θ均處于中等水平,使得B(?,θ)<0<S(?,θ)時,穩定均衡為可能為完全集聚狀態,也可能為對稱分散狀態。

圖1 市場轉移指數θ和貿易自由度?綜合作用下的空間經濟均衡分界示意圖

圖2 市場轉移影響下的空間經濟“戰斧”圖
圖1是對定理1的直觀示意。克魯格曼(1991)揭示了空間經濟格局與貿易自由度之間存在“戰斧”形態的關聯關系。從定理1和圖1也可以觀測到這一關聯關系。不僅如此,上述結果還進一步揭示市場轉移程度對空間經濟格局具有同樣重要的影響。圖2的戰斧圖中的突破點θB(?)和支撐點θS(?)分別是B(θ,?)=0和B(θ,?)=0的解。市場轉移程度較低時,空間經濟中集聚力相對較弱,呈現穩定的分散均衡格局;轉移程度較高時,則集聚力占據主導,并呈現為中心-外圍的完全集聚格局;轉移程度處于中等水平時,則會出現多重均衡的情況,初始狀態或外部沖擊強度等成為左右經濟均衡格局的重要“歷史”因素。當市場轉移程度不斷變遷,經過突破點和支撐點附近時,空間經濟將經歷劇烈突變的均衡轉換。由此可見,對于空間經濟的重要現象“突變”,已經不再是貿易自由度的“獨角戲”。而且兩種因素的復合影響,圖1進一步揭示,在區際貿易一體化不斷深化的進程中,市場轉移程度提升將更快地推動空間經濟邁向集聚;反之,市場轉移程度下降,則可以抵消一體化對空間經濟集聚的影響,甚至使得分散力占據主導。例如在中國快速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人口半城鎮化現象,導致市場轉移程度處于較低水平,降低了城鄉一體化對經濟效率的促進作用,浪費了推進一體化投入的寶貴資源。
4 總結

本文通過引入衡量收入遣返程度的指數,構建了一個一般化的流動要素模型,將此前相互獨立的FC和FE模型變成為同一模型框架下的兩個特例;同時,通過可解析的均衡分析,揭示收入遣返程度下降能夠增強異質品部門的空間集聚力。對于空間經濟長期穩定狀態,收入遣返指數同樣呈現出戰斧形態的影響機制,能夠產生“災變性”影響和形成多重均衡存在的條件等重要空間經濟特征。本文對于分析產品市場“一體化”與區域協調的相互影響具有重要的啟發,產品區際貿易壁壘和成本的下降能夠普遍提升各地區居民的福利,但是既有的觀點認為這也可能帶來經濟的過度集中,導致外圍地區的蕭條。本文的分析說明政府可以通過一定程度的轉移支付或者其他市場開發行為,抑制外圍地區的市場流失,進而維持其產業的經濟活力。
當前中國新型城鎮化是進一步發掘和釋放區域經濟紅利的重大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的目標之一就是促進勞動力和鄉-城移民的完全城鎮化,提高遷移勞動力要素收入與支出空間同步程度。本文結論一方面證明了這一戰略目標有利于提高城鎮經濟的集聚力和生產效能;另一方面,也提示經濟格局的演化和規模經濟效能的提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勞動力和移民城鎮化達到一個較高的水平之后,才能促成經濟集聚格局的形成和規模經濟效能的顯著提升。對于發達經濟體,在國內市場高度一體化的情況下,要想實現經濟格局適度分散的再“擴散”和再平衡過程,可以通過提高流動資本和勞動力要素的收入遣返程度,將中心地區市場轉移程度降低到足以維持經濟分散的較低水平。此外,本文基于流動要素的購買力的轉移的視角,對于國際或區域之間的經濟差異的演化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模型所揭示的收入遣返的空間經濟效應拓展了對國際或區際貿易保護措施經濟影響的分析維度。
參考文獻:
[1] 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3).
[2] Baldwin R E,Forslid R,Ph M,et al.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
[3] Forslid R,Ottaviano G.An Analytically Solvable Core-Periphery Model[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3,(3).
[4] Martin P,Rogers C A.Industrial Location and Public Infrastructur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5,(39).
[5] Melitz M J,Redding S J.Heterogeneous Firms and Trade[C].Chapter 1 in Handbook of Internation Economics,2014,(4).
[6] Takahashi T,Takatsuka H,Zeng D Z.Spatial Inequality,Globaliza?tion and Footloose Capital[J].Economic Theory,2013,(53).
[7] Helpman E,Krwgman P R.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uce:In?creasing Returns,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Cambridge:MIT Press,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