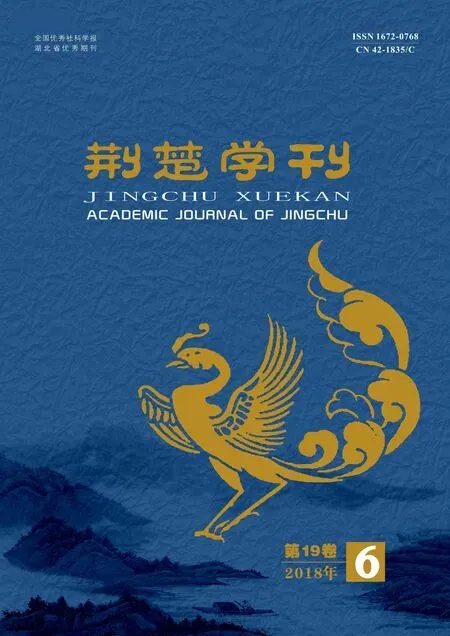明清時期湖北文學批評中的楚文化創新影響論
(華中農業大學 文法學院,湖北 武漢430070)
楚文化是中華文化之中非常有特色和活力的核心組成部分之一,湖北是楚國的核心區,研究楚文化對后世文學發生的影響,從明清時期的湖北入手,自有其典型性。
歷史上的楚國,樞要之地在湖北。但直至明代以前,行政上的湖北治域尚未形成,所以楚文化在湖北人的心中還是很平淡的。洪武九年(1376),明朝設立湖廣承宣布政使司,基本囊括兩湖地域,其中洞庭湖以北即湖北,將湖北今境除了英山、建始二縣之外的所有區域,首次納入同一高層政區。湖廣雖為一統一政區,但八百里洞庭事實上將之分隔為湖北湖南兩個區域,統一施政,多有不便,所以,某些業務的有限分治,時有發生。尤其是正德五年(1510),“以大湖(洞庭湖)中分南北”,設置南北巡按御史二人,分按湖北、湖南。(參《明武宗實錄》卷59“正德五年正月癸亥”)這個官職是省級配置,湖北與湖南分省已顯苗頭。雖然基本獨立的湖北政區要到康熙三年設置,然而,期間有關行政、司法、科舉、糧政、民族、軍政等方面南北分理之策,多有出臺。這些就使得湖北成為了一個機能文化區,具有文化發生學的作用。大量文獻顯示,此后的湖北文人樂道楚文化,以楚文化自豪;楚文化在湖北文人身上形成濃郁的區域文化意識,深刻地影響著明清時期湖北文學的發展。這方面的研究在王齊洲、王澤龍所著《湖北文學史》和湖北作協組編的《湖北文學通史》中,有所體現,但限于體例,明顯缺乏專門性、系統性、鮮明性。因此,從明清時期的湖北入手,研究楚文化對后世文學發生的影響,頗具學術意義。
有關楚文化對后世文學發生的影響,中外研究成果甚夥,其中有兩部集大成的著作:郭維森的《屈原評傳》和蔡靖泉的《楚文化流變史》。前著集中論述了屈騷對后世文學發生的影響。后著論述了楚文化在以后各個朝代文化中的流變,其中就包含楚文化對各個時期文學的影響。縱觀這些成果,總體上是從文學創作的角度探索楚文化的影響,至于楚文化對后世文學批評的影響,尚未引起學界的足夠關注。本文所關注的正是楚文化對明清時期湖北文學批評的影響。
文學發展是很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情形復雜,這就往往導致學界在探討某種文化對文學的影響時出現抽象的武斷。如文學中的現實主義精神、愛國主義精神、道家精神等,在中原文化和楚文化中都包含著它們的源泉,如果探討楚文化對文學的影響時,每逢這些精神便屬諸楚文化的影響,就難免武斷。事實上,現在的楚學界已經出現了較為明顯的楚文化影響論的泛化傾向。鑒于此,本文擬以明清時期湖北文人自身的言論為依據,論述楚文化對湖北文學的影響,看看作為受楚文化影響的親身經歷者,他們究竟意識到楚文化怎樣的影響。這樣的研究,別有其學術意義。
明清時期的湖北文學批評,包含大量有關楚文化影響的言論,涉及到的楚文化因素有楚國的立國史,楚人多憂、多怨、貴真、氣直大激昂、才氣踔厲、無門戶之見、能自樹立的文化性格,惟楚有才和楚地悠久的文化文學創新傳統,等等。經過研究可以發現,這些因素有著共同的核心,那便是楚文化的創新精神,它們都是從不同的角度指向這個核心。本文擬抓住這個核心,考察楚文化對明清時期湖北文學批評的影響。
一、楚文化培育湖北文人創新精神的要素論
(一)楚國的興族立國史和地理優勢是培育湖北文人創新精神的基礎

就地理位置來看,正如光緒時鐘祥黃振鋐所言“楚居天下之中,當水陸之沖”,因此楚國有著極強的文化交匯力、融合力,胸懷寬廣,視野開闊,有利于文學的創新。康熙時孝感夏力恕在《湖北詩佩序》中云:“天下名山大川,其環拱于外而絡繹于中者莫如楚,楚固四方風氣之所通,豈僅娖娖焉守一家言,與海內執牛耳諸公若熏蕕冰炭之不相入哉!有明一代,曰竟陵,曰公安,竟陵、公安尚矣。竟陵一家也,公安又一家也,楚地之不為竟陵、公安而自為一家者,豈系無人?”[5]
這位夏力恕目光敏銳,看出了楚國是一個中央大國,四方風氣之所通,文化包容,文學上善于與不同流派之間融合生長,顯示出一派文學創新的生氣,創造出了“公安”、“竟陵”諸派的輝煌。正如萬歷時蘄水郭士望所說:“楚人無門戶,此楚人之得也。”
(二)楚人的性情氣質培育了湖北文人創新精神的主體特征
明清時期湖北文人對楚人的性情氣質多有評價,比較集中的觀點有:楚人多憂、多怨、貴真,氣直大激昂,才氣踔厲,無門戶之見,能自樹立等等。從這些評論的邏輯來看,他們要強調的核心是不傍門戶,能自樹立。多憂體現改變現狀的責任,多怨是對現狀的批評,貴真是創新的人性依據,直大激昂是創新的氣魄,才氣踔厲是創新的力量。明清時期的湖北文人清醒意識到,楚人的這些性情氣質培育了他們文學創新精神的主體特征。
貴真是創新的人性依據,同樣也是文學創新的人性依據。中國文學自來就有修辭立其誠的古訓,從來文章傳真不傳偽。明清湖北文人看到了楚人有著鮮明的保真性格特點,正因為如此,才創造了文學的輝煌。萬歷時蘄水郭士望在《蘄上社初集序》中云:“宇內博士家,無不高楚人才分者。”接著,郭氏指出楚人才分高妙的性情根據:“夫文,與人不相遠也。幼清有言:為文而欲使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為文;為人而欲使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為人。故人不破綻,定非真人;文不破綻,定非真文。”[6]指明了真文源自真人,而不是完人(不破綻)。所謂完人,全合道德準則,故為文亦汲汲于法度,“十指漸欲縮”,“必不能有所發明”。那么,真人為什么會寫出真文呢?萬歷時夷陵雷思霈云:“真者,精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夫惟有真人而后有真言。真者,識地絕高,才情既富,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并且將袁宏道作為一面大纛昭示這番道理:“(石公)但任吾真率而已。…石公之文,石公之自為文也,明文也;石公之詩,石公之自為詩也,明詩也。……或古人所有,石公不必有;或古人所無,石公不必無…則石公獨知之契,恐古人不多及也。石公,楚人也。”[7]作為楚人的袁宏道(石公),但任情真率,故能與古人抗首,自鑄偉詞,成就了楚人在明代文壇上的輝煌。這種看法也是袁石公的自道,他曾說:“大抵物真則貴,真則我面不能同君面,而況古人之面貌乎?”[8]可以看出,這些立論,同時也是對于明代文壇擬古之風的有力批判。
多憂善怨也是楚人的氣質。明清湖北文人看到了楚人多憂善怨。明末清初景陵鄒枚在《雅笑編自序》中云:“鄒荻翁曰:‘楚人始為騷經。’余楚人,多憂,固近之矣。”[9]嘉靖時興國吳國倫云:“予讀《楚辭》,而知楚之人善怨,其天性哉。”“夫《離騷》,自怨生也。”[10]袁宏道云:“且《離騷》一經,忿懟之極,黨人偷樂,眾女謠諑,不揆中情,信讒斎怒,皆明示唾罵,安在所謂怨而不傷者乎?窮愁之時,痛哭流涕,顛倒反復,不暇擇音,怨矣,寧有不傷者乎?且燥濕異地,剛柔異性,若夫勁直而多懟,峭急而多露,是之謂楚風,又何疑焉!”[11]他們認為楚人本性多憂善怨,文學上的典型便是《離騷》。其實,說多憂善怨是楚人的天性,并不過分。楚族的文化自來就與儒家文化占絕對優勢的中原文化有所不同,儒家道德對感情的抑制相對較輕;同時在儒家文化之外,非常重視道家文化,重視個體的獨立性,因此,楚人的天性之中主體精神格外鮮明。體現在文學上,便是文人強烈的批判精神和情感抒發,即所謂的多憂善怨。
楚人這種性格特征,內含著文學創新的力量。嘉靖時沔陽陳文燭在《少泉集序》中云:“夫騷,楚辭也。三閭大夫,憔悴湘潭,忠而抱憤,溢為苦言。凄婉忉怛,不能澤以中和。孟、杜兩襄陽,睹時艱而遭隱淪,其詩窮而后工。余每讀‘哀郢’、‘懷沙’之章,‘垂老’、‘無家’之嘆,‘不才’、‘多病’之詠,千載而下,使人沾襟。倘所謂楚人之深于怨乎!”認為屈原“忠而抱憤,溢為苦言”而成《離騷》,也就是說《離騷》是憂怨之聲;并總體解釋了這種文學創造感人至深的原因,即“凄婉忉怛,不能澤以中和”,認為這種深于怨的情感,沖破了儒家中正平和的抒情界域,勃發出了“使人沾襟”的動人力量;還援引孟浩然和杜甫印證。接著通過當時京山太仆少卿王少泉的詩作,具體探討了這種原因:“(王少泉抱器而濩落終身,其詩)情屬景生,神在象外,如元造播物,色相種種。一物之中,生意俱足。其文麗而則,正而不迂。苕發穎豎,離眾絕志,而奇氣橫逸,不可控馭。”認為王少泉懷憂怨之深情,則奇氣橫逸,不可控馭;托諸景,故神行于化境之中;這種文學上的任情揮灑,很像“元造播物”,任憑“色相種種”,每一種都“生意俱足”。所以陳文燭云:“若先生者,其張楚乎。”[12]認為王少泉的詩風,與《離騷》一道,彰顯了楚國文學的創新精神。
明清湖北文人還看到了楚人直大激昂的性格特點,這正是創新所需要的氣魄。咸豐、同治時黃梅吳鐸云:“楚人氣悍,能自樹立。”[13]楚人的文氣充沛激蕩,故能創立成就。氣本來是一個哲學范疇,轉用于文論之后成了一個基本的文論范疇,這里的氣,是指文人的精神生命力。曹丕提出“文以氣為主”,韓愈提出“氣盛言宜”,方東樹提出“詩文者生氣也”,都主張氣本言末,詩文的根本在于生氣流貫。所謂楚人氣悍,是指楚地文人的精神生命力充沛飽滿,放逸奔涌。明末嘉魚尹民興在《姚天逋詩序》中云:“艾軒曰:‘詩芽茁,自楚國。’蓋以風始江漢,騷肇三閭也。楚人以直大激昂之氣泄諸詩歌,故能內貢丹心,外儀峻表,靜言哦之,穆然懷矣。”[14]指出楚人氣悍,所以風騷皆于楚地發其端。尹民興在《某小吏學詩序》中解釋這種原因,認為以直大激昂之氣泄諸詩歌,能破除和平溫厚,能“廣心肆志”,“自酣自唱”,“自顛自狂”,故能自造門戶。[15]乾隆時漢陽彭湘懷歷數有明以來,楚地文人尚氣性所激發的詩歌創造:“聲詩之盛,三百年來莫楚若矣。蓋楚風直質,尚氣性,能不傍門戶。若興國、黃岡(謂王稚欽、伯固兩公)、公安、景陵(鐘、譚前有魯公振之),皆是也。杜茶村推為楚風之極盛。”[16]其中特別是公安派主將袁宏道,史載其“年方十五、六,即結文社于城南,自為社長。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師之,奉其約束不敢犯。”[17]不僅年少才情富贍,更具有非同一般的勇氣與膽略,可謂“氣悍”。
才氣踔厲是實現文學創新的力量。楚人,因得江山之助,又得豐富而瑰麗的文化滋養,還得舒展的精神滋養,因而文才駿發踔厲,這恰恰是楚人在文學方面除舊布新的實力。吳鐸在《龍岡山人詩鈔序》中云:“明季公安、竟陵,為世所詬病,然并能以其力易天下者。說者曰‘楚人氣悍’則然,夫非徒氣也,唯其能自樹立也。右臣(洪良品——引者)不求悅于里耳,而日以金鐘大鏞,鏗鍧于折楊、皇荂之間,其不謂之能自樹立者與!”[18]認為文學創新,固然離不開悍氣,但又不能止于悍氣,還須有才氣。明季公安“三袁”、竟陵“鐘、譚”,清季龍岡山人洪良品,都不徒“氣悍”,更重要的是“并能以其力易天下”,能自樹立。
(三)楚地悠久的文化創新傳統是養成湖北文人創新自信的資本
1.這種創新自信來自屈原的偉大人格和文學成就。
自《詩經》以后,屈原所創造的楚辭成為我國詩歌的兩大源頭之一。這一點,湖北文人有著強烈的認同。崇禎時蘄水官撫辰在《霜輪上人詩序》中云:“自《詩》亡,楚固詩之祖也。”[19]同治、光緒間孝感龍登甲在《楚辭原本六藝論》中云:“粵自風雅不作,文體屢遷,屈宋繼興,爰創騷體,擷六藝之精華,為藝文之準臬,信乎辭賦之先聲,文章之極則矣。”[20]都指出《詩》之后,騷體是詩賦之宗祖,藝文之準臬。而且,屈騷包含的是一種行廉志潔的偉大精神,正如道光時蘄水范德煒所說的那樣:“(屈原)匪直文章著述稱盛一時,其志潔行廉,竭忠事主,尤足垂世教而勵末俗。”[21]這樣一來,屈原的文學成就便超越了“藝文之準臬”,而具有了文化神像的意義。順治時孝感黃文星云:“詩變為騷,自吾楚屈大夫始,今昭然與日月爭光。”[22]明末黃岡杜岕云:“屈宋以騷繼經稱,與日月爭光。楚之振于古以此。”[23]湖北文士們皆篤信司馬遷“推此志(志潔行廉)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的崇高評價;而且斷言,正是憑屈原的成就,楚國才在古代的文壇上振拔起來。
屈原的成就給湖北文人帶來高度的自信,正是這種自信,激勵著湖北文學的創新。明末景陵鄒枚在《郢中白雪記敘》中云:“吾郢自三皇以迄戰國千萬年,而屈原為一人。夫以靈均為千古一人可乎?緣其事,考其心,察其著述,而靈均之品地乃見,則楚之所共尊,而天下萬世所共尊也。……至性之人,無所效述,惟楚有之,至今不絕。”[24]指出屈原為千古一人,堪稱至性之人,無所效述,只有我楚地之人,被屈原遺芳余韻,代生異人。康熙時夷陵王言惠認為,正是在屈原的激勵下,湖北形成了唐詩“獨標先進”和明詩“迭主夏盟”的光輝成就。
2.這種自信也來自楚文化悠久的創新傳統。

這種自信心激勵著楚地后人的文學創新。如雍正時孝感程光炬在《厀嘯集宋序》中評價漢陽張叔珽的詩學主張云:“吾楚夙號多材……江永漢廣,賢哲挺生。……先生(漢陽張叔珽——引者)之詩,久已雄三戶矣。……天門、公安之后,又為詩場立一壇坫矣。(先生)搜羅往籍,爰集宋詩。言詩者每高談盛唐,睥睨中晚,遞至于宋幾乎靡曼視之矣。夫宋豈無詩哉?……(宋詩)與開元大歷諸君子并駕齊驅耶!”[27]這段評論體現了湖北文人文學批評的一種常見心態,先鋪排楚地多才,賢哲挺生的傳統,旋即力稱作者的開拓之功。張叔珽,康熙時漢陽文人,從他評論時人程松門詩文“語必驚人,論忌諧俗” (張叔珽《程松門集序》)看,他的文學創作是追求創新的。從程光炬評論他的詩“季鷹鱸膾,托興秋風;林泉嘯傲,靜對古人”看,在當時詩壇上,他很可能是得了王士禎神韻說的風氣。從對待詩歌傳統的態度來看,康熙時宗唐派依然勢盛,慢視宋詩,而張氏認為宋詩堪與開元大歷諸君子并駕齊驅。這也可以說為詩壇尚宋派的風頭助了鼓吹之力。因此,程光炬充分評價了張氏在“天門、公安之后,又為詩場立一壇坫”的開拓之功。
(四)湖北文人從楚地悠久的文化創新傳統中覺悟到創新的責任
楚文化悠久的創新傳統也給湖北文人以高度的創新責任感。光緒時松滋雷以震在《擬集湖北詩征序例》中云:“荊楚之地,方廣千里,江漢炳靈,代產人杰。”他列舉一長串在文學和文化上具有創造之功的湖北人,如屈原、宋玉、景差、王逸王延壽父子、庾肩吾庾信父子、杜甫(按祖籍襄陽)、孟浩然、岑參、薛據、戎昱、衛象、潘大臨、林敏功林敏修兄弟、“三袁”、鐘惺、張仁熙、杜于皇、李云田,等等,真所謂“匯千古之騷雅,聚一時之壇坫”;然后申述編輯湖北鄉賢詩作的意圖:“不有表章,何昭來許?一旦殞落,允替陵蔑。姓名淪于荒榛,文字磨乎洛劫。風流精爽,沈翳厚地。后之君子,與有責焉。”[28]表示如果自己不輯錄和傳承楚地鄉賢成果,如何激勵后生?如果鄉賢文獻在我輩手中湮沒沉埋,我們就成了后輩的罪人。無獨有偶,光緒時沔陽盧靖在《湖北先正遺書序》中亦云:“鄉人讀此,當知吾鄂數千年之灝氣英光,流風余韻……于以張吾楚幟,發揚光大,躋于不朽之林。非所重賴于后賢者乎!”[29]可以看出,楚地悠久的文化和文學創造傳統,在湖北文人身上滲入了頑強的統系意識和責任意識,他們以統系的延續者和光大者自許或許人。
正因如此,他們常常能從歷史的使命高度定位自身的文學活動,評價湖北文學史上的每一個進步。如明末孝感夏煒在《沈大悟青云堂稿序》中評價公安派和竟陵派的進步:(面對“后七子”傳響趨聲之徒),“公安出而救之以自然,竟陵出而救之以簡遠。不階尺土,狎主齊盟。此以三戶復楚者也。”[30]認為公安派和竟陵派以其文學創造復興了楚文學。然而,公安派和竟陵派的弊病卻授人口實,作為楚人的漢陽李以篤遂憂心如焚,遂擔起維新的使命。因此,他在《江北七子(非指前后七子——引者)詩選自序》中說:“(后七子)其弊也縟繪而無風骨。公安袁氏起而乘之,獨賞清迥,鐘、譚揚其波而逐其流,其弊也佻巧而無聲韻。夫數君子又皆吾楚人,于是海內率以楚為口實。余與友人程子鰓憂焉,思有以正之。……(江北七子詩)于以息兩家之異同,正群言之淆亂,將使王李鐘譚異趨而同歸,鳴我清一代之盛。”[31]明末,屬于“后七子”殘余力量的興國吳國倫、京山李維楨基本維持王世貞、李攀龍的后“七子”派重格調的主張,其羽翼末流對于漢魏盛唐詩徒襲形貌,遺落真力,“縟繪而無風骨”。公安派及竟陵派相繼起而排之,重視詩歌才情,但其末流又分別陷入率易失范及幽渺褊狹,“佻巧而無聲韻”。因為兩個陣營的干將都是楚地人,于是時人對這些文學問題的批評遂轉化成了對楚人的批評。此情此景,李以篤作為楚人后生,憂心如焚,以“鳴我清一代之盛”為己任,糾偏補弊,以選江北七子之詩示法。他的詩論既重格調,亦重性情,“將使王李鐘譚異趨而同歸”。正如邵長蘅所說:“明季詩學榛蕪, 歷下、竟陵爭焰互熸, 浸淫五六十年。國初猶沿余習, 江北七子出, 然后詩道寖昌。”[32]可見當時李以篤所選的《江北七子詩選》在矯詩壇六十年之偏弊,給詩壇注入活力方面,產生了很大的效益。
二、楚文化培育的湖北文人創新精神在明清時期湖北文學評論中的體現
由楚文化培育出的這種鮮明的創新精神,在湖北文人對明清時期湖北文學創作發展進程的評論中得到鮮明的體現。
明前期文壇,被臺閣體籠罩,暮氣沉沉,亟待變革,遂出現“七子”的復古風潮。乾隆時漢陽彭湘懷云:“聲詩之盛,三百年來莫楚若矣。蓋楚風直質,尚氣性,能不傍門戶。若興國、黃岡(謂王稚欽、伯固兩公)……皆是也。”[33]認為明代楚地詩歌是發展得最好的,因為尚氣性,善創造,便出現了興國吳國倫、黃岡王稚欽等人的新成就。事實上,在前后“七子”的文學復古過程中,湖北有一大批才士投身這一文學改良運動,其中之尤者,與前“七子”一道的有黃岡王稚欽,嘉魚“二李”(李承芳、李承箕),與后“七子”一道的有興國吳國倫,京山王格、李維楨,沔南陳文燭等。他們一方面以古詩文高古宏壯的格調,矯“臺閣體”平庸萎靡之積弊,另一方面,又保持清醒頭腦,不走極端,在習古的同時不忘師心。王稚欽的觀點偏向何景明,擬古詩頗能得古詩神髓,創作成就侔于“七子”上乘,實乃復古運動中的一大干將,朱彝尊稱其“蓋在正嘉之間,何景明最為俊逸,廷陳(即王稚欽——引者)之天骨雄秀,抑亦驂乘矣。”(《四庫全書》別集類·《夢澤集》提要)惜其過早歸田,妨了名位。吳國倫是后“七子”的干將,提倡“詩道性情”,“閎襟宇而發其才情”,強調性情。這些才士們,在明代前、中期現實難以給文學提供活力的時候,從古詩文那里尋求養分,給萎靡不振的文壇“補鈣”,另一方面,又不忘重視性情,啟迪著詩文發展的新方向,為公安派的挺生蓄積力量。
“七子”的復古運動,其注重古詩文法度格調的思路并沒有為文學的發展指明真正的出路,久之,陷入了擬古的窠臼而難以自拔。此時,提倡性靈的公安派,以其“莫把古人來比我,同床各夢不相干”的氣概,以其回天的才力和“信心而出,信口而談”的創作成果,給詩文打開了一條充滿生機的道路,恰如錢謙益所云:“中郎之論出,王、李之云霧一掃,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淪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涂澤之病,其功偉矣。”[34]因此,光緒時應山進士左紹佐在《荻訓堂詩鈔序》中云:“吾楚詩人能以氣力斡回一世者,明有公安袁氏。”[35]袁氏氣力宏大,一掃模擬之習,以真實的性靈代替矯飾的道德,以自然的文風代替陳言套語,廓清之功甚巨。
然而,公安派提出的主要口號“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本身也有缺陷,導致該派末流出現了率易鄙俗的反文學傾向,于是竟陵派起而補偏救弊。嘉慶時漢陽邱樹棠云:“至明末而又有楚派者行,則竟陵鐘退谷先生為之也。”[36]竟陵鐘惺論詩,刻意求新。他曾說:“今稱詩,不排擊李于鱗,則人爭異之。或以為著論駁之者,自袁石公始。與李氏首難者,楚人也。”“(人人效于鱗),世豈復有于鱗哉?石公惡世之群為于鱗者,使于鱗之精神光焰有復見于世,李氏功臣,孰有如石公者!今稱詩者,遍滿世界化而為石公矣,是豈石公意哉?”[37]當初后“七子”的李攀龍(于鱗)執詩壇牛耳,人人爭效之。如今處在性靈派時代,人們談詩,無不排擊李攀龍而稱頌袁宏道。鐘氏認為這種表面的趨新恰恰是從眾、守舊。其實創新正是來自批判。當初袁氏批判李氏,正是為了保持李氏的創造光輝,是保護李氏的功臣。現在自己對袁氏予以救弊,也是為了保持袁氏創造的光輝。這段話顯示鐘惺有著強烈的文學創新意識。邱樹棠評鐘惺詩云:“若其清幽峭逸,則固楚人騷怨之遺,亦自成其為楚聲而已。”因為翕集在“三袁”周圍的文士中,平庸之輩湊的是表面上的熱鬧,邱樹棠認為鐘惺提倡的書寫獨幽之感遇,探尋詩歌幽怨的真情,確實可讓他們警醒,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謂得了騷人之旨。在這里,鐘惺強調當初對李攀龍發起首難的袁宏道是楚人;邱樹棠強調給袁氏發難的鐘惺也是楚人。都突出了楚人的創新精神推進了湖北的文學創作。
然而,竟陵派提倡的幽情單緒又陷入幽僻、褊狹之中,將文學引入旁門,于是湖北文人們又開始了新的探索。清中期漢陽王元起借王士禎之言稱許乃祖王孟谷云:“楚才踔厲,橫絕古今。百年來公安淺俚,竟陵蒙昧,為世口實。得吾侄(王孟谷——引者)大才,令三湘七澤別開面目。”“銜華佩實,自名一家。”[38]認為王孟谷才大,橫絕公安、竟陵之上,引導詩歌華實兼顧,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 咸豐、同治間孝感沈用增在《程維周先生詩抄序》中所言更為深刻:“當明神宗時,詩學榛蕪,吾楚鐘、譚二子特標性靈之旨拯其弊,說固本諸滄浪也,顧不主性情而專性靈,久之遂入于幽僻。于是登騷壇執牛耳者,以沉雄博大相矜尚而集矢竟陵,至謂楚人為厲階,不亦太過矣乎。杜茶村山人勝國移民……詩以理性情,性情之發為忠孝,猶天之有經緯,地之有泰華也……然則詩有山人,可識性情之正;黃岡有山人,足稱張楚也已。”[39]指出自明后期以來,公安派、竟陵派專主性靈,忽視性情,只關注心性情趣,忽略了胸懷和社會責任。于是杜茶村等人起而矯之。杜茶村即黃岡杜濬,清初遺民詩人,倜儻有高才,歷經易代大亂,功名濩落,困居他鄉,以不羈之才,寫亡國之痛、興亡之感,以及自身的憂憤,喚醒了沉埋已久的風騷精神。
清代中期,文壇風云變幻,派系迭起,如王士禎的神韻說,沈德潛的格調說,翁方綱的肌理說,袁枚的性靈說。這些派別,各走偏鋒。吳鐸在《龍岡山人詩鈔序》中云:“自袁簡齋以性靈之說倡率后進,海內靡然從風,其陋者往往束書高閣,不解風格為何語。而矯其失者,則又巑岏面目,屏黜性靈。兩家率齟齬而不合。自右臣為之,庶幾無所偏徇與。自來天下風氣,微楚人不能開先。”[40]指出袁枚倡性靈說之后,海內風從,末流則只見性靈,忽視詩歌風格的豐富性。另一邊翁方綱的肌理說則引起許多文人對學問義理的重視,卻忽視了詩歌的性靈。兩派執偏相攻。吳鐸認為黃岡洪良品氣勢超越,合兩家之長以成己;認為這體現了楚人開天下風氣之先的優良傳統。
總之,在明清時期的湖北文人看來,當時湖北甚至全國的文學發展,幾乎每一步都伴隨著楚文化在湖北文人身上培育出的創新精神的支持,這里不再費筆。
余論
楚文化的創新精神,不僅培育了明清時期的湖北文人,被當時的湖北文學批評界共同關注,而且一直貫通影響到現當代湖北文學。這里不妨摘錄王先霈先生評論湖北當代文學批評的一段話:“湖北的文學理論批評,屢屢有人敢于提出新異見解,在文學批評史上留下深刻的印痕。……(這類相關)文章和發言在發表的當時,都因為言人之所未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而引起強烈反響,遭遇到猛烈的批判。更加敢于提出理論異見的是胡風,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陣營內部,他長期發出獨特的聲音,自信地堅持自己的見解。由此,我們是不是可以說,湖北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有一種‘狂者’之風?”[41]這里的‘狂者’之風,就是楚文化中勇于開創的精神。
同時,我們可以由此發生引申,楚文化在湖北文學中培育出的這種創新精神,并不是孤立的,它與思想領域的李贄童心說的挺出,社會發展領域的張之洞督鄂先得歐風美雨之實,政治界的辛亥首義的橫空出世,等等,都應該是呼應的,相通的。特別是清末,當中華民族處在空前的存亡危機之中的時候,楚文化所培育的這種創新精神,又一次激發湖北人勇于開拓,勇于擔當。如1903年由留日湖北同鄉會主辦的報紙《湖北學生界》,其《敘論》云:“吾楚尤為中心點之中心點乎”,“今日之楚,乃因各國競爭之局勢,而重其價值者也”;湖北是“吾國最重要之地, 必為競爭最劇最烈之場”, 而“競爭最劇最烈之場, 將為文明最盛最著之地”。[42]434該報又云:“中國之內, 有位置如武漢之足重者乎, 無有也。其所居者為競爭之中心點, 故其所任者為世界之重心。”該報《湖北調查部紀事敘例》云:“(湖北)無人不思有所以效其力于中國者在。夫豈有捐棄,偏視故鄉, 甘使天下人士謂吾楚人皆沐猴而冠帶者乎!”[42]443湖北居天下之中心,將引領民族的文明;武漢為競爭之中心,將任世界之重心;楚人紛紛踴躍報效國家,勇肩使命,絕不愿抽身事外,辱沒楚人的優良傳統。這些言論與后來辛亥革命在武漢爆發并取得成功,合若符契。這樣看來,中華民族能從近代苦難中走出,有一份大功勞該歸諸楚文化的創新精神。吳鐸云:“自來天下風氣,微楚人不能開先。”這話說得有勇氣,也有底氣。從這樣的高度去看,明清時期湖北文學批評中所凸現的楚文化創新精神,在中華民族文化發展和社會進步方面,便具有非凡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