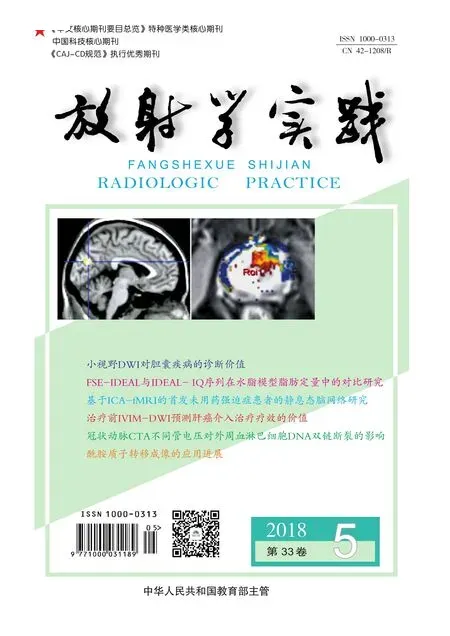基于ICA-fMRI的首發未用藥強迫癥患者的靜息態腦網絡研究
劉俊宏, 程敬亮, 李幼輝, 薛康康, 陳苑, 劉亞楠, 王彩鴻, 牛琪惠, 文寶紅,張勇
強迫癥(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是一種以強迫思維和/或強迫行為為主要特征的精神疾病,在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全球致殘原因中位列第十[1]。該病的突出特點是同時存在自我強迫與反強迫,這兩者的強烈沖突使患者感到無比焦慮和痛苦,嚴重影響其日常生活和社會功能[2],終身患病率為1%~3%[3]。近年來,神經影像學技術的發展為探索強迫癥的病理生理機制提供了新途徑,其中靜息態功能磁共振成像(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RS-fMRI)因其無創、易操作、重復性強、避免任務態執行過程中的個體差異影響等優勢而逐漸受到關注[4]。獨立成分分析(independent componem analysis,ICA) 是一種數據驅動RS-fMRI分析方法,無需先驗假設和傳統模型驅動,能有效去除噪聲干擾,尤其適用于靜息態功能連接網絡分析[5]。本研究采用基于ICA的RS-fMRI方法,分析首發強迫癥患者靜息態腦網絡的特點及異常改變,旨在了解未經藥物及心理治療干預情況下強迫癥患者的靜息態腦功能狀態。
材料與方法
1.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擇2015年6月-2017年6月在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精神科門診就診的首發強迫癥患者。病例納入標準:①符合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IV)第4版中的強迫障礙診斷標準;②首次發作,未進行過藥物或心理治療;③年齡15~46周歲,右利手,漢族;④小學及小學以上文化程度;⑤本人或監護人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①目前或既往患有嚴重軀體疾病、酒精依賴或藥物濫用;②腦部存在器質性病變;③目前或既往患其他精神障礙、合并精神發育遲滯、一級親屬中患有精神障礙;④磁共振檢查禁忌;⑤妊娠或哺乳期婦女。本研究共納入24例患者,其中男16例,女8例,平均年齡(24.54±9.82)歲,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2.92±2.81)年。本研究對照組均為招募的健康志愿者,按DSM-IV的診斷標準排除精神障礙診斷,既往無精神障礙病史,腦部無器質性病變。對照組共納入24例健康志愿者,其中男16例,女8例,平均年齡(24.50±8.02)歲,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4.63±3.52)年。本研究獲得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倫理委員會的審核批準。
2.方法
診斷及量表評定:由1位精神科主任醫師依據DSM-IV第4版修訂版中強迫障礙的診斷標準對入組被試者進行診斷;采用DSM-IV-TR臨床定式檢查(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IV Axis I Disorders-Non-patient Edition,SCID-I)對入組被試者進行篩查;由2位經過量表一致性培訓的精神科醫生采用耶魯-布朗強迫量表(Yale-Brown Obsessive Compulsive Scale,Y-BOCS)、24項漢密爾頓抑郁量表(24-Item 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HAMD-24)、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ilton Anxiety Rating Scale,HAMA)等對入組被試者進行臨床訪談和心理學評估。
MRI檢查:采用GE Discovery 750 3.0T磁共振掃描儀(美國通用電器公司),8通道相控陣頭線圈。用配套的泡沫墊固定被試者頭部,雙耳塞橡皮塞以減少噪音干擾。掃描時囑被試者保持靜息狀態,閉雙眼,身體靜止不動,保持清醒狀態,盡量不思考任何事情,不能入睡。所有掃描操作均由同一位熟練MR操作的放射科醫生完成。先行常規序列掃描,再行RS-fMRI掃描。常規序列包括T1液體衰減反轉恢復序列(fluid 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FLAIR)、T2WI及T2-FLAIR,用以排除兩組被試者的大腦器質性病變。RS-fMRI數據采用梯度回波(gradient echo,GRE)單次激發回波平面成像(echo planar imaging,EPI)技術采集,掃描參數:TR 2000 ms,TE 30 ms,翻轉角90°,矩陣64×64,視野220 mm×220 mm,層厚4.0 mm,層間距0.5 mm,層數32,共采集180個時間點,掃描時間為6 min,共采集5760幅圖像。
3.數據預處理
掃描所得圖像采用MRI croN軟件進行格式轉換,將DICOM格式的數據轉換為nii/img格式。圖像預處理采用rs-fMRI數據處理助手(Data Processing Assistant For Resting-State fMRI Advanced Edition,DPARSFA)[6],基于MATLAB 7.14(R2012b,MathWorks,Natick,MA,USA)平臺,去除前十個時間點后進行時間校正和頭動校正(排除平移超過1.5 mm和旋轉超過1.5°的數據)。將每個被試者的圖像配準到標準的蒙特利爾神經研究所(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MNI)模板,以3 mm×3 mm×3 mm的體素進行重采樣。采用半高全寬(Full Width at Half Maximum,FWHM)高斯平滑核(8 mm×8 mm×8 mm)進行空間平滑。患者組中1位被試者因頭動參數超過設定閾值而被去除,最終23例患者和24例健康對照者納入獨立成分分析。
4.獨立成分分析
運用基于盲源分離技術的組成成分分析軟件GIFT(group ICA of fMRI toolbox,http://icatb.sourceforge.net)對預處理后的數據進行獨立成分分析。采用三次主成分分析(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ze,PCA)進行數據降維。使用GIFT軟件自行運算識別成分,成分數為28,選擇infomax算法,運算次數為100次。對每個被試者的獨立成分(包括空間圖和時間序列)進行重建,并進行FisherZ轉換。通過GIFT的Display GUI模塊顯示所有被試者的所有成分,根據先驗知識和文獻[7]選擇合適的腦功能網絡進行分析,提取每個被試者相同的成分組成子數據包。
5.統計學分析
使用SPM8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采用單樣本t檢驗(FWE校正,以α=0.05為檢驗水準)。選擇閾值(簇體素大小≥100個體素)后得到每個成分的t值圖,使用xjview軟件顯示并制作該成分的模板。對每一成分進行上述步驟,分別得到所有感興趣區的靜息態腦網絡模板。對患者組和對照組的每個靜息態腦網絡模板分別使用SPM8軟件進行雙樣本t檢驗(Alphasim校正,以α=0.001為檢驗水準),將年齡、性別和受教育年限作為協變量,從而得到兩組之間的差異t值圖,并用xjview軟件顯示,選擇閾值(簇體素大小≥40個體素),疊加single T1模板為背景,從而顯示該網絡內兩組間不同的腦區。
使用Rest軟件提取組間差異性腦區的功能連接值,使用SPSS軟件對差異性腦區的功能連接值與Y-BOCS總分、HAMD-24總分、HAMA總分等臨床量表得分進行Pearson相關性分析,以P<0.05為檢驗水準。
結 果
1.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
本研究最終納入47例被試者,其中首發強迫癥患者23例,正常對照24例。兩組之間的年齡、性別、受教育年限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表1)。
2.靜息態腦網絡

表1 兩組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
ICA分析后共得到28個靜息態腦網絡,肉眼觀察軟件生成的所有成分空間圖,明顯的白質、腦脊液和噪聲成分均予以剔除,最終選擇10個靜息態腦網絡,分別為前默認網絡(anterior default-mode network,aDMN)、后默認網絡(posterior default-mode network,pDMN)、內側視覺網絡(medial visual network,mVN)、外側視覺網絡(lateral visual network,lVN)、枕極視覺網絡(occipital pole visual network,pVN)、聽覺網絡(auditory network,AN)、左側額頂網絡(left frontoparietal network,LFP)、右側額頂網絡(right frontoparietal network,RFP)、背側注意網絡(dorsal attention network,DAN)、突顯網絡(salience network,SN)。
3.首發強迫癥組與對照組間靜息態腦網絡內功能連接的比較
分別對10個不同的靜息態腦網絡進行網絡內功能連接的分析,觀察兩組間每個網絡內存在顯著性差異的腦區,其中后默認網絡、右額頂網絡和外側視覺網絡內存在顯著性差異腦區。首發強迫癥患者組與正常對照組比較,后默認網絡內雙側楔葉功能連接增強,右額頂網絡內右側頂下小葉功能連接增強,外側視覺網絡內右側枕中回功能連接增強,無功能連接減低腦區(表2,圖1~4)。

表2 組間網絡內功能連接異常腦區
注:Alphasim校正,以α=0.001為檢驗水準,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BA分區:布羅德曼(Brodmann)分區,由德國神經外科醫生科比尼安·布羅德曼提出的根據細胞結構將大腦皮層劃分的一系列解剖區域。
4.組間差異腦區與臨床量表的相關性分析
Pearson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右側額頂網絡中的右側頂下小葉的功能連接值與Y-BOCS總分呈負相關(P<0.05),余未見顯著相關(P值均>0.05,表3)。

表3 組間差異腦區與臨床量表總分的相關性分析
注:* Pearson相關性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圖1 首發強迫癥組與對照組共同進行獨立成分分析所分離的部分靜息態網絡。a)后默認網絡;b)右額頂網絡;c)外側視覺網絡。

圖2 與正常對照組相比,首發強迫癥患者后默認網絡中雙側楔葉的功能連接增強。 圖3 與正常對照組相比,首發強迫癥患者右側額頂網絡中右側頂下小葉的功能連接增強。 圖4 與正常對照組相比,首發強迫癥患者外側視覺網絡中的右側枕中回功能連接增強。
討 論
強迫癥是以反復闖入性的、不自主出現的負性思維、影像或觀念,伴或不伴重復、刻板或儀式化的動作為特征的一種神經癥性障礙,對該病認識不足及疾病本身慢性病程的特點常導致患者就醫不及時,預后較差。雖然早在一百年以前,強迫癥就已經作為一種精神疾病為人們所認識,但直到目前強迫癥病因仍然未明,治療仍是一個難題。近年來,神經影像學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對強迫癥神經環路的認識,提出眶額葉-紋狀體-丘腦-皮質環路(cortico-striatal-thalamic-cortical,CSTC)功能障礙可能是造成強迫癥的神經生物學基礎[8],但經典環路外是否存在其他功能網絡的異常也同樣值得研究。目前國內強迫癥靜息態腦功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局部一致性(regional homogeneity,ReHo)和低頻振幅(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ALFF)等研究方法上[9,10],罕有關于強迫癥患者靜息態腦網絡內功能連接的研究。ReHo和ALFF僅反映了局部腦區神經元的自發活動,較為局限。因此,本研究采用獨立成分分析的方法對強迫癥患者的全腦網絡及網絡內功能連接進行分析,以期在無先驗假設的情況下,客觀而全面地反映強迫癥患者靜息態腦網絡的變化,探討強迫癥可能的神經生物學機制。Anand等[11]的研究表明,強迫癥的部分治療藥物會造成腦網絡連接的改變,因此,本研究被試者選取首發未經治療的患者,排除了藥物及心理治療干預的影響,結果相對客觀、可靠。
默認網絡(default mode network,DMN)是目前研究最為廣泛和深入的、最重要的靜息態腦網絡[12]。Raichle等[13]首先提出默認網絡的存在,靜息狀態時大腦部分腦區的代謝明顯高于其他腦區,而執行特定任務時這些腦區的能量代謝低于其他腦區,稱為默認腦區。DMN主要包括前扣帶回、后扣帶回、楔前葉、內側前額葉、雙側角回、海馬旁回、內側顳葉和外側顳下回等腦區。默認網絡包括前默認網絡和后默認網絡兩個子網絡,前默認網絡與社會認知、自我意識的加工等有關,后默認網絡與內外環境監測、情景記憶提取等有關。國內外多項研究表明,強迫癥患者存在默認網絡的異常,Gruner等[14]研究發現強迫癥患者靜息態腦網絡存在中部或背側前扣帶回網絡、前后扣帶回網絡、視覺網絡的異常;Weber等[15]研究發現強迫癥患者組較正常組存在扣帶回網絡及聽覺網絡的異常;Cheng等[16]研究發現強迫癥患者存在默認網絡的異常。本研究發現后默認網絡中雙側楔葉的功能連接增強;陳惠娟等[17]的研究結果表明,部分功能連接增強可能反映了腦區功能的代償,是認知功能的代償性再分配的結果。本研究結果提示強迫癥患者可能需要調用更多的認知資源,提示強迫癥患者存在情景記憶和認知功能的異常。
視覺網絡主要包括內側視覺網絡(初級視覺皮層)和外側視覺網絡(高級視覺皮層),與視覺注意等行為相關。本研究中視覺網絡分裂為內側視覺網絡、外側視覺網絡、枕極視覺網絡三個子網絡。莊麗頻等[18]的研究提示強迫癥患者存在視信息加工異常。關于強迫癥患者視覺網絡的研究鮮有報道,Gruner等[14]的研究結果顯示相較于對照組,強迫癥患者組的視覺網絡功能連接減弱,而本研究發現首發強迫癥患者的枕極視覺網絡內右側枕中回功能連接增強,筆者考慮由于枕葉為視覺中樞所在,該結果可能與視覺強迫癥及余光強迫等有關。
額頂網絡,又稱執行注意網絡[19],位于默認網絡與背側注意網絡之間,主要包括背外側前額葉、頂內溝、頂下小葉、楔前葉、背側額葉和中扣帶回等腦區,與記憶、語言注意、控制空間注意和視覺處理等功能相關,包括左側額頂網絡和右側額頂網絡兩個子網絡。Stern等[20]研究發現強迫癥患者存在額頂葉網絡的激活;莊麗頻等[18]的研究提示右側頂葉皮層在視空間注意的警覺和定向任務中起到關鍵性作用,本研究發現右額頂網絡中右側頂下小葉功能連接增強,這可能與患者的強迫思維,如注意力不受控制地集中于某些事物相關,反映了執行注意功能的異常,同時也可能與強迫癥患者工作記憶等認知功能的異常有關。此外,本研究發現右側額頂網絡中的右側頂下小葉功能連接值與Y-BOCS總分呈負相關,這在de Vries等[21]的研究中也有提及,這可能表明存在一種認知補償機制,提示強迫癥患者可能存在認知功能的代償。
Weber等[15]研究發現,相較于正常組,強迫癥患者組存在聽覺網絡功能連接的增強。Posner等[22]研究發現,未服藥的強迫癥患者突顯網絡與默認網絡間的功能連接增強。關于強迫癥患者的背側注意網絡,目前國內外文獻尚未發現陽性結果。相較于之前的研究結果,本研究雖分離出了聽覺網絡和突顯網絡,但統計學分析并未得出功能連接異常的腦區,分析原因可能與人種、疾病的異質性、樣本量差異、網絡提取過程中與其他網絡重疊等原因有關。其次,本研究納入被試者的例數較少,這也可能是導致結果偏差的原因之一。因此,尚需要更大樣本量、更多測量指標、更深入的數據處理方法以及進一步的實驗設計進行首發強迫癥患者的腦功能異常研究。本研究只探討了首發強迫癥患者腦功能改變情況,治療后靜息態腦網絡改變的評價對于評估患者病情及預后也有重要意義,這將是我們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綜上所述,本研究結果表明首發強迫癥患者存在多個靜息態腦網絡異常,涉及默認網絡、額頂網絡以及視覺網絡,主要表現為網絡內功能連接的增強,提示強迫癥患者的發病可能與其情景記憶和認知功能、執行注意功能、視信息加工等的異常有關。本研究既證實了強迫癥患者存在CSTC功能障礙,同時也提出經典環路外尚存在其他靜息態網絡功能連接的異常,為探討強迫癥的病理生理學發病基礎提供了新的思路。
參考文獻:
[1] Salkovskis P,Welton N,Baxter H,et al.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clinical effectiveness and cost-effectiveness of pharmac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for the management of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in children/adolescents and adults[J].Health Technol Assess,2016,20(43):1-392.
[2] 吳海蘇,肖澤萍.谷氨酸系統在強迫癥發病機制中的作用[J].中華精神科雜志,2013,46(5):314-317.
[3] Ruscio AM,Stein DJ,Chiu WT,et al.The epidemiology of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in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Replication[J].Mol Psychiatry,2010,15(1):53-63.
[4] Barkhof F,Haller S,Rombouts SA.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 imaging: a new window to the brain[J].Radiology,2014,272(1):29-49.
[5] Groves AR,Beckmann CF,Smith SM,et al.Linked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for multimodal data fusion[J].Neuroimage,2011,54(3):2198-2217.
[6] Chao-Gan Y,Yu-Feng Z.DPARSF:a MATLAB toolbox for "pipeline" data analysis of resting-state fMRI[J].Front Syst Neurosci,2010,14(4):13.
[7] Beaulieu C.The basis of anisotropic water diffusion in the nervous system-a technical review[J].NMR Biomed,2002,15(7-8):435-455.
[8] Posner J,Marsh R,Maia TV,et al.Reduc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within the limbic cortico-striato-thalamo-cortical loop in unmedicated adults with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J].Hum Brain Mapp,2014,35(6):2852-2860.
[9] 楊濤,程宇琪,羅春蓉,等.強迫癥首次發病未服藥患者腦靜息態低頻振幅研究[J].中華精神科雜志,2011,44(3):140-144.
[10] 馬麗沙,徐曙,黃茹燕,等.未經治療的強迫障礙患者靜息態磁共振腦功能局部一致性研究[J].南京醫科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5,35(4):580-584.
[11] Anand A,Li Y,Wang Y,et al.Antidepressant effect on connectivity of the mood-regulating circuit:an fMRI study[J].Neuropsychopharmacology,2005,30(7):1334-1344.
[12] 盧光明,張志強.靜息態腦功能連接磁共振成像技術及臨床應用[J].中華醫學雜志,2010,90(21):1441-1442.
[13] Raichle ME,MacLeod AM,Snyder AZ,et al.A default mode of brainfunction[J].Proc Natl Acad Sci USA,2001,98(2):676-682.
[14] Gruner P,Vo A,Argyelan M,et al.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of resting state activity in pediatric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J].Hum Brain Mapp,2014,35(10):5306-5315.
[15] Weber AM,Soreni N,Noseworthy MD,et al.A preliminary study of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medication nave children with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J].Prog Neuropsychopharmacol Biol Psychiatry,2014,53(4):129-136.
[16] Cheng B,Cai W,Wang X,et al.Brain gray matter abnormalities in first-episode,treatment-naive children with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J].Front Behav Neurosci,2016,30(10):141.
[17] 陳惠娟,孔祥,文吉秋,等.腎移植術后腦默認網絡和認知功能變化的研究[J].放射學實踐,2015,30(5):513-518.
[18] 莊麗頻,史堯勝,陳毓顫,等.強迫癥和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聽及視信患加工過程中感覺性腦誘發電位特征比較[J].中國臨床康復,2004,8(30):6782-6784.
[19] Liu H,Liu Z,Liang M,et al.Decreased regional homogeneity in schizophrenia:a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udy[J].Neuroreport,2006,17(1):19-22.
[20] Stern ER,Fitzgerald KD,Welsh RC,et al.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fronto-parietal and default mode networks i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J].PLoS One,2012,7(5):e36356.
[21] de Vries FE,de Wit SJ,van den Heuvel OA,et al.Cognitive control networks in OCD:A resting-state connectivity study in unmedicated patients with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and their unaffected relatives[J].World J Biol Psychiatry,2017,18(9):1-13.
[22] Posner J,Song I,Lee S,et al.Incre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the default mode and salience networks in unmedicated adults with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J].Hum Brain Mapp,2017,38(2):678-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