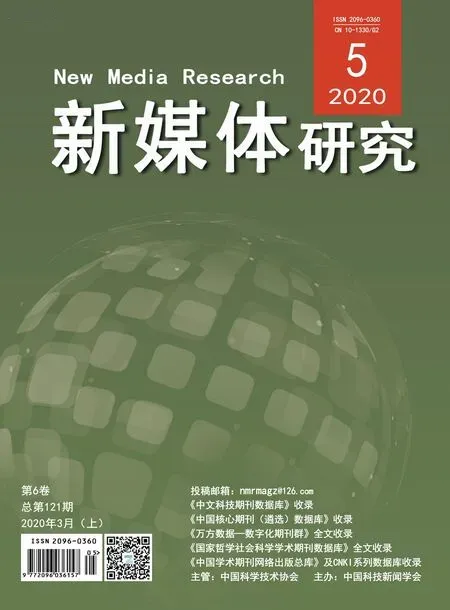“公民觀察團”現象的多維解析
李昌祖 王慢慢
摘 要 運用調查法和案例分析法,通過對數據的歸納整理,對以“公民觀察團”為代表的網絡群體事件進行多維整合和動態解析,以彌補學術界進行單因素定性分析的研究不足,期望為突發性群體事件的預防和應對提供參考。
關鍵詞 公民觀察團;多維解析;影響;對策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18)05-0007-02
在新媒體蓬勃發展的社會大環境下,網絡群體性事件的頻頻爆發無疑給輿論環境的治理和社會穩定提出了巨大挑戰。對“公民觀察團”現象進行多維解析有助于深層次了解其形成機制和動態演變,以引發關于中國地方政府管理中深層次問題和應對機制缺乏的反思。
1 研究背景
1)社會網民劇增。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40次互聯網發展狀況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到7.51億,半年共計新增網民1 992萬人。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4.3%,手機網民規模達7.24億,占上網比例的96.3%,移動互聯網主導地位強化[1]。
2)社會矛盾激化。改革開放和經濟全球化帶來物資富足的同時也帶來貧富的兩極分化,加劇了人民群眾的相對剝奪感。此外,地方政府對社會沖突的調解缺乏完善的應對機制,致使地方政府公信力流失和社會矛盾加劇。
3)“觀察團”發展現狀。經濟全球化和社會思潮的多元化客觀上促進了公民意識的覺醒和民間話語權的崛起,新的社會輿論環境激發了網民對輿論生產過程的積極參與熱情,使其對社會管理與監督呈現集體性創新和自發性監督的新形式。
2 現狀及成因
2.1 現狀分析
云南“躲貓貓”事件中出現的“網友調查團”以及后來在“鄧玉嬌案”中出現的“公民司法正義觀察團”標志著社會群體事件開始形成比較固定成熟的線下輿論參與模式,其具體特征如下。
1)集體性創新行為。目前中國處在突發事件的高發期,鐘智錦[2]等人對2002—2012年來發生的182件重要網絡事件進行研究,結果表明有45.1%的動機訴求是監督政府公共權力,27.5%是倡導公共行動,而以“觀察團”作為線下抗爭形式的比重占17.8%。可見“公民觀察團”是新的媒體時代條件下網民進行輿情干預的集體性創新行為。
2)自發性監督行為。互聯網的發展一方面突破了傳統媒體設置議程的功能,催生了更加民主的輿論環境,另一方面微博、微信等移動客戶端的普及為網民監督功能的實現提供了可能。“公民觀察團”現象的出現是基于網民對當前生存環境的不滿和對自身各項權利的維護。
3)社會反思的新載體。在頻頻發生的網絡群體事件中,自媒體媒介在輿論監督過程中所傳達的意見都來自民間。新媒體平臺帶來的便利使媒介的政治參與和社會整合功能以新的形式發揮巨大的
作用。
2.2 成因分析
1)相對剝奪感加劇。我國現在正處于特殊的社會轉型期,各種社會矛盾疊加。貧富分化、官民對立、司法腐敗等使民眾對生活產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和相對剝奪感。趙鼎新[3]曾提出“變遷、結構、話語是研究社會運動的三大視角。而由于種種原因而引起的剝奪感或壓迫感顯然是引發社會運動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在正常的渠道無法維護利益時,巨大的相對剝奪感很容易促使網民以極端的手段將個體行動變成群體行為。
2)地方政府公信力流失。政府信任衰落以及由此而來的“信任危機”和“信任赤字”是社會轉型期中國的一種現狀[4]。在突發性群體事件中地方政府不當的調解處置使官民之間長久以來產生巨大的隔閡,樂清事件中“錢云會死于謀殺”的謠言正是在傳播過程中標簽化和煽動性表達,契合了網民在以往的公共事件中地方政府總是作為受益方而收尾這樣的刻板印象,進一步激化了網民對政府的不信任和反感。
3)社會抗爭的新嘗試。社會抗爭通常是民眾針對政府進行的持續性、有組織地提出要求的一種公開努力。它指的是這樣的一些互動,在其中,行動者提出一些影響他人利益或為共同利益或共同計劃而導向協同努力的要求;政府則作為所提要求的對象、要求提出者抑或第三方而介入[5]。值得指出的是,我國群體性事件中網民在反對社會不公、揭露官民矛盾的同時依然渴望依靠政府維護正義、關注民生,其在意識形態上不存在和國家制度的對立。
3 影響
1)“輿論倒逼”式的官民互動。“輿論倒逼”是網絡時代獨有的現象,它是在自媒體異常發達和傳統信息系統渠道封閉僵化的雙重背景下產生的,網民以巨大的輿論力量迫使官方就某些事件出面澄清或采取解決措施。樂清事件出現后無法平息的民意與輿論壓力最終迫使地方政府接受了廣大網民派出“公民記者團”進行調查的要求,這是新媒體時代“輿論倒逼”的典型形式。從表現形式來看,它不僅僅是廣大民眾以主人翁的身份要求保障自身知情權與監督權的行為,更是官民雙方進行良性互動的新形式,也有利于緩和官民矛盾恢復其公信力。
2)促進社會文明化進程。“公民觀察團”現象體現了公民就社會公共事件主動發聲、占有媒體話語權的欲望以及參與感的提升。中國網絡政治的興起推動著中國政治文化向參與型政治文化和現代公民文化轉變,推動著中國政治文化更加傾向于理性、溫和與客觀,更加傾向于民主、公平與透明[6]。人民群眾利用逐漸開放的國家政策、便利的傳播設備、名人效應的帶動、自媒體的廣泛影響力對社會熱點和公眾事務進行討論,在客觀上促進了文明化進程。
3)群體極化風險。盡管以輿論倒逼和網絡曝光的形式可以迫使政府正面應對和解決某些公共事件,但是在公共訴求勝利的表面下我們也不能盲目樂觀。由于我國網民的專業知識有限、媒介素養有待提高,導致扭曲事實、真偽不辯的“扶弱抑強”的傳播現象頻頻出現,而群體決策可能使個人更加冒險,因其行動責任分散至所有成員上導致其觀念和行為更加偏激,這種群體極化風險,極易引發“烏合之眾”“輿論審判”,輕則使政府形象受損,重則破壞社會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