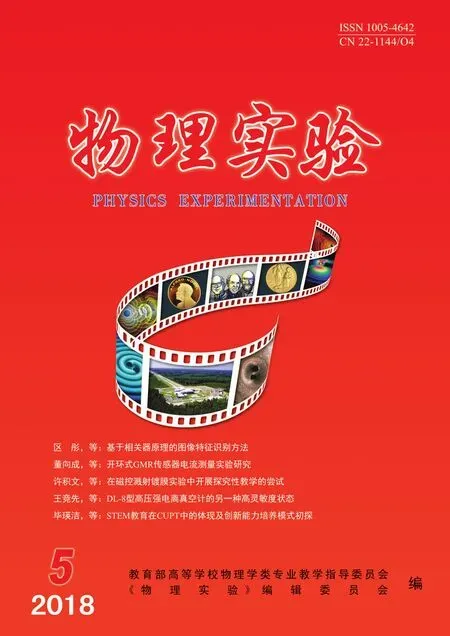中國古代指南魚和指南針的復原實驗研究
岑天慶
(中山市華僑中學,廣東 中山 528400)
科技史研究與一般歷史研究略有不同,因為不能重新走進歷史,所以學術界主要采用王國維先生的二重證據法,即:古文獻之間以及與古文物相互印證的研究方法. 科技史要對其涉及的科學問題進行研究,科學研究的核心是要進行科學實驗,而科學實驗最本質的特征是具有重復性. 所以用科學實驗證實古代的科學發現或科技發明,遠比通過古文獻之間相互印證得到的推測結論可靠和有說服力. 本文以對《武經總要》和《夢溪筆談》古文獻本意的解讀和分析為基礎,充分從中獲取關于指南魚和指南針制法的信息,如實按照古文獻的要求,實事求是地進行復原實驗. 通過相關物理知識和認知邏輯分析,探索古代指南魚、指南針制法科學問題的秘密,揭示其歷史真相.
1 我國古代關于指南魚制法的記載及過往研究
北宋時期,曾公亮在《武經總要》(1040—1044)中記載:用薄鐵葉剪裁,長二寸,闊五分,首尾銳如魚型,置炭火中燒之,侯通赤,以鐵鈐鈐魚首出火,以尾正對子位,蘸水盆中,沒尾數分則止,以密器收之. 用時,置水碗于無風處平放,魚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向午也. 這是學術界普遍公認和接受的我國最早發明指南針的記載.
20世紀40年代,王振鐸認為:《武經總要》指南魚未記載磁化方法,可能是撰者直接引文未加思索,或有意保密;熟鐵矯頑性較低,指南魚當用薄鋼葉制作;淬火只是加強鋼鐵硬度,與獲得磁性毫無關系;正對南北方向淬火是為了附會五行理論;“密器”可能內置磁石,保存指南魚的同時繼續磁化[1].
1992年,李強實驗發現:地磁場的熱剩磁效應非常弱,不足以驅動魚形鐵片指南. 他用鋸條做了模擬實驗,分別用家庭火爐、電爐加熱到約700 ℃淬火,兩端表磁或測不到或極小,插在泡沫塑料上,浮于水面,沒有指南跡象;用磁石摩擦磁化,鋸條兩端表面磁感應強度為1.6×10-3~1.8×10-3T,指南效果顯著. 文章還提到中國歷史博物館曾用中碳鋼制作魚形浮子,電爐加熱到700 ℃淬火,首尾磁感應強度為4×10-4~1.1×10-3T,無指極性. 李強判斷:中高碳鋼高溫淬火獲得的熱剩磁不足以克服水的表面張力而指極;磁石摩擦可以輕易使鋼片具有指極性. 藉此認為《武經總要》記述的指南魚制法是先通過高溫淬火獲得少量磁性,然后放在置有磁石的盒內封存,不斷傳磁,與近代“養針法”大體一致[2].
50年代,劉秉正提出《武經總要》指南魚的磁化利用了地磁場的熱剩磁效應. 他認為:鐵片被燒紅后,溫度可能達到鐵的居里點(770 ℃)以上變為順磁體;沿南北放置,是被地磁場磁化,冷卻后形成熱剩磁;鐵片“沒尾數分”表明磁化角度順應了地磁傾角,可最大限度利用地磁強度. 他還用縫衣針做了多次試驗,插軟木塞浮于水上,能指南北;蘸水和緩慢冷卻效果相同,前者更快捷[3].
黃興對劉秉正、李強制作指南魚實驗進行了評述,稱按照文獻記載加工制作了可浮在水面魚形鐵片,質量約0.45g[4]. 但對制作和實驗過程沒有說明,實驗結果能否指南沒有明確的結論.
對于條形薄鐵片正對南北方向淬火能否獲得磁性及條形薄鐵片制作指南魚用水浮法實驗能否指南,劉秉正與王振鐸、李強的實驗結果相反,形成的結論也大相徑庭. 從其古文獻中有關指南魚制作和使用的翔實描述看,曾公亮應該既是其見證者也是其實踐者,其作用主要是指導在軍事上的實際應用,古人應是在不斷重復驗證和實踐中形成和得到的結論,不應懷疑其記錄和描述的真實可靠性. 只有如實按照古文獻的記述制作,并進行系統、規范、全面而又耐心細致地復原實驗,才能發現其中的秘密及找到其中的原因,真正解決問題和形成可靠的結論.
2 指南魚的制作過程及實驗結果

圖1 制作的指南魚鐵片和鋼片, 木板和用于磁化的天然磁石
古文獻中對指南魚制作的長和寬是確定的,對薄鐵片的厚度描述不明確,但通常厚度如薄鋸條在0.7mm以上才有實用價值. 為了進行對比實驗,剪裁長為67mm、寬為17mm(長二寸寬五分)、厚分別為0.9mm和1.6mm薄鐵片及厚為0.7mm薄鋸條鋼片各2塊,其中1塊保留為條形,另1塊用砂輪打磨成魚形(圖1). 加工完成后,分別用其與打磨留下的鐵粉接觸,發現均不能吸取鐵粉,說明沒有直觀磁性,用高斯計測量發現所有樣品表面最大磁感應強度均只有5×10-4~1.5×10-3T的殘余剩磁.
將長為67mm、寬為17mm的薄鐵片磁化后,直觀磁性能勉強吸取1根細針,在液化氣灶上加熱至通紅,經澆水冷卻后發現直觀磁性消失,說明在液化氣灶加熱,溫度能達到居里溫度以上. 將厚為0.9mm的魚形薄鐵片和厚為0.7mm的魚形薄鋼片在液化氣灶上加熱至通紅后,沿南北方向放置澆水冷卻. 如何使薄鐵片浮于水面上,古文獻中沒有說明. 通常認為在魚的肚皮部分凹下去些,象小船,可以浮在水面上. 但筆者認為此制法不真實,首先其并沒有古文獻依據,其次這樣制作的指南魚很輕很薄,加工和能讓其浮于水面極其困難.
采用最原始最樸素的方法. 取長為56mm、寬為39mm、厚為8mm、質量為5.348g杉木板1塊,將以上制作的魚形薄鐵片和薄鋼片分別放在杉木板中央. 在直徑為18cm大碗中加入半碗水,在無風和周圍無鐵磁性材料的情況下,將杉木板和其上的魚形薄鐵片浮在碗中央的水面上. 開始魚形薄鐵片并沒有明顯的運動跡象,經過一段時間后,發現開始極緩慢地旋轉,且轉動逐漸變快,并逐漸趨于南北方向,經過多次反復回轉后,魚形薄鐵片最后穩定在南北方向上. 這樣就如實按照古文獻,采用古人最可能使用的漂浮方法,完成了2個指南魚的復原并成功進行了指向實驗. 也與宋代《事林廣記》記載用木頭做指南魚的方法相吻合:用1塊木頭刻成魚的樣子,像手指那樣大,指南魚就做好了. 把指南魚放到水面上,魚嘴里的針就指向南方.
為了更準確地進行觀察和實驗,在碗口上沿直徑在南北方向放1根木棍,將魚形薄鐵片沿東西方向放置與木棍垂直,用手指輕壓薄鐵片中央,目的是讓魚形薄鐵片靜止并防止其向碗邊浮移. 將手指輕輕抬起后,發現魚形薄鐵片在10s內沒有明顯的運動跡象,隨后開始極緩慢地旋轉,且轉動逐漸變快,當與木棍平行時轉動達到最快,然后轉動又開始變慢,當薄鐵片與木棍夾角約為30°時開始回轉,其過程約60s. 再經過約120s反復回轉后,魚形薄鐵片穩定在與木棍平行的南北方向上. 用魚形薄鐵片和薄鋼片多次重復實驗,情況基本相同. 將其沿180°或任意方向浮在碗中央的水面上,只要不靠到碗邊,經過足夠長的時間,樣品均能在水面上穩定指向南北方向(圖2).

圖2 用水浮法制成能穩定指南的指南魚

圖3 厚1.7 mm薄鐵片做水浮法實驗
將正對南北方向蘸水淬火的魚形薄鐵片和薄鋼片與鐵粉接觸,發現均不能吸取鐵粉,說明仍沒有直觀磁性,用高斯計測量發現表面最大磁感應強度為5×10-4~1.5×10-3T. 由此筆者推測:用另外3塊薄鐵片和1塊薄鋼片做水浮法實驗,同樣可以有效指南. 與沿任何方向蘸水淬火無差別,均不能增強磁性. 經過多次反復實驗,結果正如預期,制成條形的薄鐵片或薄鋼片不需要磁化或正對南北方向蘸水淬火,直接用水浮法實驗,只要不靠到碗邊,經過足夠長的時間,就能穩定指南. 將其余4塊樣品加熱后,沿任意方向放置澆水冷卻后,發現均沒有直觀磁性,用高斯計測量表面最大磁感應強度為5×10-4~1.5×10-3T,磁性幾乎無差別,與加熱前的磁性也幾乎無差異. 另外用厚1.7mm的薄鐵片做水浮法實驗,效果明顯好于厚為0.9mm的薄鐵片和厚為0.7mm的薄鋼片,指南所用時間明顯縮短(圖3). 但用厚為0.4mm的薄鐵片做同樣實驗,效果較差,不能準確指南. 說明直接將魚形薄鐵片浮在水面上的方法不可行.
表1是某次水浮法實驗的詳細記錄.

表1 某次水浮法實驗記錄
此外筆者購買1包10枚的普通針和1包10枚的普通鋼針,發現均沒有任何直觀磁性,不能吸取鐵粉. 將所有針分別插在泡沫塑料上,浮于水面,發現所有普通針和普通鋼針均會快速轉動,在10s內大體指南,30s內穩定指南(圖4). 說明水浮指南針比水浮指南魚靈敏. 但受外界因素影響較大,指南針容易漂移和晃動,不如指南魚穩定. 將針在液化氣灶上加熱至通紅并沿任意方向放置澆水冷卻后發現,其直觀磁性和水浮法實驗結果與加熱前基本無差異.

圖4 水浮普通針和普通鋼針
用表面最大磁感應強度為5×10-2~6×10-2T的蹄形磁鐵分別磁化厚為0.9mm的條形薄鐵片和厚為0.7mm的條形薄鋼片樣品,5h后,發現薄鋼片表面最大磁感應強度為1.5×10-2~2×10-2T,直觀磁性能吸取厚為0.7mm的魚形薄鐵片;而薄鐵片表面最大磁感應強度只有4×10-3~8×10-3T,直觀磁性只能勉強吸取1根細針. 說明薄鐵片也能被磁化,只是磁化后的剩磁較弱. 再用其做水浮法實驗,發現磁化薄鋼片的靈敏度與水浮指南針相當,磁化薄鐵片達到穩定指向所需時間則明顯縮短.
取沒有任何直觀磁性不能吸取鐵粉的長二寸的鋼鋸條,將其在表面最大磁感應強度為8×10-3~1×10-2T天然磁石磁性最強處摩擦磁化,發現鋸條直觀磁性能吸取微量鐵粉,兩端表面磁感應強度為1.2×10-3~1.8×10-3T,做水浮法實驗指南效果明顯改善,在10s內大體指南,30s內穩定指南. 用天然磁石磁性最強處摩擦薄鐵片,則實驗效果沒有明顯變化.
3 對過往研究的評價和關于指南魚研究的結論
從以上復原實驗和對比實驗的結果,可以對關于指南魚的研究和實驗作如下分析和評價:
1)王振鐸[1]認為“指南魚正對南北方向淬火只是加強鋼鐵硬度,與獲得磁性毫無關系”的結論是正確的,但不相信《武經總要》的記載,認為“用薄鐵片制作指南魚不真實,只有用磁化鋼片制作的指南魚才能指南”的結論卻是錯誤的. 李強[2]由于在文獻[1]觀念的影響下,為證實其推測和判斷的正確性而進行實驗,從而得到“用薄鐵片制作指南魚實驗沒有指南跡象”的錯誤結論. 其用磁石摩擦磁化,鋸條兩端表面磁感應強度為1.6×10-3~1.8×10-3T,指南效果顯著,該實驗內容真實可靠. 文獻[2]還提到中國歷史博物館曾用中碳鋼制作魚形浮子,電爐加熱到700 ℃淬火,首尾磁感應強度為4×10-4~1.1×10-3T,無指極性. 由于沒有觀察足夠長的時間,錯失了發現指南魚能指南的現象.
2)劉秉正[3]相信《武經總要》的記載,但沒有完全按照《武經總要》中有關指南魚制作和使用的描述進行實驗,將針燒紅后按南北方向蘸水,然后將它穿入軟木塞上令浮于水上,果然可以指南北. 文獻[3]認為鐵片被燒紅后,溫度可能達到鐵的居里點(770 ℃)以上變為順磁體;沿南北放置,是被地磁場磁化了,其結論有誤. 由此證實制作指南魚能有效指南的結論也是不可靠的.
3)黃興[4]按照文獻記載加工制作了可以浮在水面的魚形鐵片,質量約為0.45g. 0.45g僅是1枚粗針的質量,如果按照文獻記載加工制作魚形鐵片,其厚度將小于0.1mm,薄如紙片,不符合事實常理.
由以上復原實驗的結果可以得到如下結論:
1)如實地按照曾公亮在《武經總要》有關指南魚制作和使用的描述,能成功進行復原實驗,證實其古文獻的記載是真實可靠且具有重復性.
2)由于地磁場弱,普通薄鐵片制成指南魚磁性也弱,且其轉動慣量也較大. 在實驗中,需要耐心細致地觀察足夠長的時間,才能發現用水浮法指南魚有指南的效果,觀察時間是能否發現其有效指南的關鍵因素. 該問題在古文獻中沒有特別說明. 同時薄鐵片要有適當的厚度,這樣有利于增強轉動的磁力矩.
3)指南魚的制法與是否經過磁化和正對南北方向蘸水淬火無關,薄鐵片按南北方向蘸水并不能被地磁場磁化獲得磁性.
4)指南魚是在其殘余剩磁與地磁場相互作用下指南的,但并不能由此認為從《武經總要》的記載中,古人發現了磁的指向極性,指南魚的發明與發現磁的指向極性無關. 文獻中指南魚的制法與磁石吸引鐵的現象之間并沒有必然聯系,不能由此過度解讀文獻. 但從指南魚制法要正對南北方向蘸水淬火,說明古人認為南北方向與其他方向不同,南北方向可能存在某種神秘力量的理念卻是正確的,指南魚制法正對南北方向蘸水淬火可能與這種神秘力量有關系. 正是在這種理念的指導和影響下發明了指南魚并發現其指向性,其發現開創了在古代技術條件下,用鐵磁材料采用阻力矩最小的水浮法制作指向工具,對其后發明指南針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4 《夢溪筆談》的記載及指南針制法的研究
繼《武經總要》之后,北宋沈括在《夢溪筆談》中關于指南針制法有翔實記載: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 水浮多蕩搖,指爪及碗唇上皆可為之,運轉尤速,但堅滑易墜,不若縷懸為最善. 其法:取新纊中獨繭縷,以芥子許蠟綴于針腰,無風處懸之,則針常指南. 其中有磨而指北者. 余家指南、北者皆有之. 磁石之指南,猶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以上記錄說明沈括同樣既是見證者也是實踐者. 這是學術界普遍公認和接受的我國最早發現磁的指向極性和磁偏角,以及最早發明指南針的最重要古文獻證據. 通過對文獻的解讀,其關于磁現象的任何一項研究和記載,均堪稱物理學史上非常重要的科學發現,代表當時科學技術的最高水平. 由此可從中得到如下信息和研究結論:
1)雖然沈括并不明白磁石指向的原因,但在科學史上卻是最先明確記載發現磁的指向極性,并將磁與指向相聯系.
2)關于磁偏角這一重要的科學發現,沈括是用磁針確定南北的方位與日晷確定南北的方位比較得到的結論[5].
3)明確記載古代方士術士手中存在強磁性的“方家磁石”,能磁化鋼針而非普通天然磁鐵礦石.
4)最先明確記載發現強磁性“方家磁石”能通過摩擦,在短時間內快速磁化鋼針.
5)文中選用磁石磨針鋒是因為普通針并不全是鋼,只有針尖的部分是鋼,其余部分是鐵. 最早發現只有鋼磁化后才有強剩磁.
沈括總結制作指南針的4種方法:水浮法、碗邊旋定法、指甲旋定法和縷懸法. 從以上關于指南魚的復原實驗可知:水浮法阻力矩小,其是否能有效指南與針是否經磁石磁化無關. 碗邊旋定法和指甲旋定法阻力矩更大,實踐中可操性差,不能成功復原指南針,幾乎沒有實用價值.
筆者對縷懸法作復原實驗:取長為4.3cm、直徑為0.7mm的普通針和鋼針各1枚,直觀磁性均不能吸取鐵粉,將細線一端系于針中央,另一端系于木棍中央,線長約17cm. 為了減少風的影響,將針放入直徑為18cm的塑料桶中觀察,在桶口上將木棍沿直徑在南北方向放置. 穩定后發現兩針均更靠近南北方向,但不能有效指南(圖5). 將兩針在天然磁石上摩擦,直觀磁性能吸取微量鐵粉,但定向實驗結果沒有明顯改善.

圖5 用未磁化的針做縷懸法復原實驗
將兩針在表面最大磁感應強度為5×10-2~6×10-2T的蹄形磁鐵磁極上摩擦后,發現直觀磁性能吸取同樣大小的細針,定向實驗發現針能快速轉動指南,穩定后發現兩針均能有效指南. 但不如指南魚穩定,易受外界干擾而晃動(圖6).

圖6 用磁化后的針做縷懸法復原實驗
以上復原實驗說明:在天然磁石上摩擦普通針或鋼針,雖然磁性略有增強,但用縷懸法不能有效指南,不能復原指南針.
圖7是鐵磁性材料初始磁化曲線和磁滯回線. 從磁化曲線可以看出,鐵磁性物質從退磁狀態受外磁場磁化時,其磁化過程可分為3個階段:

圖7 鐵磁性材料初始磁化曲線和磁滯回線
1)起始磁化階段. 當外磁場H很小時,磁感應強度B和磁化強度M隨H增大,在這一階段,與外磁場方向成銳角的磁疇能量低,磁疇擴大;而與磁場方向成鈍角的磁疇縮小. 磁疇大小的變化通過疇壁的可逆遷移過程實現,磁化是可逆的. 去掉外磁場不保留磁性.
2)急劇磁化階段. 隨著外磁場H增大,磁感應強度B和磁化強度M都迅速增大. 在這一階段,磁疇壁隨磁疇的增大而快速移動,與磁場方向成鈍角的難磁化的磁疇轉向夾角較小的易磁化方向. 當外磁場H增大到一定強度時,所有自旋磁矩通過磁疇壁的跳動來實現,轉動到與磁疇成最小夾角的易磁化方向,稱為磁疇壁的巴克豪森跳躍. 磁化是不可逆的,去掉外磁場后還保留部分磁性.
3)飽和磁化階段. 隨著外磁場H進一步增大,磁感應強度B和磁化強度M的增大逐漸變緩. 在這一階段,發生磁疇轉動. 磁疇由易磁化方向轉動到與外磁場一致的方向. 這時撤去外磁場,磁疇由與外磁場一致的方向又轉動到易磁化方向.
由初始磁化曲線可知,用普通天然磁石磁化普通針或鋼針,仍在起始磁化階段,磁化是可逆的,去掉外磁場后剩磁只是略有增加. 選取2塊實驗過程斷裂的普通條形磁鐵進一步作磁化鋼針實驗. 取1塊直觀磁性能勉強吸取1根小鐵釘的條形磁鐵,用高斯計測量其兩端最大磁感應強度分別為1.2×10-2T和2.5×10-2T,發現用其同樣不能明顯磁化鋼針. 說明用磁感應強度達到天然磁石2倍的普通條形磁鐵仍不能磁化鋼針,仍在起始磁化階段,磁化是可逆的.
取另1塊直觀磁性能吸取1根較大鐵釘的條形磁鐵,用高斯計測量兩端最大磁感應強度分別為2.5×10-2T,3.5×10-2T,磁性達到普通天然磁石3倍左右,發現用其能磁化鋼針,直觀磁性可吸取同樣大小的細針,說明突破了磁疇壁的巴克豪森跳躍,磁化是不可逆的,進入了急劇磁化階段. 普通蹄形磁鐵最大磁感應強度在6×10-2~7×10-2T,說明選取磁鐵的磁感應強度只要達到普通蹄形磁鐵最大磁感應強度的一半就能磁化鋼針.
由此印證筆者關注到的類似于吳魯衡羅經老店強磁性的“天然磁隕石”在中國古代一直秘密存在[6-7]. 其磁性應達到普通天然磁石3倍以上. 南北朝梁代陶弘景在《名醫別錄》中也有記載:優良磁石出產在南方,磁性很強,能吸引3~4根鐵針,使幾根針首尾相連掛在磁石上. 磁性更強的磁石,能吸引十多根鐵針,甚至能吸住1~2斤刀器. 據黃興所述:經多方考察在邯鄲武安、張家口赤城等地采集了數批磁鐵礦和磁赤鐵礦,后者表磁最高可達8×10-2T以上,遠高于前人實驗所用樣品[4]. 但并沒有提供相關實物直觀磁性的圖片. 根據筆者進行過的各種磁鐵磁化鋼實驗的經驗,磁性應超過物理實驗用的磁性較強的鐵氧體蹄形磁鐵(表磁最高小于7×10-2T),表磁最高可以達到8×10-2T,其直觀磁性應至少能吸取1把大剪刀. 如確有此種強磁性天然磁鐵礦石,可以肯定也極其稀少.
需要說明的是沈括最早明確記載發現磁的指向極性和磁化現象,但并不能由此說明此時中國古人才知道磁的指向極性和磁化現象,因為文獻中主要是介紹磁偏角和用縷懸法制作指南針. 東漢王充《論衡·是應篇》有“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抵指南”的記載,文獻只記錄了司南的使用過程,并沒有關于司南制法的信息. 說明王充只是其見證者不是其實際制作者. 吳魯衡老店保存的“天然磁隕石”能長期用于磁化普通鋼針,說明用“天然磁隕石”磁化普通鋼勺能制成司南,說明此時期中國古人可能已秘密用“天然磁隕石”磁化鋼勺發現了磁化現象和磁的指向極性.
參考文獻:
[1] 王振鐸. 司南指南針與羅經盤(中)[J]. 中國考古學報,1949(4):186-203.
[2] 李強. 指南魚復原試驗 [J]. 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 1992(18/19):179-182.
[3] 劉秉正. 我國古代關于磁現象的發現[J]. 物理通報,1956(8):458-462.
[4] 黃興. 中國指南針史研究文獻綜述 [J].自然辯證法通訊,2017,39(1):85-94.
[5] 岑天慶,林國勝. 關于沈括發現磁偏角的思考[J]. 物理教學,2014,36(11):73-74.
[6] 岑天慶,熊德永. 關于“勺形司南”是磁隕石或用磁隕石磁化制成的研究[J]. 物理教學,2015,37(8):75-78.
[7] 岑天慶. 用磁鐵磁化復原“勺形司南”及定向實驗研究[J]. 自然辯證法通訊,2017,39(2):7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