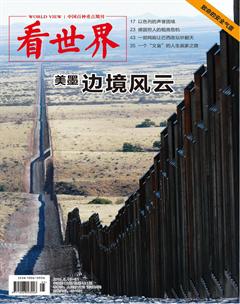50年前一夜之間瑞典從靠左行改為靠右行
“激動人心”這個詞是簡·拉姆維斯特在談到瑞典全國交通改革時說得最多的詞語,那一次的改革令瑞典全國駕駛者和騎自行車的人改變了一生的習慣,從靠左行駛改成靠右行駛。
“所有人都在談論這件事,但我們都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成功推行。”簡·拉姆維斯特如今已經77歲,當年26歲的他還只是馬爾默市一名剛拿到資格證的交通工程師,他參與了1967年9月3日瑞典全國規劃上的巨大轉變。這一天被正式稱為“H?gertrafikoml?ggningen”(右行交通)或簡稱為“H日”,目的是要令瑞典與其他歐洲鄰國一樣汽車靠右行駛。
除了希望提高國際聲譽外,瑞典政府也越來越關注本國的交通安全——當時瑞典的人口約為780萬,而根據瑞典統計局中登記的車輛數量,瑞典車輛從10年前的86萬輛,急升到“H日”的198萬輛。

1967年9月3日,是瑞典的“右行交通日”,或簡稱為“H日”
雖然瑞典全國奉行靠左行駛,但其實當時很多瑞典人的汽車方向盤都在左邊。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很多瑞典人會從國外買車,而國外的車都是適用于靠右行駛(方向盤位于左邊);另一個原因是像Volvo這樣的瑞典大品牌國產車為了順應國際市場需求,也選擇生產方向盤在左邊的車子。而當時有人擔心,右駕車輛在左駕道路行駛往往容易造成視野盲點,這是造成瑞典致命車禍事故增加的原因之一。事實上,有數據顯示,瑞典車禍事故從1950年的595宗上升到1966年的1313宗。
“瑞典的汽車市場不夠大,所以我們都會買左邊駕駛的車輛,”烏普薩拉大學歷史經濟學教授拉史·曼格尼松說道,“但是這意味著你的車其實適用于相反的道路通行方向,結果是你開車的時候就只能看到溝渠。”
“簡直忙翻了”
在“H日”開始實施之前,每個地方市政當局都必須修改道路標記,重新安置公共汽車站和交通燈以及重新設計十字路口、單車道等等。包括斯德哥爾摩,馬爾默和赫爾辛堡在內的多個城市更是借此機會整頓公共交通,例如關閉電車線以騰出道路空間加開公車路線。全國各地市購買了數百輛新公車,并翻新了8000輛舊公車,為其裝上雙門,總計公共交通改善工程成本為3億多瑞典克朗(約2.2億元人民幣)。
全國約36萬個路牌需要在一夜之間完成轉換或移動,時間緊迫,連軍隊也加入工作直至深夜,確保“H日”當天一切都能正式投入服務。同時,除了必須的交通工具,其他車輛都禁止上路。

工作人員在“H日”前連夜設置相關的道路標志
“我那天晚上簡直忙翻了,”拉姆維斯特回憶道,當時他負責確保馬爾摩市3000個路標都轉移到正確位置。“我的老板很自豪,因為我們是第一個致電到斯德哥爾摩、通知委員會負責人我們已完成任務的城市。”拉姆維斯特記得當晚辦公室工作熱情高漲,“我們半夜都在吃蛋糕和喝咖啡。”當然,除了成功的喜悅,對于有些人來說,“H日”也給他們帶來了龐大壓力。現為赫爾辛堡市交通顧問、已82歲的亞瑟·奧林回憶道:“最大的挑戰是時間不夠用,完全沒有假期,幾個月來每天工時都極長,我差點要自殺了。”亞瑟花了一整年部署物流規劃,一年后,因為壓力過大他簡直想“一頭撞在墻上”。“我的醫生下達了指令,讓我到非洲度假兩周,完全切斷工作上的所有聯系。”
一個新的時代
隨著“H日”的到來,艱苦的工作終于有了回報。1967年9月3日凌晨5點,在電臺廣播倒數后,瑞典人開始小心翼翼地在全國各地的道路上靠右行駛。時任瑞典交通部長奧洛夫·帕爾梅(后來成為了瑞典首相)在廣播中宣布,“道路靠右行駛代表了瑞典人日常生活的一個巨大轉變。”
“我敢說,從來沒有哪一個國家像瑞典這樣,投入如此巨大的資金和人力來實現與國際交通規則的統一。”奧洛夫·帕爾梅說道。
實際上,整項計劃花了政府6.28億瑞典克朗(約4.65億元人民幣),僅超政府當初預算的5%,換算下來相當于現在的26億瑞典克朗(約19.3億元人民幣)。不過歷史經濟學家拉史·曼格尼松認為,考量到這項計劃堪稱瑞典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基礎建設計劃,這樣的花費相對來說并不算太驚人。
作為比較,拉史·曼格尼松還提到了2017年瑞典交通部在道路和鐵路方面的總預算大約是250億瑞典克朗(約185億元人民幣)。“某種意義上來說,‘H日真是一筆便宜的賬目,即使在當時這筆錢也不算大。”曼格尼松說道,“當時的道路系統不像現在這樣發達,所以基礎設施的成本并不是很高,同時那個時候瑞典人的車基本都是左邊駕駛汽車。”
當然,這樣重大的政策能被順利推行,也要歸功于瑞典政府的高效率和縝密計劃,以及那個時代后勤工作的完善。
交通傷亡減少
從安全角度而言,這項計劃幾乎可以立即宣告成功。瑞典人在H日(恰巧是星期日)之后的星期一就開始工作,該天全國各地有157宗輕微交通事故,比平常周一的平均數字還要少一點,而且沒有人員死亡。

現年82歲的亞瑟·奧林當年也參與了瑞典那場意義深遠的交通改革
瑞典交通顧問、著有關于“H日”書籍《靠右走》的彼特·克恩伯格當時才10歲,他回想起自己當天興奮地騎著單車靠右騎行的情景,還有很多外國媒體都聚集在斯德哥爾摩對“H日”進行報道。
“這是1967年瑞典發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彼特·克恩伯格說道,“外國記者,尤其是英國廣播電視臺的記者,他們都在等待(瑞典改右行后)出現大批交通事故,所以對于這個結果略感失望。”
從數字上來說,相較于1965年,瑞典發生的車禍事故總共造成1313人死亡,2.3萬人受傷,在執行“H日”的1967年,車禍事故總共造成1077人死亡、2.1萬人受傷,這一年的交通事故死傷數目確實有明顯下降。外界相信,這主要是因為瑞典人因切換行車方向,反而額外小心駕駛。一直到3年后,車禍導致的傷亡率才回到先前水平,但別忘了,在此期間,瑞典全國汽車數一個直在持續快速增長。
曾經有八成民眾反對
雖然“H日”最后成功推行,但其實一開始民眾不太接受突然“轉右”——1955年政府曾舉行過公投,詢問民眾意見,當時有83%的人反對把靠左行駛改成靠右行駛。為了教育瑞典公眾,令他們更易接受右駕,政府從6億瑞典克朗的“H日”總預算中撥出4300萬克朗用作宣傳,包括電視、廣播、報紙廣告以及學校講座。“H日”還有自己的標志,印在廣告牌、公交車和牛奶盒上,當時甚至還有“H日”的主題曲創作比賽。
“政客們意識到只有單項宣傳計劃是不夠的,他們需要的是全盤的宣傳活動。”彼特·克恩伯格笑道,“目標不只是讓99%的人知道,而是要讓100%的瑞典人都知道瑞典即將改變道路通行方向。”
與此同時,曼格尼松補充道,當時在瑞典市民之間盛行的“順應文化”,以及他們對政府的信任,都有助于推動公眾輿論接受右駕。“當時的媒體批判性沒那么強,專家告訴他們什么,他們都會照直報道。如果專家說這樣不會太花錢,并且每個人都會受益,那么媒體就會接受這一點,我想公眾也會接受。”
曼格尼松認為,“H日”的推行不僅提高了瑞典的全球聲譽,作為北歐國家的重要參與者,還可能為瑞典帶來了其他長期成本效益——比如來自歐洲其他地區的貿易運輸額都增加了。然而,這種經濟影響“難以評估”,“瑞典的GDP每年都在快速增長,所以很難區分出‘H日對貿易運輸帶來的潛在利益。”曼格尼松說道。
未來的交通課程
時至今日,瑞典在彭博通訊社的全球創新排名中位列歐洲第一,交通基礎設施質素高于歐盟平均水平,相信與“H日”打下的根基不無關系。但今天的瑞典是否還能順利推行類似“H日”這樣的重大政策呢?大部分人認為,隨著社會氛圍的轉變,這其實有一定難度。
彼特·克恩伯格認為,現在的政治家和官方沒有那么容易轉變公眾輿論,戲劇性地令所有人都達成新的共識。“現在的瑞典社會比過去更加個人主義了一些,如果瑞典政府現在執意進行一項公投強烈反對的政策,勢必會引起社會公憤。”
與此同時,在政策推行上,現在除了電視和廣播,人們有了更多娛樂渠道,意味著要像當年那樣“全方位”放送信息可能也不容易。從經濟角度來看,曼格尼松估計,現在瑞典的交通網絡、基礎設施的發展已經比50多年前要發達得多,想要實施“H日”所需的財務成本也會大大增加。
“很難給出一個具體數目,但我可以肯定地說,所需資金會是50多年前的10倍。當然這是我的猜測。”曼格尼松說道。即使是瑞典交通運輸方面的戰略家如今也很懷疑,1967年的“H日”計劃放在今天是否能夠順利實施。
“在我看來,這將非常困難。”斯德哥爾摩的交通計劃負責人馬蒂亞斯·倫德伯格說道,“在當時,只有少數人——通常是男人——具有足以產生廣泛影響力的權利。今天的社會(比以往)更加多元化了。”
但倫德伯格也指出,“H日”仍然三不五時地會在他們的辦公室被提起,這是瑞典交通史上極具紀念意義的事件,它有助于鼓勵公眾和政治家持續關注道路安全問題。
瑞典自1997年開始推行跨國項目“VisionZero(零交通事故)”,目標是希望實現道路“零交通事故”。瑞典目前是全世界交通事故死亡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從1966年的交通意外死亡人數1313人,到2016年這個數字已經減至270人。
而現在,倫德伯格和他的團隊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就是為未來瑞典即將開車上路的人們提前做好安全措施。斯德哥爾摩目前的交通戰略首要放在行人道、自行車道和公共交通方面。今年1月份斯德哥爾摩啟動了全國第一輛無人駕駛巴士,政府官員們對此十分關注,認為無人駕駛車輛的時代即將到來,而這可能是自“H日”以來瑞典即將迎來的最大的交通轉變。
不過倫德伯格認為,盡管會對瑞典人的生活產生巨大影響,但這種變化還需經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并且在一段時間里還需大規模地征詢公眾意見,不會像“H日”那樣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