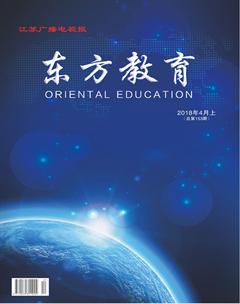特展對博物館教育功能影響的探究
張兆慧
摘要:博物館是一座城市歷史和現實的凝結,也是城市文化中心和文明的一種象征。隨著社會發展,近代以來博物館的社會化功能不斷增強,博物館早已從僅為貴族欣賞服務的藏珍室變成為社會服務的公共文化機構。博物館的功能除了收集、陳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類文化遺產的實物外,亦需要為公眾提供知識以及教育。特展作為一種靈活性強的展覽形式,其將在博物館公共教育服務的版圖中占據重要位置。
關鍵詞:特展;博物館;公共教育
自2008年《關于全國博物館、紀念館免費開放的通知》下發以來,截止到2011年年底,全國共有1804座公共博物館實現了免費開放,除此之外,行業博物館的免費開放也在積極推進中。雖然說免費開放拆除了博物館的有形經濟門檻,但如果博物館依然固守“灌輸教育”的模式理念,最終的結果將是橫亙在博物館與觀眾之間的無形門檻不僅不會打破,觀眾對博物館還會選擇敬而遠之。[1]
目前,教育及公共服務功能在整個博物館發展中正產生強大影響。博物館在國民心目中占據重要地位,是進行教育的特殊資源與陣地。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博物館承載了一定的歷史文化藝術,另一方面,博物館也是能夠為公眾提供休閑娛樂的場所。在享受政府財政撥款之后,如何提高博物館的展覽水平,怎樣通過舉辦一系列的延伸和拓展服務,使觀眾走進博物館,并且在進了博物館后有不一樣的感受,做到在拓展博物館公眾量的同時,保留觀眾,并且打造和強化博物館自身的造血功能和構建博物館的特色及品牌,從而為觀眾提供和呈現具備廣度和深度的教育活動,是各館面臨的當務之急和嚴峻挑戰,亦是我們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
從公共關系的角度來看,傳統的報紙、雜志、廣播、電視,這是博物館進行信息發布和教育宣傳推廣活動的傳統傳播媒介,而隨著信息化社會的發展,一些非大眾的傳播媒介,如通過不同種類的印刷品、郵寄品、新聞發布會等,都會對博物館的宣傳推廣起到功不可沒的作用。郵寄品和豐富多彩的印刷品具有傳統傳播媒介所并不具備的優勢,不僅成本低,而且效果顯著,針對性強,選擇性大,不拘泥于形式,傳播范圍既定,能及時得到反饋等。[2]而特展作為發揮博物館教育功能的一種傳播手段,無疑在教育活動與信息的傳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與常設展相比,特展具有諸多優勢。時間短、規模小是特展所具有的時空特征,也正是因為特展更新時間快等優勢,使得展覽舉辦的效應能夠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得以更加全面的涉入更廣泛的人群和文化,從而為公眾獲取不同的展覽信息和內容提供良好的支撐。從某種程度來講,當今社會正在朝著民主化、文化多元化和大眾化的方向發展,而作為博物館,也更加注重通過舉辦不同形式和內容的展覽來吸引大眾的目光并關注公眾走進博物館的次數。諸如近些年來日益興起的為觀眾打開視野的“觀念特展”、“劇場特展”、“戶外特展”、“觀眾參與式特展”等,可謂豐富了公眾的博物館體驗,對宣傳博物館理念及實現觀眾認知都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
以“浪漫蘇格蘭·詩意江南”特展為例,該展覽是由南京博物院與蘇格蘭歷史文化遺產機構共同主辦。該特展也正是得益于過去成功舉辦的“雙城記—南京與愛丁堡古城保護成果展”和“大明王朝:金色帝國”巡回展的基礎。該特展中,策展人將不同國界的藝術品并置于一個展廳,凸顯了中西方浪漫主義與東方詩意文化交融碰撞,為公眾搭建了一座東西方文化與藝術的橋梁。我們可以看到蘇格蘭的世界文化遺產、自然景觀和油畫作品與江南世界的繪畫、文人書房和民俗文物形成鮮明對比。觀眾通過此特展可以感受到跨區域的文化互動,從而產生跨時空的文化共鳴。
展覽未動,策劃先行。“高品質的內容策劃是展覽舉辦成功的前提,而主題是特展的靈魂。”假設藏品之間有內在的某種聯系,那么特展必須圍繞藏品設定鮮明的主題。圍繞藏品主題進行一系列的聯想、構思,從而到最后的呈現,以達到"1+1〉2"的整合優勢,實現整體功能的最優化,是擺在博物館教育部門及策展人員之間,決定其能否提供優質展覽內容的一條分割線。現階段,基本陳列與特展是博物館日常工作的中心,也是博物館履行教育職能、樹立形象的最主要渠道。從特展這一角度來深入研究我國博物館如何提高運營效率,以便在執行社會職能時更好地發揮優勢、彌補劣勢,這也是博物館工作內容的重心之一。
與西方博物館教育發達的國家相比,我國在博物館特展舉辦及展示方面還有較大差距。雖然部分國內博物館正在嘗試針對不同人群推出不同的教育項目,但都處于一種粗放式的初級發展階段。未能形成一個科學完善的特展展示體系,缺乏常年性的經典的教育項目是國內大多數博物館所面臨的現狀。而這一局面的形成主要是兩方面的問題:第一是博物館內部,存在于教育部門與其他部門之間、教育部門內部成員之間、教育研究人員及策展人員之間,他們未能形成項目合作的愉快關系;其次是外部,即各館的教育部門之間、各館之間、博物館與其他機構之間,他們未能珍視彼此的關聯影響,舍棄資源的彼此分享,甚至是對以往的經驗教訓選擇視而不見。[3]
此外,中國博物館的發展雖已跨入信息化時代,但教育手段的科技化程度明顯偏低,并且很多時候都是徒有形式。不少館至今沒有建設自己的網站,一些有網站,但存在信息更新不及時、內容不豐富、形式生硬、與觀眾互動不廣泛深入等問題。在新媒體的運用及呈現方面,發展更是嚴重滯后,與時下的社交潮流無法相提并論。
不可否認的是免費開放的參觀政策是國家步入博物館時代的有效契機,但相對而言,形成和培養相對固定的公眾群,這無疑是博物館在強化公眾教育方面所面對的一個挑戰。博物館是一部物化的發展史,也是人們進行討論與辯論的廣場與論壇。博物館應一改往日“收藏第一”的口號,轉變陳舊迂腐的思路觀念,轉而為公眾提供教育服務的功能,讓更多的公眾,尤其是青少年在接收“學校教育”之外,在博物館這片廣闊的天地中獲得啟發性的思考以及教育。
博物館是社會文化凝聚的產物,是一座城市底蘊的展現,博物館以其特有的文化氣質影響著公眾,而彌漫在公眾之間的文化自覺性與文化自信的提升也得益于博物館教育。特展以其獨特的展現形式,讓公眾教育在博物館這種環境氛圍中得以潤物細無聲地滋長。在博物館中所接受到的文明和傳統的教育是一個人文化素養的折射。特展所發揮的作用,在社會公眾心目中形成的這種自愿意識,包括徜徉在博物館中所接受到的啟發性教育無疑會影響一個人的心境。讓公眾感受到走進博物館是幸福的,看展覽是愉悅的,那么我們構建和諧社會和實現美好生活的愿望也就能夠得以更好實現。
參考文獻:
[1]單霽翔:《從“館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關于廣義博物館的思考》,天津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99頁
[2]陸建松:《論博物館接待服務中的公共關系》,《中國博物館》1995年第4期
[3]鄭奕:《博物館教育活動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