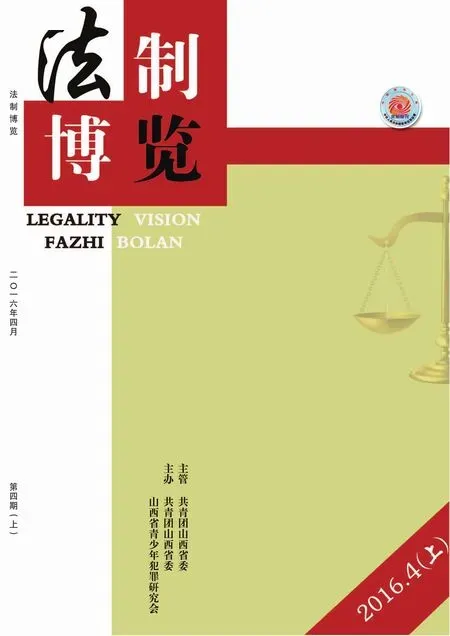見義勇為的法律分析
——以公平責任原則為核心
程 沙
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
見義勇為的法律分析
——以公平責任原則為核心
程沙
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院,北京100091
摘要:近年來,由見義勇為引發的相關法律問題頻現,極大地挫敗了見義勇為者的積極性。本文以公平責任原則為切入點,提出因公平責任原則本身的缺陷會阻礙人們實施見義勇為,最后就如何從法律上保障見義勇為者的利益提出廢除公平責任原則以及為見義勇為者設立商業保險兩點建議,并重點對后者進行論述。
關鍵詞:見義勇為;公平責任原則;商業保險
2015年10月15日,一款名為“扶老人險”的保險項目在支付寶平臺推出。截至11月16日,華安保險“扶老人險”在推出僅一個月的時間后,其天貓旗艦店的累計銷量就已經達到了5265份,獲得了極大的人氣。就具體用途而言,“扶老人險”主要用于保障因老年人摔傷撞傷等意外發生后,由于被保險人提供幫助并被誤認為是肇事者,而需要通過司法途徑來解決相關糾紛的法律訴訟費用,其賠償限額為2萬元,保期一年,并贈送全年的法律咨詢服務。除去調侃、炒作的成分,買此保險者無非是因為主觀上愿意實施見義勇為行為,只是畏于因被訛而受損才做出此種選擇。不可否認,近幾年因扶老人被訛的事件頻繁出現,這不僅讓施善者本身很受傷,更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讓更多本欲施善者因陷入“被訛”的假想而“淪為”袖手旁觀的冷漠路人。事實上,自2006年南京彭宇案以來,社會上關于“扶人”等見義勇為行為的討論一直沒有結束,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此困局何來?其中,既有扶人者、尤其是被扶者道德缺失的原因,亦可歸咎于對扶人者法律保障的以及社會管理方面的缺失和不足。
一、見義勇為的法律分析
當今中國,因見義勇為引發的糾紛大都訴諸法院,希望通過司法程序定紛止爭,因此,有必要從法律角度對“扶人”等見義勇為行為進行分析。
一般來講,見義勇為是指公民在沒有特定義務的情形下,為了保護國家、社會和集體的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權益,而采取的將自身安危置于危險之中的行為。不難看出,此種行為往往具有以下四種特征:其一,行為具有非義務性;其二,行為具有公益性、利他性;其三,行為具有危險性;其四,行為有緊迫性。
如今,在面對見義勇為時人們更多地選擇了回避,“扶老人險”的熱銷顯然反映出了人們心中的顧慮。從《侵權責任法》角度來看,一方面,現有的法律對見義勇為的保障尚不明確,未建立起相應的法律、社會保障機制,因此并未能消除潛在的見義勇為者或者說已經實施見義勇為行為的行為人的諸多后續顧慮;另一方面,由于立法本身的缺陷,導致某些法律規定對見義勇為行為存在著潛在的消極影響,進而使得對見義勇為者合法權益加以保護的本已岌岌可危的體系更加搖搖欲墜。
“見義不為”之所以頻繁出現,究其原因,不難得出以下結論:即法律自身的不完善,直接導致見義勇為者權益受損后得不到應有的補償,使得見義勇為者“英雄流血又流淚”的慘劇屢屢發生,嚴重挫傷見義勇為者的積極性。雖然,2010年正式施行的《侵權責任法》在第23條對見義勇為者權益的保護做出明確的規定,但是由于我國目前并沒有建立完備的見義勇為社會保障機制,而使其可行性大打折扣。一方面,在沒有侵權人也沒有受益人的情況下,見義勇為者并不可能依《侵權責任法》第23條之規定而獲得救濟,同時,在我國當前不存在相關社會保障機制的境況下,要實現對此類情況下見義勇為者的合法權益的保護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另一方面,即便是在存在侵權人、受益人的情況下,侵權人、受益人是否實際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對見義勇為者予以救濟,也無疑是一大難題。要在社會中鼓勵人們實施見義勇為行為,就必須弄清楚見義勇為者所關心的問題,消除阻礙他們實施善行的障礙。上述問題表明,正是由于立法者忽視了見義勇為者的關鍵利益——當見義勇為者實施見義勇為行為并因此致使其財產、甚至人身受到損害后,如何獲得使其能繼續生活下去的必要的救濟而導致的。顯然現有的立法在對見義勇為者的利益保護上已在《侵權責任法》23條中做出規定,但是由于上述缺點,致使其并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以上是針對《侵權責任法》第23條的有關缺陷的探討,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對于此點,學界的討論已非常充分。本文主要分析的是“公平責任原則”從另外一個層面對見義勇為行為所產生的消極影響,亦即見義勇為者,在實施見義勇為行為時,自己并沒有因此而受到直接損害,相反被救助者因為自己的行為受到損害,在沒有證據證明是由誰的行為導致(下文將對此加以論述,此時,一般是見義勇為者不能提出證據證明自己并非《侵權責任法》24條規定的所謂的“行為人”),而被救助者由于企圖讓他人分擔自己的損失,而違背道德,肆意利用《侵權責任法》第24條之規定,且在此條規定的所謂的“公平責任”本身并不完備的情況下,讓見義勇為者因此承擔并不應當由其承擔的責任的情形。
二、公平責任原則對見義勇為的消極影響
我國公平責任原則因其自身規定的不明確使其實質上成為一種“絕對的有限責任”,所謂“絕對”是指“遇上就得賠”;而“有限”則是“雙方根據實際情況分擔”,對見義勇為產生消極影響的主要、直接的原因是前者,即“遇上就得賠”。而造成此結果的原因有如下三點:
(一)對公平責任原則界定不清
我國對公平責任原則的性質和法律地位界定不清就直接導致公平責任原則被誤用為承擔責任的原因,即因為雙方都無法證明自己沒有過錯,所以雙方都要承擔責任。在一方是施善者的情況下,出現讓其承擔責任的結果顯然是不合理的。而事實上,我國許多學者所講的“公平責任”充其量只是一種“衡平責任”。嚴格地說,它最早起源于古羅馬法,即羅馬裁判官法中對“不法損害”額的確認方式。這一方式本身在當時就已經超出了責任確認的范疇,它一開始就是一個補充性的手段,而不是一個一般原則。另外,有學者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以下簡稱《民法通則》)132條,是關于公平責任的規定,并據此認為《侵權責任法》第24條關于公平責任的規定源于此。但是,這樣的理解是欠妥當的,尤其在我們并不承認公平責任原則能成為一項獨立的歸責原則的前提下,這一看法更是存在問題。雖然,《民法通則》中的確規定了“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由當事人分擔民事責任”,但是在《侵權責任法》頒布后,細看其第24條,可以發現其與《民法通則》中的規定是有著明顯差別的,即“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由雙方分擔損失”可以視為是對后者不當規定的一種修正,因此如果說《民法通則》第132條規定的公平原則視為歸責原則尚屬情有可原,那么從《侵權責任法》第24條得出同樣的結論,至少是不應當的。而且實際上,羅馬法中的這種“衡平責任”的出現,一開始就僅僅是一種補償性的手段,是指在沒有明確法律依據情形下,法官在判案時出于公平合理的考慮來確定當事人之間損失負擔的一種事后的補償性的法律救濟方式,它存在或者說出現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對造成損害后果的當事人責任進行確認,而是解決因不法損害所致損失的合理分配,即損失額分擔的問題,并以此實現實質上的公平。米健教授通過對《尤士丁尼法學大綱》進行研究,也認為,從其立法目的可以看出無論是“衡平”還是“公平”,此二者最終要解決的問題都只是“額”而不是“責”。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在“公平”責任的最初立法背景下,其立法目的原本就不是為了確認責任的歸屬,而僅是為了合理分配損失。如此,我們也不難看出,公平責任都不能算作一種歸責原則,更毋寧作為法律上承擔責任的原因了。
(二)轉型時期道德體系發生巨大變化
我國目前正處于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社會轉型時期,這種轉變必然導致整個中國社會道德體系的重大變化,而此種變化也即通常所講的道德轉型。該時期,舊有的道德體系開始瓦解,而適應現代社會需要的新道德雖然開始形成,但是因其并不完善、不成熟就使得其作用范圍有限,這也就導致我國在道德方面一個明顯特征就是社會功能明顯弱化。不論是學界的道德“爬坡倫”者還是道德“滑坡論“者都有共識。涉及到見義勇為時,由于道德滑坡,加之人們在利益受損時都傾向于通過各種途徑獲得“彌補”,尤其是《侵權責任法》中明確規定了,根據行為人的經濟狀況確定責任分擔,但對具體如何“分擔”又沒有做出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利益受損一方往往更愿意放棄自己的道德底線以謀取更為實際的經濟上的利益。事實上,在見義勇為舉證極其困難而人們往往對受損一方抱以同情的心態時,一旦法律規定不明確,在大多數情況下就只能依靠當事人的道德自覺,期望他們做出不違良心的判斷,但國人道德現狀事實上是令人堪憂的,這也從另一角度證明公平責任是一種“絕對責任”。另外,從法理學角度來講,正是由于道德的約束力有限,且不可靠,才需要法律作為最低的道德標準來做出強制性的規定,而公平責任原則作為法律規定卻需要道德的約束來使之真正起作用,這一點也是十分荒唐、可笑的。當然,這種現象的出現也與傳統道德規范的運作機制發生變化有關。傳統社會里,以利他主義作為道德評價的價值基礎,主要是以加大違反道德規則的成本使主體道德規則的內在化得以強化,并以此激勵主體的道德行動。但是,在社會轉型時期或陌生人社會,這種傳統的道德評判觀和機制已經難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三)見義勇為者舉證困難
因見義勇為本身具有的“緊迫性“這一特征,人們在實施見義勇為行為時往往很難保留對自己有利的證據,或者根本不具備這樣的意識。因此,我們不禁反問:是不是以后在實施見義勇為之前順序是先保留證據,再行善?但是這樣的情況明顯與見義勇為的緊迫性相沖突,也大大降低了見義勇為行為的效果。另外,在”誰主張,誰舉證“的民事訴訟制度之下,真的施善者們往往無法自證清白,也就造成“遇上就得賠”的情形開始泛濫,并使得所謂的“受害人”往往也在這種情況中獲得不正當的利益。雖然,近兩年隨著探頭等設備的普及,真相查明率已超過九成。2014年以來的21個案件,有20個案件的事實真相通過監控或證人證言得以發現。同時這意味著,無論恩將仇報還是冒充好人,大都能通過各種方式查明真相。但無論如何,總會存在”被訛“的可能,誰又甘愿冒此風險呢?同時我們還應認識到一點,即無論當事人選擇為善、為惡都是其在一瞬間做出的決定。因此縱使這種極高的真相發現比例對于減少甚至杜絕此類事件的發生極為重要,但不可否認,完善現有法律責任體系使之切實有效,則更加有助于促使當事人在這關鍵的一瞬間作出于他人和社會有利的決定。
綜上,不難發現,由于法律對公平責任原則的規定存在缺陷,導致公平責任原則對見義勇為者的主要有如下兩方面影響:一方面,會損害見義勇為者的權益;另一方面,會阻礙潛在的施善者實施見義勇為行為。
三、從法律上保障見義勇為者權益的建議
(一)廢除公平責任原則
公平責任原則的存廢一直存在爭議,既有堅定支持公平責任原則的,當然也有持完全相反意見的。本文通過探討公平責任原則對“見義勇為”這一行為的消極影響,已揭示出此原則本身的缺陷以及適用中存在的問題,因此廢除這一規定的觀點是比較合理的。
(二)對見義勇為者予以利益保障
《侵權責任法》第23條規定了對見義勇為者權益的保護,但其可行性卻大打折扣,主要是因為我國并未建立起相應、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在這種情形下,對見義勇為者的權益保障就存在兩個明顯問題。其一,在既無侵權人亦無受益人的情況下,見義勇為者的權益該如何保障?其二,即便存在明確的侵權人或受益人,但是他們是否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對見義勇為者給予賠償或者補償?那么如何讓他們因見義勇為而遭受的利益損失得到賠償或者補償呢?
現在,學界普遍主張制定統一的見義勇為法,以期通過對法律的完善來實現保障見義勇為者的權益之目的,且對此做出了比較詳盡的論述。不可否認,從法律角度來看,因為法律條文的適用問題,加害人、受害人不良的經濟狀況等原因,常常會使得加害人、受益人對見義勇為者的賠償或者補償難以真正落實。這也就表明我國現有的與見義勇為相關的立法確實存在不足,需要法律自身完善。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法律不是萬能的,我們需要法律、呼喚完善且切實可行的法律的同時也不能忽視相關社會機制的建設與改進。例如,我國現在已經存在見義勇為
基金會,即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
最近出現且受熱捧的支付寶“扶老人險”雖然只是賠付因實施見義勇為而卷入訴訟糾紛的訴訟費用,并不支付因案件敗訴而需要支付給老人的賠償金,但是這或許可以為我們的思考提供一個新的思考方向,即通過商業保險的模式,來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對見義勇為者利益的保障。盡管此款保險遭到質疑,甚至認為“扶老人險“會違反社會公德,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道德下滑要得到根本性扭轉,關鍵不在于道德的自救,而在于法律法規能不能實際發揮作用,在于法律能不能在社會中起到兜底性的作用,能不能為陷入糾紛的人主持正義。或許,這就是支付寶推出”扶老人險“的法治視角。因此,但從法律層面來講我們不應忽視”扶老人險“的價值,因為它的確反映了法律的缺位。同時”扶老人險“的熱銷也體現出在當今中國其的確是有市場的。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雖然這樣的商業保險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助推社會道德的提升,同時其也不是治本之策。但是,在當前中國,我們其實可以考慮鼓勵發展這樣的商業保險形式,使其不僅僅限于賠付訴訟費用,而是拓寬其承保范圍,在道德、法律缺位的情況下至少能發揮保障見義勇為者利益的作用。
當然,對見義勇為者利益保障的討論仍在繼續,“扶不扶“等其他見義勇為的困境仍然存在,但是也并非沒有解決掉可能,只是,要最終解決這個難題仍然需要國家、社會以及個人等多方的共同參與和共同努力。
[參考文獻]
[1]高曉蒙.公平責任的定性與適用[D].首都經貿大學,2013.3.
[2]顧航宇.社會轉型時期道德功能弱化的內在原因及其發生機制[J].理論與改革,2003(5).
[3]趙俊鳳.論社會轉型時期的道德失范[J].長春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9).
[4]應飛虎.九成真相率如何突圍“扶人困局”[N].人民日報,2015-10-16,005.
作者簡介:程沙(1993-),女,漢族,湖北人,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院,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憲法與行政法。
中圖分類號:D922.1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379-(2016)10-002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