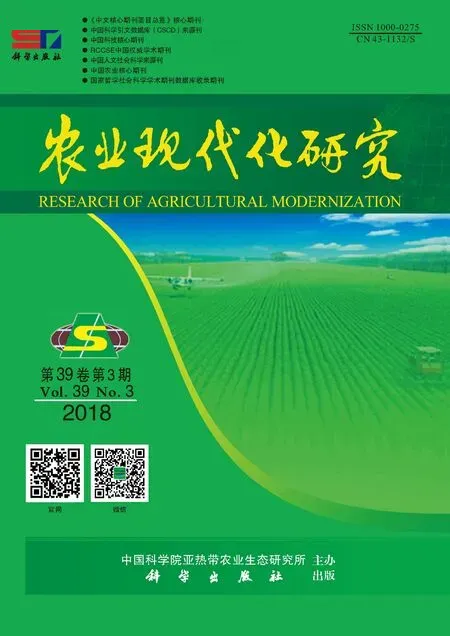日本農村振興的經驗及對我國的啟示
賈磊,劉增金,張莉俠,方志權,覃夢妮
(1. 上海市農業科學院農業科技信息研究所,上海 201403;2. 上海市委農辦研究室,上海 200003;3. 廣西財經學院經濟與貿易學院, 南寧 530003)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調整經濟結構、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等政策的驅動下,農業經濟、農村環境和農民生活得到了極大改善。但是,由于技術、資本等生產要素在城鎮與農村之間、中東部與西部之間、二三產業與第一產業之間尚未得到有效合理配置,農民收入增長乏力、傳統農業轉型升級速度緩慢、農村非農產業生存困難等問題仍難以解決。因此,減少農業農村發展不平衡,建立健全農村產業經營體系,讓農民享受到全面小康建設成果的要求十分迫切。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指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為新時代中國農業農村改革發展指明了方向。完善政策支撐體系,加強全面小康的戰略部署,引導發揮農業、農村、農民的內在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對于保證鄉村振興戰略高效有序的推進具有重要意義。
實施鄉村振興是世界范圍內“三農”的發展內容之一,諸多發達國家均進行過有益嘗試,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日本學者對日本農村振興的關注點主要有既要合理開發利用農業資源的多種用途,如設計農業景觀、開設農業公園等,又要將相關信息主動且持續的通過各種情報媒體傳達到城市居民手中,促進城鄉交流[1]。實現農村振興要激發農村內生發展動力,可從3個方面入手,第一是建成官民團結的新型農村社區,第二是以六次產業化為基礎重塑農村產業結構,第三是構建“居民參與、資金活躍、價值觀正確”的農村振興戰略體系[2]。農村振興的出發點在于將六次產業化創造出的農業附加價值“還”給農村,以保住農村發展的勢頭[3];農村振興要注重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扶持新型職業農民和培養農業接班人,更好的構架新型農民與本地居民的關系[4];要豐富企業參與農業的方式與方法,積極發展面向國外游客的鄉村旅游(鄉村國際化)[5]。
中國學者對日本鄉村振興的研究主要有幾個方面,一是對政策層面的總結和歸納,戰后日本的農業農村建設重點是與各個時期的重要政策目標相對應的[6];二是總結日本農村振興運動的特點,包括農業產業化與農村城鎮化并進,開展國民教育、提高農民素質,政府給予法律、政策和資金等扶持,促進農村發展[7];三是分析日本通過重塑鄉土價值觀來重新構筑社會意識體系,并以此為突破口進行農村振興[8]。關于非亞洲國家鄉村振興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歐洲農村有效利用鄉土文化來創造“文化經濟”效益,實現鄉村振興[9];在農村地區設立本地合作組織來指導農戶生產經營活動,能有效的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10-11];鄉村旅游是衡量農村發展情況的一個重要因素,它受到自然景觀與游客人次的影響,因此,提高當地居民和游客的參與度能促進農村地區生態環境的保護與社會經濟的發展[12-13]。
目前,中國學者對中國鄉村振興戰略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點。踐行鄉村振興戰略的政策取向和戰略措施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14-16];由于中國農村尚存在產業結構失衡、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村資源配置低效等問題,未來五年鄉村振興的策略選擇應為創新農村發展范式、重塑農業現代化目標體系并深入推進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從經濟、文化、生態、福祉和政治5個方面來建設鄉村,振興農村經濟[17-18];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現鄉村產業興旺目標,應因地制宜進行農村差異化產業規劃,構建種養融合或推動三次產業融合的鄉村產業體系,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靠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提供動力和支撐,靠惠農強農政策提供支持[19-21]。
經過文獻梳理可知,國外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具體做法主要集中在建設鄉村文化、發展鄉村旅游和重構鄉村產業等方面。在中國,由于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時間較短,目前對鄉村振興戰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解讀及路徑探索方面,鮮有關于具體措施部署的探討。日本農村振興戰略在實施的50多年間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且日本的農業農村發展情況與中國較為接近。基于此,本文就日本農村振興的由來和經驗做法為研究對象,系統分析其政策變遷、戰略部署、發展成效和不足之處,旨在為科學制定符合中國國情與農情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穩步推進農業現代化、實現鄉村與城市同步繁榮發展提供參考借鑒。
1 日本農村振興政策的由來
20世紀60年代,隨著日本經濟的快速增長,農村勞動力不斷向工業領域和城市流動,許多農村開始出現衰落跡象,主要表現為勞動力高齡化與農業兼業化現象日趨嚴重,土地拋荒、半拋荒等現象較為普遍,村落數量不斷減少,農村經濟幾近停滯,農業后繼者匱乏等,導致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給維持社會安定與保障糧食安全帶來了極大的挑戰。然而,農村勞動力的流出也給歸整零散的農業生產經營、促進農業經營向規模化集中化發展、優化農業生產結構與區域布局帶來了機遇。同時,收入的增加也引起國民對肉蛋奶和水果類高品質農產品需求的擴大,為日本提高糧食自給率、實現農產品供求的平衡與農業產業升級創造了機會。這些挑戰和機遇都對農業農村的發展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為了提高農業農村對高度成長的國民經濟的貢獻度,日本發起了農村振興運動。
1961年日本頒布《農業基本法》。該法重點關注農業生產結構的優化,通過實施直接補貼政策來引導農戶增加高品質農產品供給、減少市場需求量小或進口競爭壓力大的農產品生產,以實現農產品供需的無縫對接,提高農業經濟效益。同年,日本政府頒布了《農協合并助成法》,對基層農協展開合并,擴大農協的規模,切實發揮其維護農戶利益、改善生產生活、活躍農村地區等多重功能。《農業基本法》的實施一方面促進了農產品市場供需有效對接,推動生產規模的擴大、生產效率的提高與生產成本的降低,逐步實現了農戶收入增加和工農收入差距減小的目標,但卻導致農業兼業化進一步加劇,同時出現了農地流轉不暢的現象。于是,日本農林水產省于1967年提出了《結構政策的基本方針》,該方針采取促進農地流轉、完善融資制度、發展農戶合作經營、推動農地整理與開發、推進經營技術和農業機械的普及等手段,通過促進農地所有權轉移、發展經營委托與組織化生產來擴大農業生產規模,穩定專業化經營,并開始著眼于強化農村基礎設施、改善農村環境等問題。
1969年日本政府制定《農業振興法》,該法形成了農村振興的雛形,將完善農村基礎設施、保全農地、促進農地流轉、提高農業機械化程度、培育職業農民、促進農村居民穩定就業等作為主要內容,進一步為優化農業產業結構、發展農村經濟、增強農村活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1970年日本制訂了“綜合3年計劃”,進一步發揮農協在生產指導、產品銷售、信用合作和金融社會服務等方面的綜合功能,為日本農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70年代末,日本政府發起“造村運動”,旨在通過發展農業產業化與鄉村旅游等新型農業經營形式來促進城市和農村的交流,以保全農村生態環境、發掘農村歷史文化,保障農村的持續與發展,逐步改善農村地區的落后面貌,全面振興逐漸衰敗的農村。
1999年7月日本政府提出了指導21世紀農業發展的新農業法《食品·農業·農村基本法》,將實現國內糧食穩定供給、發掘農業多種功能與農業持續發展列為目標,并把“農村振興”作為基本理念之一。然而,新農業法的制定并不能挽回農村的頹勢。1990年到2005年間,全日本農業經營收入從6.1萬億日元減少到3.4萬億日元,農民的高齡化率從20.6%增加到37.8%,荒廢的農地也從13.5萬hm2增加到38.6萬hm2。為緩解不斷加劇的農業生產與農村社會問題,新農業法經過2005年和2010年兩次修訂,當中關于農村振興的對策由最初單一的山區直接支付政策增加到農村生態環境保全政策與農業·農村六次產業化推進政策,強調既要通過二三產業的帶動提高農產品附加價值,又要完善農村地區的觀光·教育·社保體系,加強城鄉間人口流動與文化交流。隨后,農林水產省設立農村振興局,確保農村振興戰略各項政策的落實。
2 日本農村振興政策的經驗做法
日本農村振興的做法包含3個核心戰略群,即以農產品為核心的戰略群、地域資源活用戰略群和以新技術為核心的戰略群,同時將農村振興與農業六次產業化緊密結合。
2.1 以農產品為核心的戰略群
1)農產品生產銷售戰略。該戰略提倡在生產階段,大力打造品牌農業,將農產品的生產服務與當地特有的自然、歷史、風土、文化和社會元素有機結合,積極申請農產品地理標志,強調農產品的地方特色,同時引導工商業資本與人才資源進入農業領域,建立健全農業品牌規劃,實行規模化與品質化生產[22]。地理標志農產品品牌的建立過程為發掘地區資源、確立品牌形象、開發新產品,制定生產管理標準與商標管理制度,進行市場調查與開拓商品銷售渠道。由此可產生3個效果:第一,穩定當地農產品價格,提高生產者收入,引導加工業和旅游業等新產業、新業態進入農業領域,進而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第二,將當地居民團結起來,打造宜居環境,促進農村定居人數的增加;第三,提高地方知名度,結合鄉村旅游,吸引外地游客,活躍當地的零售業、餐飲業和觀光業,最終實現鄉村振興。
在銷售階段,一方面鼓勵并協助各類農業經濟組織與超市和餐飲企業對接,降低流通成本并提升農產品質量,例如,與高級農產品經銷商聯合建立農產品品牌,注冊商標,實現農產品的生產、包裝和銷售一體化,并對進行綠色生產的區域實施地區品牌策略;另一方面,廣泛建立農產品直營店,采取地方生產的農產品由該地區消費的“地產地消”策略,農協(JA)中央會在2000年第22屆日本農協全國大會中將“地產地消”作為日本農協重點實施項目,以保證生產者獲得大部分農產品銷售利潤、實現收入的增加,并普及新鮮、健康和安全的飲食,弘揚傳統飲食文化,強化消費者與農業、農村、農民的聯系,達到城市提攜鄉村的目的[23]。同時,加大媒體宣傳力度,提升農業行業形象。
2)農產品加工戰略。隨著日本經濟發展步伐的不斷加快,國民在快節奏的生活中對速食類、半成品類、營養類食品的需求與日俱增。對此,農業生產部門在嚴格遵守食品加工法與JAS法(《農林物資規格化相關法律》)的基礎上,對優質原材料進行精細加工,如谷物類加工、油料油脂加工、茶類加工、豆制品加工、奶制品加工、水果和蔬菜的罐頭果汁制品加工等。此外,飼料加工與對農業廢棄物的加工也日漸活躍[24]。農產品加工戰略還著重強調突出地方特色,即農產品加工品能在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同時,最大限度的展現地方特色,使本地與非本地農產品有明顯的特色差異,增強地方農產品的辨識度。農業生產者或與當地大型生產加工企業進行契約化種植,不斷研發改進加工技術,提升農產品附加價值,或與食品企業聯合開發新產品,深挖農產品價值,積極探索農產品的更多用途,使農產品經過加工成為商品,再遵循一般商品營銷策略進行市場信息的搜集、商品品種與價格的確立和開拓銷路,最后向市場推出符合消費者需求的食品、營養保健品、藥品和工業原料[25]。
3)農產品出口戰略。擴大農產品的出口對于拓展農產品銷路、提高農戶收入有著重要意義。日本政府于2015年修訂的《日本再興戰略》提出了農產品出口促進對策,將米及米制品、水果、鮮花、茶、牛肉、加工食品和水產品等列為重點出口品種,以東亞、東南亞和北美各國為重點出口國,對外進行海外市場調查、參加國際農產品展銷會、舉辦飲食研討會與食品試吃會等,對內設立出口戰略實行委員會,鼓勵農產品產地間進行合作,加強農產品品牌培育,優化生產地、加工場、批發市場、流通體系的基礎設施建設[26]。同時,政府向出口企業提供政策支援與信息咨詢服務,制定并完善食品安全法、動植物檢疫法和知識產權法等法律法規,積極尋找外國買家,在了解與發掘海外市場對日本農產品需求的基礎上,強化國內生產者與出口企業的聯系并進行訂單式生產,以實現2020年農產品出口額達1萬億日元的目標。
2.2 以地域資源活用戰略群
1)城鄉交流戰略。2008年日本開始實施“兒童農村交流項目”,廣泛開展小學生到農村的住宿體驗活動,將農村作為一個教育場所,讓兒童貼近自然、接觸農林牧漁業生產,培養其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正確認識。針對中高等教育的學生,政府利用日本學校畢業旅行的傳統,積極推廣農家體驗項目,鼓勵、引導學生在農家吃住,體驗播種、澆灌、收割、放牧、乳制品的收集制作等農業生產活動,培養學生熱愛農村、珍惜農民勞動成果的思想感情。企事業單位也安排雇員定期到農家吃住學習,在體驗農村生活的同時,促進了當地經濟的增長。同時,日本各地的農協也積極開展飲食文化教育,提升消費者對傳統飲食文化的認同感。此外,政府積極建設公益性、營利性的市民農園,讓都市的百姓親近農業、了解農業、心系農業,親身參與到農業生產隊伍中,加強農民與市民的交流,并積極開展城市與農村的交流對話,推進企業和非營利組織等主體的積極參與[27]。
2)鄉村旅游戰略。日本的鄉村旅游也稱為綠色觀光,是一種到訪農村、體驗自然與人文交流的旅游形態。日本政府于1994頒布《農山漁村休閑法》,將國民的休閑活動與農村振興有機結合,將農村的農業景觀、農事活動與歷史遺跡等開發成為觀光資源,并與當地旅行社及其他社會組織聯合,設計旅游線路并規范農村民宿和農家餐館的經營,將綠色觀光組建成一種成熟的商業模式。城市居民通過自然體驗、農業勞動和加工學習,了解農村的生活方式,品味農村傳統的飲食文化,獲得放松身心的效果。農村居民通過提供食宿服務,實現家庭經營多樣化,提高了非農收入[27]。另外,政府部門組織專家學者對特色的農業景觀與現象進行環境評價,制定觀光主題,形成地域的標志化、品牌化,并在不破壞生態、不影響生產的情況下,對農村基礎設施進行改造調整,以適應旅游觀光需求。此外,還利用農業資源的保健效果創造新型概念,吸引都市游客來農村放松身心。
3)生物資源戰略。農村地區擁有十分豐富的生物資源。日本政府積極推進國產生物燃料的生產與利用,于2008年頒布《農林漁業生物燃料法》,將食品廢棄物、家畜排泄物等作為一種生物能源開發利用,形成資源循環型農業。農村地區對于生物能源的利用主要體現在開發生物酒精、生物柴油、生物瓦斯等生物燃料等方面[28]。該戰略一方面為農村引入了新的技術并創造出新產業和新崗位,降低了農業經營對石油的依賴度,減少了溫室氣體排放,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顯著;另一方面,通過推進耕畜結合、有效利用家畜排泄物等方式,在降低生產成本的基礎上,實現了能源多樣化與農林漁業的持續發展。另外,將食品生產過程中的廢棄物和不符合標準的農產品作為燃料再利用,還對水產生物資源進行高附加值化利用,如做成高級天然調味料等。
2.3 新技術戰略群
1)技術革新戰略。農業生產領域的技術革新主要體現在加速技術開發與技術轉化、創新生產與流通體系、創造使用并保護知識產權、推進農業生產安全作業4個方面。加速技術開發與技術轉化是重點研發推廣滿足生產者需求的機械與技術,推動中央、地方、高校與企業間的合作,促進生產者參與技術的規劃、研發、普及和信息反饋。創新生產和流通體系,即實現規模化、省力化、低成本化的生產技術導入,實現提高農產品附加價值的加工流通技術導入,實現降低自然災害影響的管理技術導入。在知識產權方面,制定與完善地理標志保護制度,活用研究成果和特許技術,強化海外日本農業相關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定農業生產安全作業對策的目的在于減少農業生產作業中傷亡事故,對已發生的事故進行調查分析,提高應對作業事故的勞災保險投保率,強化農業機械和農業設施的安全操作流程。
2)企業合作戰略。首先,農業生產部門積極吸引能將農產品多元化利用的企業,開展深度合作,實現資源最大限度的合理使用,形成一條穩固的農業產業鏈;其次,將食品產業進行細分,穩固擴張成熟的產業,整合開發薄弱及新型產業,吸引中小企業和創業型企業參與;最后,加大政府的扶植力度,設立公共基金,改善生產、加工、流通各環節的基礎設施,建立農企共同利用設施,導入革新技術,確保產業活力,對“地產地消”進行小規模定點實驗,定期對觀測數據進行統計分析,逐步建立成熟穩健的“地產地消”模式,確保農業生產大部分利潤保留在農村地區。
3)農業帶頭人培養戰略。為應對農民高齡化、農村人口稀少化的困境,保證農業持續健康發展,日本政府制定了《認定農業者制度》,明確了培養地方農業帶頭人策略。同時,日本農協也與官辦農業推廣部門共同開展對農業帶頭人的技術培訓,聘請有經驗的企業員工和研究人員對農村生產經營進行指導與規劃,并邀請非政府組織人員及其它業界的高級人才參與監管,制定更全面合理的人才管理制度。在此基礎上,積極推進農戶法人化與農村集體生產,通過擴大生產規模、提高農業組織化程度、培養具有市場競爭力的農業經營體來改善農業生產結構,穩定農業生產經營[29]。
2.4 農業的六次產業化
農業 “六次產業化”作為現代農業經營的一種模式,最早由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今村奈良臣于20世紀90年代提出。當時,消費者對加工食品的購買與外出就餐日趨頻繁,餐飲支出不斷增加,但農產品的市場規模與市場價格并未發生變化。能夠提高農產品附加價值的加工業、流通業和餐飲業多位于城市,而產業匱乏的農村與農業生產者并未享受到利潤的增加。因此,為了讓農戶參與到農產品的加工、流通和服務業當中,日本各地開始了以農業作為產業軸心、以工商業為輔助、廣泛吸引社會投入、做到三產融合的 “六次產業化”(1+2+3),一方面讓農戶直接獲得食品加工收入和流通利潤,另一方面有助于打造農產品品牌、開發特色農產品、開展農產品直銷,將農業產業化與農村振興有機結合[30]。

圖1 日本六次產業化的具體形式Fig. 1 Description of sixth industr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Japan
農村資源同產業的結合是農村地區進行六次產業化的基礎[31]。六次產業化的具體形式如圖1所示。首先,與飲食相關的六次產業化最為普遍。在農業生產部門,農協指導農戶根據市場需求和食品加工需求,轉變生產方式,生產高品質農產品和適于加工的農產品;在工業加工部門,采用新技術保證加工環節中食品品質與口感,同時引進HACCP等認證體系,確保加工環節的安全衛生;在流通與銷售環節,廣泛采用農產品直營店、農超對接、交通樞紐特產店等銷售方式,擴大農產品及加工品的銷路,并在商品包裝上附上原產地標識,加深消費者對農產品與農村的印象。
其次,農業與觀光產業融合,共享農場、體驗農場、觀光農場、農家餐館和農家民宿等新型農業經營形式不斷涌現,既能避免農地撂荒、提高農地利用率與生產率,又能創造出新的旅游需求,傳承農耕文化,保護生態環境。
最后,依托日本發達的醫藥研發生產體系,日本政府開展“醫福食農聯合”,促進醫療、社保等相關產業與農業合作,在生產環節鼓勵農戶種植藥用作物,在加工環節依靠藥品生產企業開發功能性食品、醫療看護食品、其他特殊醫學用途配方食品及中成藥,并以新鮮安全的農產品和醫療食品為基礎,在生態環境優越的農村地區設立養老院、療養院,開展醫療養護健康產業。為了保障六次產業化的穩步推進,日本政府于2008年頒布《農商工聯合促進法》、2010年頒布《六次產業化法》,并于2012年成立農林漁業成長產業化支援機構,設立農林漁業成長產業化基金,為六次產業化進行融資與經營提供必要的支援。
根據日本農林水產省網站2017年8月份公布的六次產業化綜合調查的最新數據可知,2015年六次產業化相關銷售額為1.97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 160億元)。其中,農產品直營店的銷售額為9 974億日元,農產品加工增加額為8 923億日元,休閑農業營業額為378億日元。自2010年正式開始開展六次產業化以來,農業生產相關活動的年均銷售額的增速達到18.4%。從總體來看,2016年農業·食品關聯產業的生產總值為115.96萬億日元。其中,農林漁業的初級農產品產值為12.7萬億日元,占比11%;農產品流通業產值32.68萬億日元,占比28.2%;食品制造業產值37.68萬億日元,占比32.5%;餐飲業產值為28.53萬億日元,占比24.6%。綜合來看,在與農業和食品相關產業里,第二和第三產業的產值所占比例高達89%。因此,日本政府提出農業應保持自己的主體性,鼓勵將第二、三產業所創造的附加價值,盡可能多的回流到農村,進一步使傳統的生產型農業向現代的綜合型農業產業轉變,以提高經營者的收入并有效地活用農村、山村和漁村區域的資源。
3 日本農村振興的效果與存在問題
3.1 日本農村振興的效果
日本農村振興戰略的核心是將各項工作進行整合與細分,確保所有環節得到落實;民眾、企業和政府各主體攜手并進,合作共贏;農產品附加價值的提高與農業生產成本控制相結合,設施建設與人才培養政策共同完善,質量與效率共同提高;國內國外市場并重,注重品牌的建立與差異化建設;樹立農村新形象,發揮農業農村的多功能性,使城鄉形成良好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農村的活力。日本的農村振興戰略使農村地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第一,消除了城鄉社區環境方面的差別。從基礎設施建設上看,在農村振興背景下,日本政府注重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一方面針對農田水利生產設施,廣泛開展農業基礎設施修整促進活動,提供農山漁村地域修整補貼,包括向農戶提供土地改良無息貸款、農業機械購機補貼,以及區域農產品加工、儲藏和運輸的設備工廠提供修整補貼;另一方面,為促進城市居民移居農村、增加鄉村旅游的游客人數,以改善農村的生活環境為中心,日本政府提供農山漁村振興項目支援補貼以完善交通、民宿、觀光農園、飲食店和零售商店等的基礎設施建設。因此,農村地區的生產和生活等基礎設施方面已趨于完善,與城市差別不大,2016年到訪農村的游客高達2 404萬人。
第二,增加了農民收入并促進了青年勞動力參與農業經營。根據日本農林水產省2017年發布的《農業經營統計調查》可知,2016年日本農戶戶均年收入為521.2萬日元,同期全國戶均年收入為563.3萬日元,可見日本的農戶與城市工薪家庭收入相差不大[32]。另外,該調查顯示,2016年個體經營農戶的經營收入有了顯著提高,如與2007年相比,水稻種植戶的農業收入從184.2萬日元增加265.8萬日元,旱地作物種植戶的農業收入從688.1萬日元增加到863.2萬日元;農業企業法人的數量從8 571個增加到18 857個,其銷售收入增加了12%;農產品銷售金額為5 000萬日元以上的農業經營者的平均年齡降低到55歲,且隨著銷售金額的增加,經營者的年齡呈下降趨勢。農村振興戰略的主要成就還包括開拓了農村市場。由于日本經濟發展的動力主要來自內需,而農村的振興為農民帶來了富裕的生活,同時為農村帶來了強大的購買力,刺激了農村消費的多元化。
3.2 農村振興戰略下日本農業部門存在的問題與今后的發展
雖然日本農村振興取得巨大成就,但還有一些問題尚未解決,主要體現在:第一,在日本人口持續減少的大背景下,農業從業人口減少和農村老齡化問題依然突出(2017年日本農業從業人口平均年齡為66.7歲),農業勞動力不足始終困擾著日本農業;第二,糧食自給率也并未提高(2016年日本糧食自給率為38%),加快農業結構調整和提高糧食自給率仍為今后日本農業亟待解決的難題。盡管農村與城市在經濟水平和生活環境上已經沒有太大差別,農村產業的振興仍擋不住青年勞動力外流的趨勢。
日本正在推行的六次產業化概念也存在許多可優化的空間,目前日本仍在繼續推進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探尋六次產業化更多的可能性。現階段,日本正著力于制定大力扶持新型職業農民和培養農業接班人的政策(新規就農政策),希望從非農行業吸收青年勞動力, 以解決農業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同時,為鼓勵更多外國游客深入到日本的鄉村旅游(鄉村國際化),日本政府積極制定優惠政策,開展各種項目并積極向海外進行宣傳,如農林水產省2016年建立“SAVOR JAPAN”制度,以地方所生產的原材料烹制的“美食”為核心,配合當地的旅游資源,打造“SAVOR JAPAN”來吸引訪日游客。
4 日本鄉村振興經驗對中國的啟示
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戰略和重要組成部分,旨在全面解決“三農”問題,扎實推進新農村建設,早日實現全面小康。鄉村振興戰略全方位涵蓋了農業發展、農村治理和農民生活,是一項系統且復雜、長期而艱巨的歷史任務。為解決“三農”問題,穩步開展鄉村振興各項新舉措,制定政策時要注重科學規劃,堅持速度與質量并重。
中國和日本同為亞洲農業生產大國,在生產規模、經營方式和種養品類等方面相似度較高,也同樣面臨農業農村衰退的問題,二者的不同之處在于日本的農村環境較好、耕作方式更先進、農業產業化與市場化程度較高,但農村空心化嚴重,而中國農業資源豐富、糧食自給率高、農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大,但農村較落后。基于中日兩國農業農村的異同,參考日本農村振興成功經驗,提出中國開展鄉村振興戰略的幾點建議。
4.1 以打造區域特色農業為基礎,提高農產品附加價值
中日兩國皆為農產品生產和消費大國,農產品附加價值的提高有助于增加農民收入,也符合消費需求。日本的農業資源較貧乏,農產品品種相對較少。日本政府針對農產品制定了生產、加工、銷售和出口策略,依托其完善的農產品質量監管制度、完整的工業體系和成熟的生產工藝,重點打造地理標志農產品品牌,在保證農產品質量安全的基礎上,引入醫藥、美容、健康等產業進行精深加工,深挖農產品多種用途,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價值,在農產品品牌營銷上著重拓展農產品價值產業鏈。
中國農業資源豐富,農產品種類多。目前,從整體來看,農產品精深加工行業存在規模小、技術落后、資金和人才缺乏等問題,農業加工品的質量和檔次不高,農產品加工業發展緩慢。與日本不同的是,中國國土面積大,各地區擁有特有的自然資源和生態條件,造就了品種多樣、具有區域特色的農產品。現階段,中國應立足于地方資源的特色和比較優勢,打造區域特色農業,建立健全地方農產品質量安全體系,鞏固特色農產品生產,提高特色農產品質量水平,做大做強地理標志農產品品牌,形成優質特色農產品產區,以質量和特色為抓手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價值,推進農業綜合開發和促進農民收入提高。針對農產品的戰略設計,日本重在“精”和“深”,而中國應注重“廣”和“特”。
4.2 以激發農業發展活力為重點,培育新型經營主體
鄉村振興的核心是產業興旺,通過推廣農業產業化經營,以產業帶動農村和農民實現自我持續發展。日本農業勞動力短缺且老齡化嚴重,政府在制定農產品產供銷策略、實施城鄉交流與鄉村旅游戰略、發展六次產業化時,一方面培養地方農業帶頭人,鼓勵青年勞動力從事農業經營,另一方面推進農戶法人化,培養具有市場競爭力的農業企業,并強化農村集體生產概念,以企業帶動村落共同參與產業建設,達到優化農業生產結構,穩定農業生產經營的目的。
在中國,由于農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轉移,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成為農村土地流轉的受讓主體。為實現農業產業化經營,應發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帶頭作用,組織并引領小規模分散農戶參與生產。現階段,種養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和龍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不斷涌現,政府也出臺了《“十三五”全國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發展規劃》,加強職業農民培訓,培養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以實現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推進一體化發展的目標。但是,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新型職業農民的作用不應僅限于構造現代化產業經營體系,還應結合鄉村振興戰略,從產業發展上升到農村整體發展的高度,在進行產業化經營的同時,也應投身開發區域性資源、打造農村區域品牌、創建宜居鄉村等活動之中并帶動廣大農民共同參與建設,汲取和發揚群眾智慧,使“以大帶小”、“以點帶面”的榜樣效應從生產到生活實現全方位覆蓋,通過產業興旺來達到區域興旺的目的。
4.3 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抓手,夯實都市綠色農業發展的基礎
日本在實施農村振興戰略時,十分注重城市與農村的交流,從教育、體驗、旅游等層面入手,以新鮮的農產品和良好的自然景觀為中介,引導城市居民移步農村,接觸農業,感受自然。加之日本國土面積小,在布局完善的交通體系支撐下,城市與農村間的通行時間被大大縮短,城市居民出行方便,積極響應政府“體驗三農”的號召。與日本不同的是,中國國土面積廣闊,城市與農村之間距離較遠,城鄉交通一體化尚未實現。要實現城鄉交流,在繼續發展高質量鄉村旅游的同時,還應著力打造都市綠色農業,為城市居民創造就近接觸體驗農業的機會。
發展都市綠色農業,建設高科技農業園區、觀光農園和教育農園等集生產、觀光和教育功能為一體并能同時推進一二三產業有機融合的都市綠色農業產業示范基地,首先拉近了農業與城市居民的距離,使城市居民對于農業農村的參觀體驗活動變得容易,為農業產業升級創造先決條件;其次,該基地可向城市提供農產品,減少了農產品流通的環節和成本,保證了農產品的新鮮度,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有效對接,讓農業生產者能快速掌握城市市場需求情況并及時進行生產經營上的調整,由“生產導向”向“消費導向”轉變,為消費者提供個性化、高品質的農業商品;最后,依托城市的科學技術與人才資源,促進農業技術創新和可持續集約發展,夯實農業產業基礎,實施旅游與教育產業差異化運營,走產出高效、產品安全、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都市綠色農業發展道路,為城市增綠,實現城鄉融合和都市綠色農業發展有機銜接,利用城鄉融合新途徑實現鄉村振興。
4.4 以提升鄉村自治能力為重要內容,健全鄉村治理體系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須在鄉村治理體系建設上深入著力。在日本農村治理的過程中,農協功不可沒。農協以行政村為基本單位,通過縣級聯合會及全國中央會的多層網絡將全國農民聯合成一個整體。農協不僅在生產和生活上給予農民指導,也是國家政策的執行者,同時又代表農民群體來爭取政府的各項支持,是政府與農民之間的紐帶。日本農協與行政系統形成了一種相互合作的模式,在日本農村治理上發揮了巨大作用。同時,日本農村振興戰略里包含了相互扶助系統,強調集體主義,即在基層杜絕農民孤立的狀態,號召農民融入集體,結成生產、生活、人際交往上的互助網絡,在地區層面,促進農村與農村之間的橫縱向聯合發展。
中國可以借鑒日本農協發展的經驗,提升鄉村自治能力,健全鄉村治理體系。十九大報告將“治理有效”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之一,中國需要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在尚未建成區域性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當下,應加強村集體經濟組織建設,推進村級、鎮級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改革,全面推行村經分離,充分發揮村兩委作為連接政府與村民的紐帶,提高村民政治參與度和提供社會化服務的積極性,還要注重發揮村集體經濟組織在促進村民就業增收、提高村民福利等方面的作用。
相比日本,中國的農村還面臨著貧困問題。中央政府提出,脫貧攻堅要與鄉村振興有機結合。扶貧首先要“扶志”,要從根本上喚醒農民努力生產、改造鄉村的意愿,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挖掘鄉鎮政府、村兩委、村民個人以及各種民間組織的治理潛能,做到還權于民,培育和保護鄉村社會的自治能力,激發農民主人公意識,才能進一步推動農民積極主動參與鄉村建設,凝聚起振興鄉村的內部力量,使農民主體成為鄉村振興的助推器。
4.5 以重塑鄉村風尚為保障,復興鄉村文化
鄉村文化的保全和傳承是鄉村振興戰略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日本政府為此頒布了《農山漁村休閑法》,以保護鄉村文化、弘揚地方民俗特色為出發點,打造成熟的農村旅游觀光商業模式,將鄉村文化振興寄于國民的休閑活動中,并與農村振興有機結合。同時,日本通過鼓勵城市居民深入農村參加農業體驗、農業學習等活動,強化各行業、各年齡層的城市居民對農業農村文化生活的再認識。
基于日本的成功經驗,中國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重視挖掘本地的人文資源、保護鄉村歷史文化,傳承和弘揚民間藝術等非物質文化遺產,采取鄉村文化振興策略。基于各鄉村的民俗文化特色,探索具有可實踐性的“風景+文化”式的農村旅游商業模式,在擴展休閑活動多樣性的同時,帶動農村的經濟發展。同時,鑒于目前中國學生集體出游難,可鼓勵農耕文化教育走進校園,建設農業教育和體驗實驗室,增強農業的趣味性,引導學生參與農業科普與農事體驗,使學生了解農業生產概況,增加對“三農”的認識和情感。此外,還應豐富農民文化生活,組織開展形式多樣的科技普及和文體娛樂活動。以衛生創建為載體,組織農民參與環境衛生綜合整治活動,提高農民群眾的整體素養,使鄉村呈現整潔有序、地方特色突出、勤勞樸實、熱情友好的鄉村新風尚。
4.6 以美麗鄉村建設為引領,打造生態宜居新農村
良好的生態環境是鄉村振興的重要標志,強化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改善農村環境、將農村改造成與城市無差別的宜居地是日本振興農村的首要任務,也是其成功經驗之一,為農業產業、旅游產業和醫療康復產業的生成發展奠定基礎。
借鑒日本的經驗,中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在尊重農村地區現狀和農民意愿的基礎上,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如修整道路,推進互聯網建設,加快水電氣增效擴容改造,加強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發展科教文衛事業,實施環境治理等。推進城鄉基礎設施互通互聯,創新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運行管理機制,積極引導社會資本參與農村公益性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農村留守兒童、婦女和老人的關愛服務體系建設,同時也為農民工返鄉創業提供良好的硬件支持與創業環境。此外,要充分調動村民參與實施振興戰略的積極性,促使農村居民對本地資源再認識并培養地區建設意識,激發廣大村民參與宜居鄉村建設的熱情,努力把農村建設成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農村。
5 結語
日本的農村振興戰略起步較早,積累了一定的先進經驗,也在發展的過程中暴露了一些問題,本文通過研究日本農村振興戰略的具體做法和優化方向,對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規劃布局與實施路徑提供參考借鑒。對于人口數量多、國土面積大的中國而言,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既有挑戰,也具有長遠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各地在制定和實施鄉村振興規劃過程中,以打造區域特色農業、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推進都市綠色農業發展、健全鄉村治理體系、復興鄉村文化和改善鄉村生態環境等為抓手,因地制宜打造農產品品牌、創新農業發展技術、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有序引導社會其他產業與農業有機結合,延伸農業產業鏈,深度挖掘農產品附加價值,優化鄉村產業結構,激發農業發展新動能,打造適應市場需求的農村新產業和新業態,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美好愿景。
參考文獻:
[1] 秡川信弘, 長谷山俊郎. 農業·農村の多面的機能の內部化と地域活性化—三重県阿山町の農事組合法人をコアとする事例から—[J]. 農業経営研究, 2000, 38(2): 87-90.Seikawa S, Hasegawa T. A case study on internalization of rural of multifunctional value and vitalization by using local resources[J].Japanese Journal of Farm Management, 2000, 38(2): 87-90.
[2] 小田切徳美. 農村地域再生の課題[R]. JA総研レポート,2007(2): 8-10.Odagiri T. Issues of rural regeneration[J]. JA Japan—Cooperative General Research Institute Report, 2007(2): 8-10.
[3] 石田一喜. 地方創生と連動して進む農業の取組み[J]. 農林金融, 2016, 69(2): 36-48.Ishida K.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linked with regional creation[J].Monthly Review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y Finance,2016, 69(2): 36-48.
[4] 盛田清秀,梅本雅,安藤光義, 等. 農業経営の規模と企業形態—農業経営における基本問題[M]. 東京:農林統計出版, 2014.Morita K, Umemoto M, Ando M, et al. The Scale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and Corporate Form - Basic Problem in Agricultural Management[M]. Tokyo: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tatistics Publishing Inc, 2014.
[5] 谷口憲治. 集落営農の「6次産業化」と「コミュニティ·ビジネス」による農村振興[J]. 農業と経済, 2012, 78(5): 24-36.Kanji T. “Sixth industrialization” of community farming and“community·busin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J].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s, 2012, 78(5): 24-36.
[6] 金洪云. 日本的農村振興政策[J]. 中國黨政干部論壇, 2006(4):42-44.Jin H Y.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of Japan[J]. Chinese Cadres Tribune, 2006(4): 42-44.
[7] 譚海燕. 日本農村振興運動對我國新農村建設的啟示[J]. 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4, 23(5): 25-28, 92.Tan H Y. The enlightenment of Japan’s rural revitalization movement on China’s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J].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14, 23(5): 25-28, 92.
[8] 楊希. 日本鄉村振興中價值觀層面的突破:以能登里山里海地區為例[J]. 國際城市規劃, 2016, 31(5): 115-120.Yang X. The exploration of values i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Japan: A case study of Noto’s Satoyama and Satoumi[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6, 31(5): 115-120.
[9] Christopher R. Cultu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erritorial rural development[J]. Sociologia Ruralis, 1998, 38(1): 3-20.
[10] Gary P G, Anna H, Adam D, et al. The role of loc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 in rural America[J]. Rural Sociology, 2002, 67(3):394-415.
[11] Mohammed N, Lee W B. Role of cooperatives in rural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south nations nationalities and people region, Ethiopia[J].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2014,4(19): 32-39.
[12] Kim J. The meaning of differentiation in rural development projects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resident assessment[J]. Land Degradation & Development, 2015, 21(2): 79-90.
[13] Qongo S C. 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rural tourism to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strateg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 case study on the Ukhahlamba district-Senqu municipality in South Afric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 2013, 413(1):68-76.
[14] 李銅山. 論鄉村振興戰略的政策底蘊[J]. 中州學刊, 2017(12):1-6.Li T S. On 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vitalization[J].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2017(12): 1-6.
[15] 葉興慶. 新時代中國鄉村振興戰略論綱[J]. 改革, 2018(1): 65-73.Ye X Q.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China’s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new era[J]. Reform, 2018(1): 65-73.
[16] 黨國英. 振興鄉村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J]. 理論探討, 2018(1):86-91.Dang G Y. Revitalizing the countryside and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modernization[J].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2018(1): 86-91.
[17] 張宇. 未來五年農村振興的策略與路徑[J]. 河南社會科學,2018, 26(2): 21-27.Zhang Y. Research on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J]. Henan Social Sciences, 2018, 26(2): 21-27.
[18] 張軍. 鄉村價值定位與鄉村振興[J]. 中國農村經濟, 2018(1): 2-10.Zhang J. Village value orient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J].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8(1): 2-10.
[19] 李國祥. 實現鄉村產業興旺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的若干重大關系[J]. 中州學刊, 2018(1): 32-38.Li G X. Exploration on some important relations in realizing the prosperity of the rural industry[J].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2018(1): 32-38.
[20] 王俠. 發展“三位一體”綜合合作加快打造為農服務大平臺[J].求是, 2017(3): 48-50.Wang X. Developing the “Trinity”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accelerating building a large platform for agricultural services[J].Qiushi, 2017(3): 48-50.
[21] 曾福生, 蔡保忠. 以產業興旺促湖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現[J].農業現代化研究, 2018, 39(2): 179-184.Zeng F S, Cai B Z. Realizing 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of Hunan by promoting rural industrialization[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8, 39(2): 179-184.
[22] 杉浦禮子. 地域ブランド構築による地域活性化と効果に関する考察[R]. キャリア研究センター紀要·年報, 2017(3): 19-24.Reiko S. Consideration on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and effect through regional brand building[R]. Career Research Center Bulletin·Annual Report, 2017(3): 19-24.
[23] 尾室義典. 農山漁村活性化法案のねらいと手法[J]. 農業と経済, 2007, 73(6): 13-22.Yaimi O. The aim and method of village activation bill[J].Agriculture and Economics, 2007, 73(6): 13-22.
[24] 千葉諭, 信太道子, 新井俊裕. 農業競爭力強化支援法案について:生産資材価格の引下げと農産物の流通·加工の構造改革[J]. Research Bureau論究: Journal of the Research Bureau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4, 2017(12): 277-295.Satoshi C, Michiko S, Toshihiro A. Bill on support agricultural competitiveness: Reduction of production material price and structural refor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distribution·processing[J].Journal of the Research Bureau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14, 2017(12): 277-295.
[25] 雜賀慶二. 森山裕.攻める日本のコメと農林水産業:品質と加工技術で世界最高の農産物を海外へ広めるために[J].Voice, 2016(6): 132-141.Hiro M, Yuri M. Japan’s rice and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 sheries industry: To spread the world’s best agricultural products overseas with quality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J]. Voice, 2016(6): 132-141.
[26] 下渡敏治. 食品輸出拡大への新たな挑戦と輸出促進の課題[J].農村と都市をむすぶ, 2016, 66(10): 6-13.Toshihiro S. New challenges to expanding food exports and challenges of export promotion[J]. Rural and Urban Areas, 2016,66(10): 6-13.
[27] 小沢亙. 地方創生と農村振興に向けた取り組みの現狀と課題:平成27年度農業白書を踏まえて[J]. NOISAI, 2016,68(9): 12-21.Ozawa T.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efforts toward regional cre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nnual report on food,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Japan FY2015[J].NOISAI, 2016, 68(9): 12-21.
[28] 大石卓史, 大南絢一. 生物多様性に配慮した農業由來の農産物·加工品に対する消費者選好:品目別の価格プレミアムとその規定要因[J]. フードシステム研究, 2015, 22(3): 287-292.Takashi O, Aya O. Analysis of value recognition and features of biodiversity - friendly agriculture perceived by urban residents[J].Journal of Food System Research, 2015, 22(3): 287-292.
[29] 山藤篤, 香月敏孝. 農業生産法人を核とする農村活性化の新展開(小さなまちの戦:地方創生とまちづくり[C]. 地域活性學會研究大會論文集8, 2016(9): 210-213.Atsushi Y, Toshitaka K. New development of revit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rporation as a core (Challenge of small town: Regional creation and town planning)[C]. Journal of the Japan Associ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Vitalization 8,2016(9): 210 -213.
[30] 室屋有宏. 6次産業化の現狀と課題─地域全體の活性化につながる「地域の6次化」の必要性─[J]. 農林金融, 2013(5):302-321.Yuhiro M.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sixth industrialization—Necessity of “regional six” leading to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entire region—[J]. Monthly review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 shery fi nance, 2013(5): 302-321.
[31] 山下雄. 業界の動向6次産業化の現狀と事業成功に導くためのポイント[J]. JAS情報, 2017(12): 7-10.Yamashita Y. Present state of industry trends on the sixth industrialization and points of leading business success[J]. JAS Information, 2017(12): 7-10.
[32] 農林水産省. 農業経営統計調査報告[EB/OL]. (2017-12-21)[2018-02-16]. http://www.maff.go.jp/j/tokei/kouhyou/noukei/index.html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of Japan. Report of statistical survey on farm management and economy[EB/OL]. (2017-12-21)[2018-02-16]. http://www.maff.go.jp/j/tokei/kouhyou/noukei/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