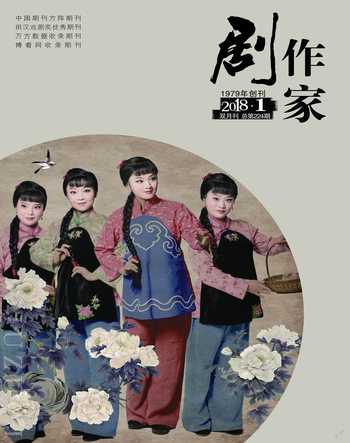蔣孝《舊編南九宮譜》編纂特點芻議
曲譜在中國古代戲曲創作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它是劇作家、曲作者填詞制曲所依據的范本。明嘉靖間人蔣孝編纂的《舊編南九宮譜》[1](以下簡稱《蔣譜》)是現存最早的南曲譜。它一方面在目錄中保存了陳、白二氏所傳的《十三調南曲音節譜》和《南九宮譜》,另一方面它也影響了后世如沈璟《增訂南九宮曲譜》(以下簡稱《沈譜》)等曲譜的編纂,故而蔣孝此書在曲譜史上開創之功不可謂不大。本文擬從兩方面來論說《蔣譜》在編纂方面的特點。
一、集曲著錄方式的創新
集曲是南曲中普遍運用的一種曲調變化方式,它通過摘取若干支曲牌中的若干樂句,來組成一支新的曲牌。宋元以來的南曲實踐中已產生了許多集曲,《蔣譜》亦收錄有不少這類曲牌(見表1)。
集曲的曲文如何著錄,在蔣孝之前并無現成的曲譜可參考,《蔣譜》對集曲的處理方式也體現了蔣孝的編輯智慧。茲舉【正宮過曲·錦庭芳】【南呂過曲·五樣錦】【商調過曲·鶯集御林春】三例以說明之。
錦庭芳 錦纏道頭、滿庭芳尾
向名園,對韶華風光儼然,花柳競爭妍。折一枝嬌滴滴海棠新鮮,可人處花如奴少年。○咱這里為情人戀芳塵,虛度了青春。早早從人愿,告天天可憐見,早交我成就了好姻緣。
五樣錦 臘梅花、香羅帶、刮古令、梧葉兒、好姐姐
姻緣將謂五百年眷屬,十生九成歡聚。○經艱歷險,幸然無虞也。止望否極生泰禍絕受福。○末后,尚有如是苦。○急浪狂風。○風吹折并根連枝樹,浪打散鴛鴦兩處孤。
鶯集御林春 鶯啼序、集賢賓、簇御林、春三柳
恰才的亂掩胡遮,事到如今漏泄。○姊妹心腸休見別,夫妻上莫不有些周折。○教我難推怎阻,我一星星對伊仔細從頭說。○姓蔣名世隆,中都路是家,是我兒夫授儒業。
《蔣譜》將不同來源的曲牌用符號○區隔,結合曲牌后的小注,其曲牌組合形式可謂一目了然。唯其如此,《蔣譜》對填詞作曲者方才能起到示范的作用,而且對集曲中不同曲調的區分也體現了蔣孝的曲學素養。
《蔣譜》對于集曲的標注方式是具有創造性的,而這一方式在《沈譜》中也被吸收與繼承,茲舉《沈譜》【南呂過曲·五樣錦】為例:
五樣錦
【臘梅花】因緣將謂是五百年眷屬,十生九成歡聚。【香羅帶】經艱歷險,幸然無虞也。指望否極生泰禍絕受福。【刮古令】末后,尚有如是苦。【梧葉兒】急浪狂風。【好姐姐】風吹折并根連枝樹,浪打散鴛鴦兩處孤。
可知,《沈譜》關于集曲的著錄方式無非是在曲文中標示出了每個曲牌名,其本質與《蔣譜》并無區別。
二、小注中所反映的蔣孝的曲學思想
(一)《舊編》目錄即陳、白二氏所藏《南九宮譜》
王古魯《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之蔣孝〈舊南九宮譜〉》一文判斷《舊編九宮譜》的目錄即是陳、白二氏所藏《南九宮譜》目錄。他說:
蔣氏所謂之陳、白二譜,名雖為譜,實為目錄,而蔣譜則由蔣氏依據此目錄。目錄原為陳、白二譜中之《南九宮譜》。蔣氏于每調各譜一曲時,具有或種理由,而作此有系統的省略及增出,但仍存舊譜面目,未撰新目。[2]
王古魯的意思是《舊編南九宮譜》現有之目錄保留了陳、白二氏所藏《南九宮譜》的原貌,而《舊編南九宮譜》的正文則是以《南九宮譜》為基礎,由蔣孝根據實際情況適當增刪后的結果。因此,通過兩者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出蔣孝具體做了哪些調整。王文指出《蔣譜》目錄中曲名與各調所譜之曲名不相符者多達三十八處,又指出總目錄所載曲目與譜中所收之曲辭不相一致者十二處。然而,王古魯著此文時所參考的是何鈁刻本《舊編南九宮譜》,對比蔣孝原刻本,何本舛誤頗多,王氏援此為據,紕繆難免,茲以嘉靖二十八年蔣氏原刻本重新做一番考證。(見表2、表3)
據表3可知,蔣孝原刻本總目錄與譜辭前曲名有出入者實際共有十三處:【傍妝臺】作【傍妝臺犯】、【大勝樂】作【大圣樂】、【金絡索】作【金落索】、【琥珀貓兒墜】作【琥珀貓兒】、[賽官音】作[賽觀音】、【四國朝】作[四國朝前】、【玉井蓮】作【玉井蓮后】、【古江兒水】作【古江水兒】、【山東劉袞】作【山東劉滾】、【蝦?序】作【絮蝦?】、【朝元歌】作【朝元歌過】、【玉胞肚】作【玉抱肚】、【蛤?序】作[絮蛤?】。這些不同處大多可解釋為“抄錄時之筆誤或脫漏”[4]。唯【四國朝】與【玉井蓮】兩支曲牌似可進一步討論。
(二)《蔣譜》小注為蔣孝所撰
《蔣譜》【雙調引子】中【四國朝】【玉井蓮】兩支曲牌在正文中作【四國朝前】與【玉井蓮后】。
【四國朝前】漫說漫說風流的,如何來吾手下逞。更有更有風流的,如何敢僭稱。
【玉井蓮后】終朝忍冷擔饑,又未知何日是了。
查《沈譜》中這兩支曲牌的著錄方式與《蔣譜》相同,并且沈璟在[四國朝前】曲辭后有注云:
舊譜于題下注一“前”字,此四句想是前半段耳,或非全引子也。《彩樓記》:“彩樓彩樓高結起”二句正是此調,而今人皆以過曲唱之,誤矣。嗟乎,《琵琶記》之【鳳凰閣】猶以過曲唱之,況《彩樓》乎。[5]
沈氏在【玉井蓮后】曲辭后則注云:
舊譜于題下注一“后”字,而古本《琵琶記》亦刻作【玉井蓮后】,但不知全調幾句耳。舊譜“忍”字上有“終朝”二字,今依古本不用。然此二句又不協韻,不可曉也。[6]
根據沈璟的說法,也可知原刻本正文中把“四國朝”改成“四國朝前”,“玉井蓮”改成“玉井蓮后”是蔣孝有意為之,而非目錄中漏刻了“前”“后”兩字。
然而這兩個曲牌在實際使用中,題作【四國朝】【四國朝前】【玉井蓮】【玉井蓮后】的情況都存在。請看如下例子:
早于《蔣譜》的用例有《宦門子弟錯立身》有【四國朝】:
【四國朝】聽得聽得人呼喚,特特來此處。[7]
晚于《蔣譜》的用例有沈璟《埋劍記》第三十三出《狂奔》:
【四國朝前】路途路途多風景,早來到魏州傳命。[8]
張四維《雙烈記》第二十一出《乞恩》:
【四國朝】君父艱危日,正人臣扼腕時。
張琦《詩賦盟傳奇》第十九出《大宴》:
【四國朝前】(凈、老旦扮上)(凈)漫說漫說英雄的,如何來庭下。(老旦)更有更有英雄的,歡騰共拜稱。[9]
《黃孝子傳奇》第六折《逼媾》:
【玉井蓮后】哈噋是我掌管,聽得堂前呼喚。
《張子房赤松記》第十六出《夜宴》:
【玉井蓮】偏是良宵,有日有花有酒。
《重校埋劍記》第三十出《惜別》:
【玉井蓮后】他鄉老婦嬌兒,又誰知余生在此。
《弄珠樓》第二出《泊緣》:
【玉井蓮】觀光上國早辭家,濟濟方盤并駕。
《長生殿》第十三出《權哄》:
【玉井蓮后】寵固君心,暗中包藏計較。
通觀這些用例,可知明清兩代曲家早已不清楚【四國朝】【玉井蓮】全調為何。為弄清這兩個曲牌的原初形態,這里有必要對其來源做一番梳理。
在《教坊記》中記載的唐代教坊曲有【朝天樂】【西國朝天】,任半塘《教坊記箋訂》以為【四國朝】與他們有一定淵源關系,他在【西國朝天】后有箋注:“北宋宣和末,汴京多歌藩曲,曰【異國朝】【四國朝】【六國朝】等,應仿此(指【西國朝天】)取名,至南宋,【四國朝】【六國朝】已演為傀儡戲;在盛唐,未知如何。”[10]此處任氏所謂的淵源關系僅是由于曲名相像而給出的推測,至于其曲辭格律則未必有關[11]。其中任半塘所謂的傀儡戲,見周密《武林舊事》卷二:“至節后,漸有大隊如四國朝、傀儡。杵歌之類,日趨于盛,其多至數千隊。”[12]可知“四國朝”是南宋末年臨安節日活動中表演傀儡戲的舞隊名稱。同卷《舞隊》一條中,也錄有名為《四國朝》的隊伍[13]。另外,同書卷十《宋官本雜劇段數》里也記有《四國朝》的名目[14]。《四國朝》是“以歌曲演之”[15]的宋雜劇殆無疑問。而【四國朝】純粹作為曲名的記載則見于南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中:“先君嘗言,宣和間客京師,時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異國朝】【四國朝】【六國朝】【蠻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時士大夫亦皆歌之。”[16]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亦引了這段話,并云:“今南北曲中尚有【四國朝】【六國朝】【蠻牌兒】,此亦蕃曲,而于宣和時已入中原矣。”[17]
通過上述對【四國朝】這一曲牌源流的梳理,我們可以知曉【四國朝】在元代以前無論作為雜劇名抑或歌曲名,都不會在其后加上“前”字。這可與上文所舉《張協狀元》中的用例相印證。
綜上所述,大抵可以推斷在陳、白二氏所提供的《南九宮譜》中兩個曲牌原本的確題作【四國朝】與【玉井蓮】,而蔣孝也知道自己為這兩個曲牌所選的曲辭并非全調,只是當時已無法找到【四國朝】與【玉井蓮】完整的曲辭。于是,蔣孝的處理方式就是在目錄中保留原初【四國朝】【玉井蓮】兩個曲牌,在正文中則另注明“前”與“后”。而在明末以后的戲曲作品中多用【四國朝前】大抵是受了《沈譜》題作【四國朝前】的影響。
既然現存的嘉靖二十八年刊本《舊編南九宮譜》書前目錄保留了陳、白二氏的《南九宮譜》,而蔣孝對于諸如【四國朝】等一些特殊問題采取了于正文題下加小注的方式解決,因此可生出一問——嘉靖本《舊編南九宮譜》目錄中那些小注是陳、白二氏所傳譜中原有的,還是蔣孝加注上去的呢?
同為蔣孝編纂的《新編南九宮詞》[18]可以為解答這一問題提供一些線索。
先看《十三調譜》【高平調】下面一段注文:
與諸調皆可出入。其調曲名皆就引各調曲名合入,不再錄出。其六攝十一則,皆與諸調同。用賺,以取引曲為血脈而用也。其“過割搭頭”圓混,自有妙處。試觀“畫眉人遠”“夢回風透圍屏”二套可見。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第一,“不再錄出”似乎應是編纂者(即蔣孝)的口吻。
第二,其中提到“夢回風透圍屏”一套,今天我們可以考察出它由如下曲牌組成:【三臺令】【畫眉畫錦】【畫錦畫眉】【簇林鶯】【黃鶯兒】【螃蟹令】【一封書犯】【馬鞍兒】【皂羅袍】【梧葉兒】【水紅花】【尾聲】。其中【畫眉畫錦】和【畫錦畫眉】兩支曲牌屬于【高平調】[19]。
其中【畫眉畫錦】“霍起披衣襟”一支被多本曲集或曲譜收錄,并且收錄此調同時還標明所屬宮調的有如下幾種:
如表所示,在明后期,【畫眉畫錦(畫眉序犯)】這個曲牌基本都被各種曲集、曲譜歸入[黃鐘宮】,并不提及[高平調】。而只有《新編南九宮詞》中特別說明它“入高平調”,這恰恰與《十三調譜》中的歸類一致。《新編》注出這四個字,很可能是因為《十三調譜》【高平調】下的這段注文就是蔣孝所寫,所以他才能在編《新編》時同樣注明【畫眉畫錦】“入高平調”。
第三,這首【畫眉畫錦】的作者《新編》作“燕參政”,《吳歈萃雅》《詞林逸響》《南音三籟》等書俱作“燕仲義”,所指當是一人。參政是明代的官名:“明朝各布政使司置,從三品,位在布政使下。”[20]由此可知,既然這首【畫眉畫錦】是明人的作品[21],那么這段文字就不可能是《十三調譜》原有的。
另外,《十三調譜》【南呂調·浣沙溪】下有注云:
《草堂詩余》作【浣溪沙】者,非。
《草堂詩余》是南宋人編輯的一本詞選,這本詞選在明代極為流行。清人王昶《明詞綜序》中說:“及永樂以后,南宋諸名家詞皆不顯于世,惟《花間》《草堂》諸集盛行。”[22]《草堂詩余》對明代的劇作、曲選、曲論都產生了影響[23]。因此,寫出這條小注的是明代人的可能性也比較大。
綜合上述幾點可以得出如下結論:這些小注并非原來《九宮譜》《十三調譜》所有,而是蔣孝在刊印的時候加上去的。相對于整本《舊編南九宮譜》來說,這些小注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通過對其辨析,進而弄清楚了它們是蔣孝所寫的這一事實之后,可以讓我們更加確定兩點:一、蔣孝雖然沒有曲學論著存世,但他并非不諳曲律,他的曲學思想已經融匯、包容在他所編刻的曲譜、曲集之中;二、因為注文是蔣孝所撰,其中必然帶有個人化的色彩,以及時代的信息。故而在分析這些注文時,我們必須客觀地看待,不能徑直通過否定這些注文,來否定《九宮譜》《十三調譜》[24]。
注 釋:
[1]該書現存版本有嘉靖二十八年蔣孝三徑草堂原刻本、明萬歷二十二年何鈁翻刻三徑草堂刊本
[2]王古魯:《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之蔣孝〈舊南九宮譜〉》,收于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1月,第435頁
[3]下文表格“何鈁刻本總目錄曲名”“何鈁刻本譜辭前曲名”為王古魯原文所列出,“蔣孝原刻本總目錄曲名”“蔣孝原刻本譜辭前曲名”為本文補入
[4]王古魯:《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之蔣孝〈舊南九宮譜〉》,收于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1月,第435頁
[5]沈璟:《增訂南九宮曲譜》卷三十,王桂秋:《善本戲曲叢刊》第三輯,臺北:學生書局,1984年8月,第622頁
[6]沈璟:《增訂南九宮曲譜》卷三十,王桂秋:《善本戲曲叢刊》第三輯,臺北:學生書局,1984年8月,第623頁
[7]《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第242頁。錢氏注云:“引子辭句可以減省,此為末二句。上句應作‘聽得聽得人呼喚,原奪‘聽得二字,今補。《九宮正始》冊九【越調·四國朝】引《王煥》,作‘更有更有風流的,可證。”
[8]《重校埋劍記》,《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明繼志齋刊本
[9]《詩賦盟傳奇》,《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明末刊本
[10](唐)崔令欽撰,任半塘箋訂:《教坊記箋訂》,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5月,第139?140頁
[11]任半塘在《教坊記箋訂》一書后附的《曲名流變表》中將教坊曲【朝天樂】、宋詞【喜朝天】、諸宮調【朝天急】、北曲【朝天子】、南曲【四國朝令】、【四國朝序】等置于同一個流變系統之中,但任氏也承認:“曲名流變于后世者,限于字面上之直接關系……名辭之流變,以直接明顯者為限。如此猶恐名雖近似而實際無關,列之難免附會之嫌。”見《教坊記箋訂》,第197頁
[12](宋)四水潛夫:《武林舊事》卷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31頁
[13](宋)四水潛夫:《武林舊事》卷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33頁
[14](宋)四水潛夫:《武林舊事》卷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58頁王國維將其列為“金元曲調”,見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第五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50頁
[15]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第五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51頁
[16](南宋)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第45頁
[17]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第十六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31頁
[18] 《新編南九宮詞》的編者問題,參見陳浩波:《蔣孝的生平及其著作》,《曲學》第二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0月,第491?495頁
[19]具體考察請見第四章第二節第三點“【高平調】之下曲牌用作【賺】”
[20] 呂宗力主編:《中國歷代官制大辭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1月,第614頁
[21]任中敏《散曲之研究》一文也將燕仲義列為明人。見任中敏著,金溪輯校:《散曲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10月,第33頁
[22](清)王昶輯,王兆鵬校點:《明詞綜》,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頁
[23]趙山林:《試論〈草堂詩余〉在明代的流傳及詞曲溝通的趨勢》,《文藝理論研究》,2010年第4期
[24]比如魏洪洲《陳、白二氏〈九宮譜〉〈十三調譜〉考原》(《社會科學輯刊》2015年第2期)一文中便以“尾聲格調”提到了明初李景云《西廂記》,作為《十三調譜》是明初產生的理由之一。但根據本節的結論,諸如“尾聲格調”下面的注文應該也是蔣孝所撰
責任編輯 原旭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