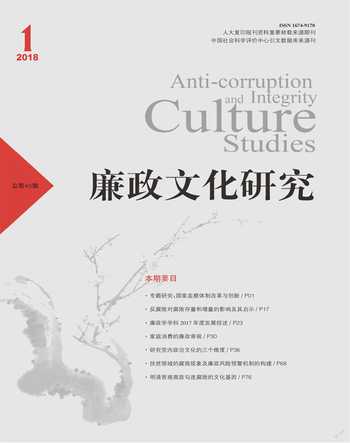明清晉商商政勾連腐敗的文化基因
韓彩英 韓斌全
摘 要:明清晉商巨賈并不是獨立發展起來的社會存在實體,而是依附明清帝國國家機器生存的商政或政商勾連一體的政治性經濟怪物。晉商好儒,但“好儒”的功利目的是顯而易見的;由于“義”與“利”之間存在必然沖突,明清商人所宣揚的“以義制利”并不具有普適價值,事實上他們也沒有普遍踐行和遵行始終。晉商“商政勾連”違法、“亦商亦官”違制(禮制),是毋庸置疑的;而晉商“助清滅明”惡劣行徑更是在根本上沖決了儒家倫理之底線。“儒商”看似高尚的標簽,其實“儒”正是明清商業大亨得以與“政”勾連的“共同文化”基礎。“儒商”實為愿與官場勾連之明清商人的總概括。此外,“好儒”之晉商常常僭越禮制,崇拜和迷戀儒“士”之奢靡的心態暴露無遺。明清晉商的可敬之處是所謂“誠信”,然而他們對于相關方的“誠信”因“人”而異,呈現出的是因“時”便宜、善惡不分、亦善亦惡的多重“選擇性”面相。
關鍵詞:商政勾連;儒商;儒家倫理;以義制利;誠信
中圖分類號:D6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170(2018)01-0076-09
學術界討論晉商衰落原因的文獻很多,切入點各不相同。其中,有不少學者認為,晉商衰落的原因是由于“政商不分”或者“商政一體”造成的。例如,劉寶宏和盧昌崇認為:“明清晉商始終靠結托封建政府并為之服務而興盛,當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時,晉商也必然禍及自身。”[1]無疑,“政商不分”或者“商政一體”是造成晉商衰落的原因之一,甚至是最為基本、最為直接的原因。但問題在于,習孔孟之道“以義制利”的“儒商”,為什么會干出“官商勾結”相互利益輸送的卑劣勾當?畢竟,利益輸送、賄賂官員或商政一體利益均沾,在今天看來是違法的,在明清也是不合法的。那么導致晉商諳習且熱衷“商政勾連”這種致使自身“興也勃焉,亡也忽焉”經商之“道”的文化秉性或文化基因是什么?這是我們不得不究問的根本性問題。
一、晉商崛起和消亡的原因
正如趙榮達和郭玉蘭指出的:歷史上,“晉商是以誠信、勤勞、節儉而著稱的,應當說這也是晉商前期順利發展的根本原因,但是,晉商在后來的經營活動中卻漸漸地發現了一條謀取暴利、快速發展的捷徑——擁有特權。晉商對于特權事實上經歷了一個由偶然、無意地享受到自覺、刻意追求的過程”[2]。完珉指出,“執五百年商界牛耳的晉商,與明清的政權難分難解。”“翻檢晉商各大家族歷史,越到王朝后期,朝綱混亂綱紀廢弛,就越可見政商互結、官企不分”。[3]總體而言,歷史上的三晉普通商人“誠信、勤勞、節儉”是其本質特征和生存法寶;而三晉商人中的所謂“晉商”巨賈卻是以商政勾連方式獲得特許經營從而攫取巨額利潤崛起的。張華強指出:“明朝時他們通過為政府運輸軍糧獲取‘鹽引,曾經壟斷了巨大的商業資源;由于在明清交戰期間建立的良好關系,晉商又受到了清統治者的禮遇,被奉為‘御用皇商,最終修煉成為主宰大清經濟命脈的‘天下第一商幫。”[4]
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實行“重農抑商”基本國策,直至“晚清之際,對商業的性質與商人角色的認識仍未有根本性的變化。輕商之風氣實際上仍存在于中國社會之中”[5]。處于“重農抑商”的封建時代,面對嚴格管控,私商要想獲得生存和發展空間,不但在經營貨物范圍上,而且在經營區域——包括地方轄區和邊境國際貿易——上都須獲得官府許可或默許,阿諛賄買官家無疑是便宜之徑;而明清帝國或因戰爭或因天災財政匱乏及物資轉運難以為繼時,倚重商幫雄厚財力和無處不達的轉運能力,也是不可為而為之的現實選擇,更何況官僚可從中獲取巨額不法利益。因此,明清時期的“商政勾連”在主動性意義上是雙向的。“晉商從開中法起登上商界舞臺,由此形成不同尋常的官商關系。而他們結交官吏、謀取利益的過程就是尋租的過程。”而商政“雙方互動合作從而形成的長期合作關系就是政府與鹽商的設租-尋租關系”[6]。顯而易見,這種“尋租”是雙向的。謀取不當利益的封建商人總是在單向利用官方與官商雙向利用中交替前行。
張正明指出:“封建社會的商人大多與封建政府有著特殊關系,而山西商人尤為突出。”[7]在大清帝國如日中天之際,晉商可謂如魚得水,資本和經營規模迅速擴張。進而商政通吃,使得晉系商幫蓋過了其他所有商幫——包括徽商。“以山西票號來說,他們不但從經濟上幫助窮儒寒士入都應試和走馬上任,而且還施盡手段結交在任的王公大臣。最著名者,如蔚盛長交好慶親王,百川通交好張之洞,協同慶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粵海關監督某氏等等,可謂是‘一個成功的票號背后總有一位大官員。”[2]到太平天國后期,“晉商票號的掌柜們越來越熱衷于結交清廷的王公大臣、各地的封疆大吏,與其稱兄道弟,關系非同尋常。晉商后期喜歡通過捐輸買官,他們買官不是為了做官,而是為了以官商身份更好地獲取經營上的特權地位”[3]。依附官府、依附官員乃至亦商亦官雙重身份是晉商生存與發展的實用主義選擇。也如馮筱才指出的:“與歷朝政府為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而采取一些保護商人的政策相似,晚清政府推行其重商政策之目的在于使國家強大。商人只不過是達到這一目的的工具而已。”[5]在清王朝不思改革進取以及因外患內憂等原因走向衰落之際,倚重商人巨賈似乎成為他們的必然選擇。“晚清政府對商業的重視首先是源于財政上的需要”,“經鴉片戰爭及太平天國之役,政府愈來愈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從中央到地方,商稅成為解決難題的重要途徑。國家經濟基礎,開始由農業轉向工商,政府亦增加了對商人的仰賴”[5]。
然而,清朝末期,“晉商票號和清王朝之間的聯系越來越打成了解不開的死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辛丑條約》賠償白銀四億五千萬兩,仍然由晉商票號匯解,這是一筆難得的大生意,晉商票號從此進入了發展的極盛時期(1902~1906)。幾年后,辛亥革命爆發,晉商票號就和氣數已盡的清王朝在相互攙扶下同歸于盡了”[3]。劉可為指出:“與封建政府聯系過緊,脫離了商品經濟的土壤,使山西票號成了滿清王朝的殉葬品。”[8]其實,明清晉商的崛起和山西票號的創立和發展,本來就是以“商政勾連”為其根基的。“商政勾連”基礎一旦崩塌,其商業大廈傾覆就成為歷史必然。張華強明確指出:“作為一個稱雄數百年的商幫,晉商在清王朝滅亡后不久而衰落,與他們把自己的商業經營和政治思維完全捆綁在一起不無關系。”[4]趙榮達和郭玉蘭說,晉商票號商人“經濟上精明、政治上糊涂”[3]。其實,清末晉商并非“政治上糊涂”,而是骨子里的依附心理、商政勾連經營之道在作祟,他們心理明白,清王朝倒塌之時就是他們商業帝國坍塌之時。在八國聯軍攻陷北京之際,慈禧南下逃亡之途,晉商不惜巨資資助“老佛爺”這位大債主的逃亡之旅。對此,有些文學影視作品非常推崇晉商這一獲得巨大商機的“智慧”或曰“機謀”。然而,在筆者看來,這只不過是晉商為挽回損失、挽救命運的一場豪賭。
晉商巨賈在經營思想中充斥著政治考量,充斥著利用官方權力最大限度牟利的商業計謀。直至大清王朝覆滅,整個中國社會的“士農工商”這一封建等級觀念和基本制度依舊。晉商巨賈雖然“風光”,但并未真正改變其末等的社會等級地位。官方有違封建等級制度的政商勾連行徑,無論是腐敗官僚為謀不當利益而與商人勾肩搭背,還是封建官僚甚至朝廷為維護政治統治而屈尊與商人勾連結盟,都只是(官員)獲取非法利益和(官府)獲取經濟支撐的權宜之計。因此,明清晉商巨賈并不是獨立發展起來的社會存在實體,而是依附明清帝國國家機器生存的商政或政商勾連一體的政治性經濟怪物。“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左傳·僖公十四年》)似乎,民國開啟,封建商人跟不上社會制度的巨大變遷,跟不上經濟制度轉型的步伐。其實不然,民國已降,依靠自身商品、服務和信譽生存發展的小商小販依然生意興隆,甚至獲得巨大發展——民國民族資本家的崛起大多如此。當然,革命不徹底的不倫不類的民國,還滋生出了“四大家族”這一新型的商政勾連怪胎!
從現象上看,或者從直接原因看,明清晉商(甚至徽商)都是因封建帝國坍塌而衰亡的。在大清帝國坍塌、民國開啟國家基本經濟制度重大變革的時候,晉商的“氣數”就到頭了。當然,“徽商”之類的封建商幫與晉商一樣依靠“商政勾連”的明清富商巨賈的“氣數”都到頭了。然而,明清帝國滅亡只是中華大地上的政權更替,并非遭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消亡——就像猶太人的歷史遭遇那樣——滅頂之災。如此看來,我們在贊美晉商、徽商等明清商人“誠信文化”、“以義制利”等儒商文化的時候,不得不剖析其“生于斯”、“死于斯”的根本原因,進而剖析其“誠信文化”的種種“面相”——特別是誠信上的“腐敗文化面相”,剖析其文化基因,剖析其商業文化給中華文化、三晉文化遺留下的“負資產”及其危害。
二、晉商“儒商”標簽的文化基因
段江波和張厲冰指出:“商人對儒家倫理的態度有兩種表現,一種是‘儒賈,是用儒家倫理精神自覺規范其商業行為,其價值指向是‘儒。另一種是‘賈儒,‘以儒飾賈,把儒家倫理作為工具理性運用商業經營活動之中,目的是‘利。前后兩者的境界有天壤之別。”[9]如同徽商,晉商“賈而好儒”是不爭的事實,其表現在:第一,多延師課子,令子弟“業儒”;第二,“雅好詩書”,好學不倦;第三,老而歸儒;第四,重視和資助文教。①“賈而好儒”“是明清時期許多地區的商人共同具有的,它反映的是明清時期許多地區的商人的普遍特征。”[10]
對于明清時期為什么會有如此多的地區的商人“賈而好儒”,張明富認為:“任何行為選擇都是主客觀相互作用的產物。明清商人較為普遍的‘賈而好儒這一行為的產生也不例外,它不僅取決于他們所處的經濟文化環境,也與他們的需要直接相關。可見,明清商人較為普遍的‘賈而好儒,其原因是復雜的,需要從多角度予以分析。”在張明富看來,其原因有三:首先是文化環境方面,“由于儒學是一種占主導地位的文化,特別是與科舉制的結合,使其傳布甚廣,為人們廣泛崇信”;其次是社會生存策略選擇方面,對農業經濟的“本根”依附心理,魏晉以來的世族-地主非官方強勢士族階層社會環境認知,以及唐宋以來“科舉制度”“型塑”的士人耕讀傳統、士紳成為官方鄉村管理代理人,“規定了明清商人‘好儒的方向”;最后是商業經營本身“需要的驅動”。[10]“好儒”的功利目的是顯而易見的。段江波和張厲冰就認為,明清商人之所以體認儒家倫理并以“儒商”自居,是因為,“從明清時期的社會歷史條件分析,商業倫理秩序的建立既具有客觀現實性的功能,為其商業活動尋找社會認同提供社會倫理辯護。而商人主動賦予其商業行為以道德價值更是謀求自我尊嚴、自我認同從而達到自我辯護的目的”[9]。
明清商人如同明代蒲州商人王文顯訓誡其子所說,“夫商與士異術而同心”[11],但“許多人在經商致富后,有的用金錢威力打通馳往仕宦的道路,有的以其經商所得支持子弟奮進科場。”“在他們的文化觀念上,表現出了迷戀權力的傾向。”[12]張明富此語可謂一語中的。敬畏權力、謀取官位本來就是儒者的宿命。在儒家文化中,“商政勾連”并不是恥辱,而是其文化本質使然。
并且,儒者必仁,但為什么有時或有些“仁者”還貪婪?對此,馮兵在討論朱熹提出的“仁緣何貪”這一問題時指出,“仁者愛人”“在于其中似乎蘊含了一個道德悖論:‘仁是儒家倫理思想中最為核心和基礎、也是最重要的德性標準,但恰恰是具備了這一德性的仁善慈愛之人,卻又往往難以在財富等各種欲望面前保持警醒與理性”[13]。在朱熹看來,“仁(愛人)”而致“貪”,如果能夠清心寡欲、以“義”制“仁”,人的貪念貪欲就不會無限膨脹。然而,清心寡欲、以“義”制“仁”或仁(愛)義(善)兼修這一策略只能在純粹的儒士或儒者身上起作用——“仁愛”且“義善”之知識分子在中西方知識分子史上不勝枚舉。商人以追逐利益為其本性,“愛財”是其本性,讓他們清心寡欲何以可能?何況,如果說“義”之所以可以制“仁”,是因為“仁”與“義”都屬人心之內在修養及其衍生出的外在修為,二者之間并沒有根本性沖突,且在一個人身上完全可以是互補和相互制衡(關于這一問題可參閱學術界關于王陽明心性學說的論述)。而“義”與“利”之間存在必然的沖突;“義”是否可以制約那些溝壑難平商人的謀“利”之心,實在值得懷疑。①最起碼,對于“遵循‘王霸道雜而用之、‘儒法相漸的倫理文化”[11]的晉商而言,以“義”來制約商人牟利之心、制約一些貪得無厭商人的貪婪欲望,并不具有普適價值。況且包括晉商在內的封建商人并沒有普遍踐行和始終遵行 “以義制利”這一的商業倫理準則。
亦商亦儒的所謂“儒商”畢竟不是“儒(士)”而是“商”;商人牟利天性使然。只是,所謂“盜亦有道”,何況具有合法身份的商人。自詡為“以義制利”的“儒商”就理當“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或許,視自己為“儒”的商人做出些許不傷大雅的商政勾連之事,且如果大體上也沒有突破儒家傳統文化的基本道德底線,也許可以理解。然而,問題在于,商政勾連、相互利益輸送,這種“取財之道”在中國封建社會是合法的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對這種行為的“逾矩”違法定性是毋庸置疑的。這是其一。其二,在讀書以取士之道難以行得通的情形下,以經商獲得社會聲望,甚至獲得“士途”(亦商亦官)、獲得政治地位、獲得社會等級的提升,這種“曲線救國”的伎倆,也許有些人認為是正當的,但畢竟不合當時的體制規制——中國封建社會“商”不得為“士”是通制(唐朝開啟的科舉舉士制度明確禁止商人及其子弟參加科舉考試),僅是大清封建王朝彌補財政虧空的一種“變通之術”而已。對這種行為的“逾矩”違制定性是毋庸置疑的。特別是,一些晉商竟然將獲取官方特許軍用物資壟斷經營的這一套“商政勾連”之術用于助清滅明,甚至不惜充當間諜②。劉庭玉指出:晉商在與滿人的交往中,“充當著滿人的物資供應商和事實上的情報提供者,從物資供應的角度看,晉商在清兵入關的行動中所起的作用是吳三桂也不能起到的”[14]。顯然,“助清滅明”這種惡劣行徑有違民族情懷大義、有違“家-國”情懷大義、有違尊君愛國儒家基本倫理。這就在根本上沖決了儒家倫理之底線。這就是清代晉商的崛起和繁榮之“道”!熱衷商政勾連的晉商,踐踏法度之“矩”,僭越“士農工商”等級禮制之“矩”,種種“逾矩”行徑說明,在他們身上,儒之“道”、士之情懷實已蕩然無存,“儒”在他們身上只能說是不折不扣的“面具”而已。
盡管晉商,特別是“三晉”中小商人并非都是商政勾連之輩、貪得無厭之徒,“三晉”也的確出現過不少以儒之道(儒家倫理)規范其商業行為的儒商;“三晉”商人看重口碑,也樂于濟饑民、濟鄉民。但晉商“普遍”尚“義”的現象,并不能掩蓋晉商巨賈唯利是圖的本性。明清巨賈“儒商”的所謂“利以義制”(或“以義制利”)是“口實而惠不實”。不少所謂“儒商”見利忘義,甚至發國難財,如前述資敵(明商資滿清入侵)牟利,又如清代山西商人將“大量商業利潤轉為高利貸資本牟利”。“據《清高宗實錄》卷1255載,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河南連年欠收,‘西晉省富戶恃其素積多資,遂乘中州荒欠,前往舉利放債。近人衛聚賢說:‘明末清初,凡是中國的典當業,大半系山西人經理。”[7]可以說,之所以崛起為巨賈的晉商大多具有樂于善行也樂于惡行的兩面性。甚至可以說,晉商巨賈之所以“善行”,是為了掩蓋或“稀釋”其“惡行”以求得“善果”,是深深扎根于民間的佛教因果報應思想在起作用。
中國明清富商巨賈的道德標簽是“儒商”。“儒商”看似高尚的標簽,其實“儒”正是明清“晉商”和“徽商”等商業大亨,得以與“政”“商政勾連”的“共同文化”基礎,甚或商政、政商公開交往,公開“勾連”的“遮羞布”。由此,“貪腐成性政府無德,尋租謀利晉商失魂”[3]。
至此,不得不給出這樣一個結論:“儒商”實為愿與官場勾連之明清商人的總概括。
另外,在儒家文化中,“奢靡”并非“無良”,也是其文化本質使然。“禮制”是周代的根本制度,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一切國家-社會-家庭領域,是規范整個國家社會生活的根本準則。更是中國各個封建朝代“儒”(儒士、儒家門徒)維系其社會身份、社會地位,鞏固其既得利益或獲取封建社會地位及各種利益的制度保障。其中,“儒”所享有的特權、享有的奢華、享有的風光,是各個朝代儒士/儒生夢寐以求的人生境界。孔子以學生和追隨者眾多而風光;孟子則更上一層樓,不但因學生和追隨者眾多而風光,而且各國國君的“超豪華”禮遇、“超豪華”宴饗以及無上特權,更讓各朝各代儒士/儒生眼饞。由此也就衍生出“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車馬多如簇”、“書中自有顏如玉”的說法。儒商的奢靡并不能算到“商”的頭上,因為“商”本來是周王朝嚴厲約束之下的亡國族群的謀生職業,在其基因中難有享有特權、享有奢華、享有風光之夢想。而“儒”就大不一樣了。“儒”的思想和生活態度中始終有享有特權、享有奢華、享有風光夢想之基因在涌動。
“好儒”之晉商常常僭越禮制,崇拜和迷戀儒“士”之奢靡的心態暴露無遺。在中國傳統社會,“商人位居四民之末,備受輕賤,統治者給商人規定的生活標準連農民都不如。明清商人經商致富后,有了雄厚財力的支持,往往視禮制為無物,摹仿仕宦官僚的豪侈生活,盡情揮霍、享受,妻妾成群,美食美衣,高堂大廈。李夢陽《空同集》卷五十九《賈論》中說,經營鹽業利潤豐厚,故鹽商較其他商人尤富,‘泰者則輒楔妓女,彈鳴瑟,即肥甘綺麗,車馬珍玩諸屬與諸大貴人等矣。夫賈編戶之民也,而一旦音樂妓女奉肥甘綺麗,車馬珍玩諸屬與諸大貴人等則淫侈而易為邪。”[12]即使像祁縣喬家嚴禁娶妾,但豪宅大院、錦衣玉食卻是必須享用的。
以“儒商”面目出現,是晉商等明清商人“好臉面”的需要,更是接近官員、巴結官僚,甚或“商官兩棲”,進而增進商業利益的需要。“賤商”不這樣“自我型塑”是難以發展壯大,甚至難以生存的。在市場經濟法治環境尚不健全、尚不完備,官員尋租彌漫的時候,“商政勾連”也是當代晉商為生存發展、也為圖謀不當利益的策略選擇。可悲的是,當代“商政勾連”之商人混跡于文化圈中,混跡于官場“圈子文化”中,時常自冠“儒商”之“冕”,其心理與明清晉商別無二致。與南方許多商人(如義烏浙商等)相比,現如今的山西商人依然秉承了明清晉商“商政勾連”之糟粕“傳統”,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而那些“老虎”、“蒼蠅”也常常以拙劣書法招搖過市,未曾一睹“經、史、子、集”(實際上他們讀也讀不懂),卻開口儒學、閉口國學,似乎張揚儒學國學“修為”可以遮掩他們貪婪成性之卑鄙人格,可以遮蓋他們貪贓枉法之丑惡行徑,實在是道貌岸然毫無廉恥之心。①
三、晉商“誠信”倫理的基本面相
明清晉商可敬之處是所謂“誠信”。其市場誠信值得推崇,無論是相對于合作商家(包括商業貿易商家和產品制造商家)的誠信,還是相對于產品和服務最終消費者的誠信。然而,明清晉商的誠信還有一個得以立命生存的根本性“面相”,這就是對官員的“誠信”。這種“誠信”,一方面是以賄賂方式取得經營特許后在經營上的“守信”,這是一種看似“守法”,實質上是恪守與官員達成的經營范圍、經營模式的“君子協定”——后文將述及;另一方面是在“履約”特許經營過程中給相關官員按約定數量或獲利比例的“紅利”返還上的“守信”,這種“利益輸送”更是一種“君子協定”。當然,這種“誠信”面相并非晉商獨有,其它成功商幫也是如此。
在“誠信”的一般意義上,晉商的誠信可以劃分為對外的誠信與對內的誠信。
對外的誠信涵蓋晉商對其商業字號或錢莊組織體系之外部的各種政治經濟組織、利益集團和相關獨立個體(及其家庭)的誠信。關于晉商的對外誠信,對官員的誠信是其一,還包括對朝廷官府的誠信、對合作商家的誠信和對消費者的誠信。
對于朝廷官府的誠信是“晉商”不得不為的“信用”,是否出自“本心”、“真心”,非常值得懷疑。之所以如此說,一是因為,明清晉商對朝廷官府的誠信是官商勾連欺瞞朝廷、鉆空投機利益輸送的虛假誠信。例如,“在明朝,晉商賺得利潤的一個主要手段就是賄賂邊將,虛出實收;買通主管官吏,在糧價便宜時上交糧食,到糧價上漲時,再向政府領取糧款,不僅可以獲得可觀利潤,連貯藏的費用也不必支付;另外還有先領糧款后買糧、凈賺差價等手段”[14]。事實上,清代晉商在襄助朝廷戰事時也使用了此類伎倆。二是因為,明清改朝換代之際,晉商并沒有對大明王朝忠誠守信到底,而是在看到“滿族大清”氣勢如虹時毅然決然倒向異族,在賺取大清方面的戰事收益的同時不擇手段地“助清滅明”。明清晉商對于朝廷官府的誠信可見一斑,最起碼沒有做到有始有終、善始善終。對于合作商家的誠信,其間夾雜著奸詐和投機。商家合作上的相互傾扎、乘人之危低價兼并,在晉商發展史上屢見不鮮。不僅如此,晉商還有“重大發明”:大商家以所謂“期貨”與“現貨”雙重運作來擠壓中等規模商家利潤空間,中等規模商家擠壓小商家利潤空間,致使本小利薄的小商家的經營異常艱難。這在大糧商←→釀酒作坊←→酒品零售小商家之利益關系鏈條中尤為突出。在明清時,晉商幾乎壟斷了整個酒業生產經營鏈,在此情形下,晉商巨賈的這種發明不能不說是借“誠信”之名實行的巧取豪奪。
另外,晉商面向農產品生產供應者“買樹梢”生意當中的誠信也值得重新評價。例如,祁縣喬家等“晉商”面向貧窮農民(糧食生產者)的“買樹梢”生意。①這是一種沒有“對沖”雙向操作機制的不可逆合約②,只以數額非常有限的定金給付就壟斷了合約農民當年所生產的糧食。以之與囤積居奇合并使用,謀取暴利就是高概率事件;而貧困農民所生產糧食之收益低微也必然是高概率事件。總之,晉商巨賈極盡盤剝中小商業業主和貧窮農牧民之能事。明清晉商——特別是一些糧商和鹽商——“囤積居奇”、“哄抬物價”是他們商業經營的“常態”手段。沒有投機機會時,他們是恪守誠信的“謙謙君子”;投機機會一旦來臨,他們就充分暴露出追逐暴利的本性。盡管,在遭遇災荒之年,晉商巨賈會“開棚施粥”做出樂善好施的姿態,但“開棚施粥”的開銷只是乘天災人禍之投機生意所賺取的巨額利潤之九牛一毛耳。
對于普通消費者而言,“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等商業行為的確是誠實守信的具體表現,也可以說晉商巨賈在直面消費者時是恪守誠信的①。但無法否認的是,向災民發放高利貸以及“囤積居奇”糧食、哄抬糧價等行徑會最終從根本上損害普通消費者的利益,特別是在“食尸”甚至“易子相食”的災荒年份。這些看似兩廂情愿的商業誠信,其實都沖決了孟子所提倡的“良知”之底線。雖然在對普通消費者方面的商業倫理、商業誠信未發現問題,且口碑良好,但這也只能被看作是為了商業生計的權宜之計,加之乘人之危的商業投機和擇人之困的商業欺詐行為,根本無法認定晉商巨賈在面對普通消費者時是恪守誠信的。
總之,在對外商業交往中,如劉建生所說:“晉商之所以遵循‘以義制利,誠信經商,是權衡得與失的結果。”[6]所權衡的“得與失”的核心就是經濟利益的最大化。
對內的誠信涵蓋晉商對其商業字號或錢莊組織體系之內部的雇員(包括掌柜及店員/伙計)、對家族成員和本籍鄉親的誠信。
“三晉”商人心胸狹窄,在對于雇員的誠信上設置了若干前置“慣例”,透露出了晉商對他人高度不信任的心理定勢。一方面,在雇員的選用上排斥外鄉人,只選用族人和本籍鄉親②。無論本地還是駐外商業字號和錢莊的雇員選用尤其如此,只有在工場作坊和商幫馬隊苦力工的選用上可以例外。雇員只選用族人和本籍鄉親充任這一“慣例”,既有防止雇員“跑路”而造成商家自身財產損失的考量,更是中國式家族社會關系思維和封建家長式管理模式的“創新”,其實質是一種為管理上實施人身控制的“巧妙設計”。另一方面,晉商對即使是族親鄉親的雇員也采取了若干防范措施。要求掌柜和店員“以店為家”,不得在商號住所外居住,且就連掌柜也只能一年甚至三年回一次家,對普通店員和學徒的限制更加嚴格。這固然可以防范商號資產被“內盜”,但也透露出晉商對雇員的極度不信任。要求掌柜及店員的“誠(信)”,商家卻缺乏對他們的必要信任,自然無“誠(信)”可言。加上嚴禁嫖娼和養小妾——有防止竊取商號錢財的考量,這種“連環”的人身控制實際上是變相盤剝——以管理和誠信的名義最大限度地榨取雇員血汗,這已不僅僅是個對雇員是否誠信的問題。另外,封建商人對于學徒店員實行的是三年無薪“慣例”,未能如期出徒之學徒店員的無薪年限會更長,加上“東家”對“出徒”條件的苛刻要求往往導致“出徒”時限的變相遲滯,“學徒時限”成為封建商人變相盤剝店員的工具。
晉商對家族成員特別是至親關愛有加,其至誠至信是另一番景象。“進入明清,科舉之艱難為士人所深為體味,所謂‘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賈而成功者十之九。”[15]儒生不得以“被迫”棄儒從商,但骨子里難以放棄由“儒生”到“儒士”再到高官而飛黃騰達的夢想。另外,儒生不得以“被迫”棄儒從商“雖則于己有顯赫于世或裕身肥家的好處,但骨子里卻更有光宗耀祖、顯親揚名的倫理動機。”在“孝道”這一根本性倫理的“合理性辯護”下,所謂儒商“可在奉養、孝養父母,盡家庭義務上得到倫理贊許”。“像此類‘棄儒從賈出于對父母、家庭和家族的一種強烈的責任感而為之的事跡,我們多見于明清商人資料中。可見這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9]對于同姓宗親,不少成功的“三晉”商人出資辦學、襄助貧寒子弟讀書舉士,進而鑲資擢升。盡管有些晉商出資助學存在為商政勾連儲備舉子、為經商儲備人才的考量,動機未必純凈,但助學之舉是必須給予肯定贊許的。另外,在士族鄉紳實際掌控鄉村社會的大背景下,助學濟困使得一些商人成為本宗本族的實際控制者,成為與士紳相抗衡的社會資本。有能力干預鄉村治理,卻又不承擔士紳義務,這就是商人的精明之處。他們樂于為同宗同族“出點血”、“破點費”,對于同鄉不同姓或同姓不同宗的鄉親就難以顧憐了。晉商(以至于整個中國近代商人)盡管自視為“士紳”,但除了家族、宗族利益,地方鄉村公用設施等公益事業辦得很少。③
東漢魏晉以來,在持續社會動蕩的背景下,儒者風范、“士”之傳統衍化出“士族門閥”(“士族豪強”/“士族鄉紳”)一脈。在國家政權軟弱時,他們作為地方豪強是地方社會政治的實際控制者/治理者——甚至上升為國家政治治理的重要參與者;在國家政權強大時,他們作為鄉村紳士(“士紳”)是鄉村社會的實際治理者。士族門閥,豢養門徒、養兵掠奴、征田霸產,士人的士族情懷演變成了世族豪強傳統。中國農業社會的宗主戶——依附戶格局就此造就。這個傳統貽害無窮、貽害至今。可悲的是,晉商是為商而非為士,卻極力效法“士族門閥”。既然做不成“士族豪強”/“士族鄉紳”,也要有點“士族門閥”的氣勢。在大肆購置田產方面,他們效法魏晉以來大地主階級的做派,大量掠奪土地。掠奪土地不分宗親還是外姓①,大量購買田產致使大量小農戶破產淪落為“依附戶”。不少晉商爆發戶,又將購置的田產用來大量種植罌粟(俗稱“種大煙”),以謀求比普通農作物種植大得多的暴利。“豪強”威風、奢靡,晉商依然效仿之,因此晉商奢靡之風、攀比之風日盛。有些明清晉商往往以“儉”起家,而以“奢靡”敗家,還沒等到朝代更替它們就自行消亡了。
自詡為“儒商”的明清晉商,無疑是“商”與“士”的“騎墻者”。雖然晉商宣稱“商與士同心”,但商人就是商人,他們絕然不可能具有“(儒)士”之純粹的儒家精神。更何況,繼承傳統需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就像王陽明及其門徒那樣。由此不得不提的是,晉商他們作為明清之人似乎對宋明理學知之甚少,可見他們所“習”儒家精神是有選擇性的。只可惜,晉商巨賈“好”“儒”之貪戀權位、奢靡無度,卻“惡”“儒”之“修、齊、治、平”。由此,他們對于相關方的“誠信”因“人”而異,呈現為因“時”便宜、善惡不分、亦善亦惡多重“選擇性”面相就不足為怪了。
四、結語
固然,“明清商人所處社會環境的復雜,新舊矛盾的重重摻雜,決定處于此狀態中商人倫理性格的兩重性,一是必須與社會普遍的倫理秩序保持一致,從而為社會所認可”,“二是必須為正從傳統中解放并不斷走向獨立的商人的營利欲提供倫理辯護,維護商人的利益。”[9]但自己所標榜的商業精神、商業倫理,是自欺欺人,還是為了欺騙他人?也許,對于明清晉商等商幫巨賈而言,二者兼有之。
既為“儒商”就應當恪守儒家“家-國情懷”、“仁義禮智信”根本之“道”,就不應該依仗“商政勾連”伎倆不斷沖決禮制、法制之網羅,逾規逾矩、無法無天。由此可見,“儒”僅僅是那些追求暴利、追求巨富之晉商巨賈的假面具而已。既然宣稱“以義制利”,既然體認“誠信”,就應當矢志不渝,就不應該以“商政勾連”、“囤積居奇”、竭力投機來牟取巨額不當得利,就不應該以為己牟利為根本尺度肆意玩弄“誠信”倫理規則,甚至不惜發國難財。由此可見,“義”僅僅是那些追求暴利、追求巨富之晉商巨賈的“噱頭”而已,“誠信”僅僅是那些追求暴利、追求巨富之晉商巨賈的倫理工具而已。
馮筱才指出,“在政商結構支配下,無論是商人,還是政客,他們追求的就不是常利,而是通過政策操縱或權力尋租、虛置法律等程序追求暴利”,“歷史人物都會隨著其生命的逝去而煙消云散,但結構卻常常會保存下來,甚至不斷發展”[16]。
可以說,明清晉商“商政勾連”的腐敗文化貽害無窮,山西系統性、“塌方式”腐敗的發生與此不無關系。因此,我們關于晉商的研究、對于晉商精神的宣揚和傳承,不可偏于一隅,片面地解讀、片面地宣揚,甚至糟粕與精華相混一味地歌功頌德,這樣只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和助長“商政勾連”腐敗文化的傳播,既腐蝕商人和官員的靈魂,也侵蝕黨和國家的機體,其后果是不敢想象的。
參考文獻:
[1] 劉寶宏,盧昌崇.晉商為什么衰落?——產權保護視角的探析[J].財經問題研究,2008(6):28-35.
[2] 趙榮達,郭玉蘭.晉商興衰原因的辯證思考[J].中共山西省委黨校學報,2005(1):38-40.
[3] 完珉.法眼觀晉商之:政商關系[J].中國商界,2011(4):56-57.
[4] 張華強.晉商興衰與規則表里[J].企業研究,2008(1):58-60.
[5] 馮筱才.從“輕商”走向“重商”?——晚清重商主義再思考[J].社會科學研究,2003(2):123-130.
[6] 劉建生,等.晉商研究述評[J].山西大學學報,2004(6):30-37.
[7] 張正明.明清山西商人概論[J].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1):80-90.
[8] 劉可為.從山西票號的衰亡探析企業的經營與制度創新[J].管理世界,1997(4):113-118.
[9] 段江波,張厲冰.明清商人倫理形成之內在沖突及其特征[J].倫理學研究,2003(4):49-54.
[10] 張明富.“賈而好儒”并非徽商特色——以明清江浙、山西、廣東商人為中心的考察[J].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2(4):10-18.
[11] 張正明,趙書華.明清晉商的經營文化[N].光明日報,2005-11-8(7).
[12] 張明富.論明清商人文化的特點[J].西南師范大學學報,1999(6):98-103.
[13] 馮 兵.“仁緣何貪”:朱熹對“貪”的認識[N].光明日報,2015-04-15(14).
[14] 劉庭玉.“媚事威權”:晉商興衰的“怪圈”[J].現代企業教育,2004(3):34-36.
[15] 張海鵬,王廷元.明清徽商資料選編[C].合肥:黃山書社,1985:251.
[16] 馮筱才.發現民國歷史的一條潛在線索——從“政商”的角度來講虞洽卿的故事[N].北京日報,2014-06-23(20).
責任編校 王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