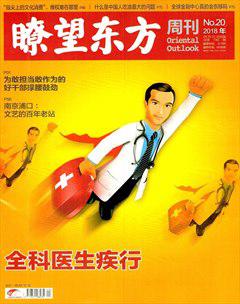易奉陽:戰旗村里的“巴適”生活
楊天
2018年2月12日,農歷臘月二十七,這是28歲的易奉陽永遠不會忘記的日子。這一天。習近平總書記來到他的家鄉成都市郫都區戰旗村,向全體村民以及全國人民拜年。易奉陽就在現場。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這是易奉陽兒時記憶中的戰旗村舊貌。那時,村民們分散在60多個散居院落中,以種莊稼為生。并不富裕。
后來。通過整理復墾村民原有的宅基地、院落等,戰旗村新增440.8畝土地。其中215畝用于安置村民及基礎設施建設,還有225.8畝土地“置換”了9000多萬元資金,利用這筆資金修建新型社區實現了村民集中居住。
兩年后,易奉陽隨全家搬進了新社區中一套173平方米的小洋樓里。當時的他不會想到,戰旗村未來的生活會更加美好,而他也將成為見證者和參與者。
易奉陽大學學習的是電力機車運用與駕駛。畢業后去了河北工作。如果不是戰旗村黨總支書記高德敏當年的一通電話,易奉陽現在可能還是一名火車司機。“孩子,回來吧!村里現在正是快速發展的時期。很需要你們這些有知識懂技術的年輕人啊!”電話那頭高書記的殷切期盼。讓本就不適應北方生活的易奉陽打定主意回到家鄉。
剛剛回來的易奉陽被派到基地學習無土栽培等新型種植技術。“當時我覺得這輩子也許就是和土地打交道了。”易奉陽說。
可是,未來遠不止如此。戰旗村人以都市觀光農業為切入點,開始打造集生產、經濟功能、生態和社會功能于一體的現代化都市生態農業旅游園區,并發展上下游產業。鄉村酒店、特色花田、太空果蔬觀光大棚、綠色蔬菜農莊……三產齊備的戰旗村“餅”越做越大。
易奉陽就這樣被戰旗村的快速發展助推著前進。學習酒店管理、市場營銷,他的知識儲備和人生閱歷不斷豐富。“我覺得每一天都過得充實而有意義。”易奉陽說。
易奉陽發現,最近幾年,越來越多像他一樣的年輕人選擇回到戰旗村發展。因為隨著村里引進和自辦的豆瓣廠、種植基地等企業越來越多,他們根本不用像在城里一樣為找工作發愁。如今,很多戰旗村的村民們既是土地股民,又是企業股東,還是產業工人。這樣的多重身份讓他們告別了祖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日子,腰包漸漸鼓了起來。
四川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啟動,戰旗村13.447畝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國有建設用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掛牌成交。這一宗地收益705.97萬元,讓戰旗村集體資產一舉突破2000萬元,村民人均現金分紅520元,此外,人均股份增值2600元。
到2017年,戰旗村的集體資產達到4600萬元。集體經濟收入462萬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26053余元,高出全區平均水平1993元。
易奉陽如今已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妻子在村里的杏鮑菇生產企業里上班,這是戰旗村引進的一家占地300畝的規模化、標準化企業,年畝產值達50余萬元。300多名員工中有200多人來自戰旗村,其他100多人則來自附近的村子。易奉陽3歲的孩子如今就讀于家門口的幼兒園,幼兒園由村委會引進專業機構辦學,不僅解決了戰旗村孩子們的入園難題,還輻射到了周邊的其他村莊。
平常閑暇時。易奉陽一家喜歡在社區里散散步。或是搬個凳子在自家門前喝茶曬太陽。由專業的清潔公司打理的社區,環境優美,干凈整潔。在戰旗村村口。便民服務站、衛生服務站等一應俱全,原本需要到幾公里之外的鎮上辦理的醫保、生育服務、生活繳費等手續,如今都可以在村里就近辦理。
“雖然還是住在農村,但生活環境比城里還好,不少城里人來耍,都打聽村里有沒有人要轉讓住房。”易奉陽說。
2016年戰旗村黨總支舉行換屆選舉,易奉陽當選了村黨總支委員。“我如今的工作和傳統的村干部工作已經大不相同了。”易奉陽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過去,村干部的工作主要是調解村民爭地爭利等矛盾。現在,我們的村民住上新型社區,已經從耕作中解放出來,我的工作內容就更加豐富了,需要參與村里的社區管理、基礎設施建設、招商引資等。”易奉陽說。
“鄉村十八坊”是村里正在全力自主開發的最新旅游項目。項目計劃以體驗式作坊經營為主,設立豆瓣坊、醬油坊、釀酒坊、陶藝坊等,利用本地的工匠資源,還原舊時的作坊生產方式,為游客更好地展示當地的傳統工藝。易奉陽告訴本刊記者,待項目打造完畢后,“不僅戰旗村對游客的吸納能力會更高,村民們也將依托這些產業,有更高的收入,過更好的生活。”
最近,易奉陽又多了項新工作——向越來越多來戰旗村學習參觀的人們介紹村莊的振興史。
2018年全國兩會期間,易奉陽自己拍攝的一段視頻短片在央視新聞頻道播出。視頻中,易奉陽自豪地邀請全國人民來成都,來戰旗村做客:“歡迎大家穿起我們的唐昌布鞋。到我們成都的天府綠道上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我們成都的幸福美麗新村。”
易奉陽(左)在村民家中走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