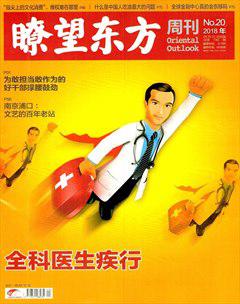“千年鳥道”之變
王念 潘強(qiáng) 朱麗莉
晚上7點(diǎn),天剛擦黑,在位于中國(guó)南方的廣西北海市冠嶺山,40歲的蘇遠(yuǎn)江戴上頭盔,拿起手電筒,開始每天的例行“巡邏”。
在接下來的兩個(gè)多小時(shí)里,蘇遠(yuǎn)江將與多位“鳥友”一道,在山中步行10來公里,為空中飛過的遷徙候鳥“保駕護(hù)航”。
“四五月正是遷徙季節(jié),成千上萬的候鳥晚上從這里經(jīng)過,飛回北方,其中不乏一些瀕危物種。”蘇遠(yuǎn)江說。
全球每年有數(shù)十億只候鳥進(jìn)行洲際遷徙,8條遷徙路線中有3條經(jīng)過中國(guó)。廣西位于東亞-澳大利亞全球候鳥遷徙路線上。中國(guó)北部灣因沿海豐富的灘涂、山林、島嶼等資源,每年吸引大量水鳥、猛禽等候鳥在此停歇。
在廣西防城港市紅沙村,夕陽下兩行白鷺正在飛回巢棲息。作為候鳥通道的交會(huì)點(diǎn),廣西防城港市目前正迎來大批鷺鳥在這里停歇
冠嶺山月朗星稀的夜空中,清晰可見成群結(jié)隊(duì)的候鳥。它們或排成人字陣,或排成一字斜陣,時(shí)而海上盤旋。時(shí)而靠樹停歇。
廣西紅樹林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孫仁杰說,遇上雨霧天氣,能見度低,候鳥容易迷失方向,朝著有光的地方飛去。過去曾有人打開自帶的光源并在附近布網(wǎng),捕捉那些朝燈光飛來的鳥群。
早在十年前,熱衷攝影的蘇遠(yuǎn)江就踏上了守護(hù)候鳥的征程。他從拍攝海灘常見的海鷗、白鷺,到登島觀賞珍稀水鳥,再到上山入林探尋猛禽,所拍攝的候鳥“近照”不斷見諸報(bào)刊或網(wǎng)絡(luò)。“那時(shí)很多人對(duì)鳥類認(rèn)識(shí)不夠,不僅沒想到保護(hù),甚至可能會(huì)為了一點(diǎn)利益對(duì)它們施加傷害。”
蘇遠(yuǎn)江點(diǎn)開多年前拍攝的一張照片,一只魚鷹張開雙翅翱翔藍(lán)天,雙腳卻被一只捕鼠夾牢牢夾住。“它只能不停地飛,直到精疲力盡而死亡。”蘇遠(yuǎn)江語氣沉重地說。
令人慶幸的是。近年來經(jīng)過當(dāng)?shù)赜嘘P(guān)部門大力打擊,規(guī)模性打鳥已經(jīng)得到有效遏制,越來越多的當(dāng)?shù)卮迕裰鸩秸J(rèn)識(shí)到保護(hù)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重要性,紛紛加入到保護(hù)候鳥的行列,曾經(jīng)的“打鳥人”如今成了“護(hù)鳥人”。
“看見捕鳥網(wǎng)就拆除,并給主管部門打電話報(bào)告。民間和官方形成合力,捕鳥現(xiàn)象已經(jīng)很少見了。”孫仁杰說,當(dāng)?shù)乇Wo(hù)鳥類的組織日益完善,除專業(yè)機(jī)構(gòu)外,近年來還成立了民間志愿者協(xié)會(huì)、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站等。林業(yè)部門在自然保護(hù)區(qū)安裝監(jiān)控設(shè)備,專門用于鳥類保護(hù)監(jiān)測(cè)。
官方大力禁止捕鳥,“進(jìn)校園”“進(jìn)社區(qū)”宣傳愛鳥意識(shí)。護(hù)鳥人士頻繁上山巡護(hù),讓途經(jīng)北部灣的候鳥有了良好的棲息環(huán)境。本刊記者走訪當(dāng)?shù)匕l(fā)現(xiàn),非法鳥類交易已經(jīng)難覓蹤影。
得益于各方人士的“愛心護(hù)航”,近些年候鳥遷徙季,北部灣群鳥翱翔,天空中常常呈現(xiàn)上千只鷹形成的“鷹河”遷徙的壯觀場(chǎng)景。孫仁杰介紹,秋冬季,近百萬只候鳥自西伯利亞、內(nèi)蒙古草原一帶遷徙而來,在“千年鳥道”冠頭嶺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鳳頭蜂鷹、蛇雕、褐冠鵑隼等猛禽就有20多種8000多只。
防城港山心沙島是候鳥遷徙的必經(jīng)之地。長(zhǎng)期研究候鳥遷徙的防城港林業(yè)局工作人員勞遠(yuǎn)華說,島上遷徙候鳥的種類達(dá)到30多種,數(shù)量不斷增多,最多時(shí)有兩三萬只,其中有瀕危鳥類大濱鷸和全球數(shù)量不足500只的極危物種勺嘴鷸。
由于長(zhǎng)期受到海水侵蝕,山心沙島面積逐漸縮小。近日當(dāng)?shù)赝瞥隽俗钚碌谋Wo(hù)方案,不僅考慮沙島的保護(hù),還廣泛聽取專家和志愿者的意見,充分考慮了對(duì)候鳥遷徙的保護(hù)。“護(hù)島也是為了護(hù)鳥。”防城港市海洋局港口區(qū)分局項(xiàng)目管理辦公室主任廖家巍說。
如今,像愛護(hù)生命一樣愛護(hù)生態(tài)環(huán)境,逐漸成為中國(guó)百姓的共識(shí)。“連小學(xué)生都知道鳥類是人類的朋友。”蘇遠(yuǎn)江說,在這條“千年鳥道”上,他愿意一直守護(hù)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