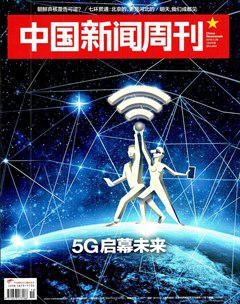互聯網時代,讀寫教育仍是重中之重
徐賁
讀寫不只是識文斷字,更是讓人明事理、辨真偽、知善惡、斷是非
在美國,沒有“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一說。閱讀和寫作,也就是讀寫(literacy)是學校教育的重中之重。這種重視經常是以讀寫危機意識表現出來的。
這種危機意識的前史是美國社會在20世紀40年代“二戰”期間形成的讀寫困境,又可以追溯到更早的20世紀初期讀寫教育問題。
20世紀初,大多數美國人都很樂觀,他們相信,在一個工業化的國家里,興辦公共教育就能把每—個孩子都培養成具有讀寫能力的成人。但是,也有人表示懷疑。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人就已經意識到,讀寫教育的效果遠沒有樂觀主義者設想得那么完美。美國軍方在招募新兵時發現,許多上過學的新兵都不具備必要的讀寫能力,這引起了教育界人士對成人缺乏讀寫能力的關注。
20世紀40年代,二戰期間發生了同樣的情況。美國和英國軍方發現,不具備“功效讀寫能力”的新兵比預料的要多。1942年,美軍不得不推遲征招433萬名新兵入伍,因為他們讀不懂書面的命令和指示,因此無法發揮軍事功能或執行起碼的任務。這再次引發了對成人讀寫問題的關注和討論。人們發現,一個士兵是否具備這種功效性的讀寫能力并不完全取決于他是否上過學校,缺乏讀寫能力的士兵可能是一種上過學的文盲。
功效性的讀寫概念是從在經濟活動中或工作崗位上的履職能力來看待讀寫的必要性的。—個人雖然能斷文識字,卻可能不具備運用文字的實際能力。他不能充分與他人交流、合作協商,不能理解別人的意思,也不能清楚和有條理地陳述自己的看法。一直到今天,改變這種實際的讀寫無能仍然是優化現有讀寫教育的主要訴求。
然而,二戰后出現了另—種讀寫觀,它所包含的不再是—個工作市場的老問題,而是—個國際社會的新問題。聯合國科教文組織1946年成立,立刻把掃除文盲確立為它的全球性任務。這個國際組織的創始人認為,公眾的無知和缺乏讀寫能力曾幫助法西斯和其他極權運動崛起,因此,必須把讀寫教育確立為一項推進世界進步和建立民主秩序的基礎工作。
這樣看待讀寫的重要性,讀寫就不只是個人的工作能力或技藝問題,而是成為人類社會認清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本質、增強相應的抵抗能力的共同行動。歷史的經驗是,幫助法西斯崛起和施虐的不只是一些目不識丁的文盲,而且是千千玩玩上過學、甚至受過高級教育的人士。他們不是不會閱讀或書寫,但他們的讀寫活動卻無助于他們思考善惡和辨別是非,也不能幫助他們在法西斯的欺騙宣傳面前保持抵抗的意識和能力。這種讀寫活動缺乏讀寫智力最本質的東西,那就是獨立思考和判斷的意愿和素質。
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把讀寫與反法西斯聯系在一起,賦予讀寫新的人文內涵。讀寫不只是識文斷字,更是讓人能夠明事理、辨真偽、知善惡、斷是非,自我成長和自我實現。1946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第一任主席萊昂.布魯姆呼吁從讀寫入手,“向愚昧發起進攻”。當然,文盲或不識字只是愚昧的—個可能原因,而不是愚昧的全部原因。
聯合國科教文組織關注讀寫問題的初衷反映了二戰后國際社會由于戰勝法西斯而特有的那種樂觀主義:相信讀寫可以推動人類未來世界的進步發展。這個組織的第一任總干事朱利安.赫胥黎表現出一種類似18世紀啟蒙運動者的樂觀熱情。他相信,讀寫可以為人類進步做出貢獻,照亮世界所有的“黑暗角落”。雖然他承認單憑讀寫還不能改變世界,但他認為,讀寫是“科學和技術進步”,也是人類“智力覺醒和心靈發展”所必不可少的。
互聯網時代的讀寫危機,印證了這樣的讀寫認識至今仍有重大意義。在互聯網時代更加重視讀寫教育,是推行人道主義文化事業、建立人類共同價值尺度的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