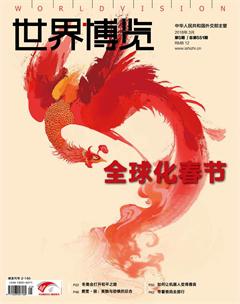外刊導讀
憑什么信任你,AI
在剛剛過去的狗年春晚上,自動駕駛汽車在港珠澳大橋上順暢行進,人工智能(簡稱AI)開始走近我們。消費者看到的更多是希望,是美好生活的愿景,而政府和監管部門會看到風險和挑戰。試想一下,當汽車行駛在跨海大橋上,你真的會將方向盤交給一個電腦程序嗎,換句話說,你放心將生命安全托付給它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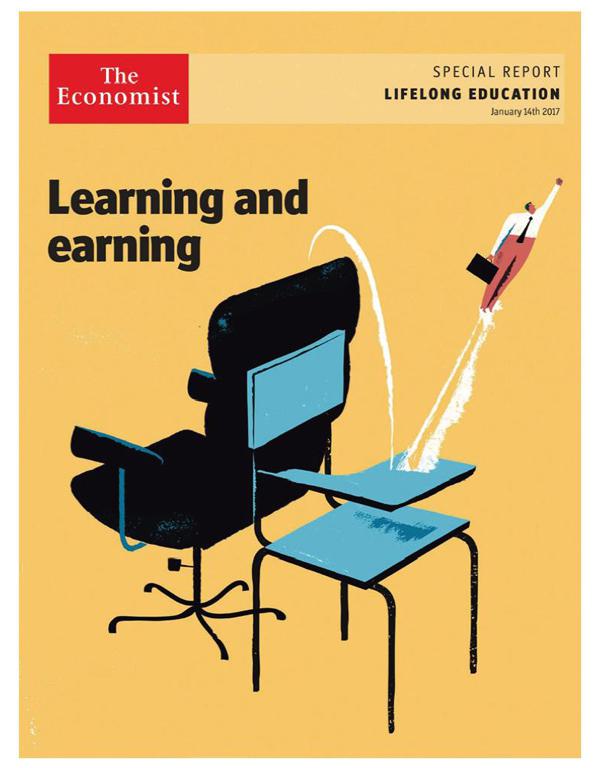
《經濟學人》的這篇文章認為,人工智能要取信于人繼而得到普及,就必須要可以解釋自己的決策和行為,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們就難以對它進行糾錯和改進,我們甚至可能會失去對它的控制,這無異于制造出一個惡魔。最新的AI系統利用了所謂“深度學習”的技術,它會自我學習,不斷進化。可是,當進化到高級階段,它決策和行為背后的邏輯會變得太過復雜,甚至讓設計它的技術專家都難以理解,它成為一個黑箱,充滿著不確定性。那么,如何讓AI系統像人一樣,有解釋自己的能力,就好比是讓阿法狗圍棋程序,每下一步都告訴我們它背后的用意呢?
本文介紹了軟件工程師們在試圖解讀人工智能方面所取得的進展。加州大學伯克利團隊的方法是,設計并訓練另一個AI主體與第一個AI主體進行溝通,進而幫助解釋第一個AI主體的行為;來自喬治亞理工學院的方法是,訓練另一個AI主體學習人類對玩電腦游戲給出的各種敘述,然后對第一個AI主體玩電腦游戲的方式進行描述。以上兩種方法本質上都是模仿人類的解釋方法,但在某些任務中,比如下圍棋,AI已經遠超人類,再模仿人類的解釋方法就有些勉為其難了。卡內基梅隆大學的計算機科學家用“壓力測試”的方法對AI系統進行評估,這種方法有助于找出系統的缺陷,剔除掉我們不希望出現的結果。還有些工程師開始嘗試從人類認知心理的角度對AI系統的行為進行類比解釋。然而,有些人認為,對AI的行為進行解釋的想法本身就是錯的,他們指出,越是復雜無法解釋的AI決策往往才是最有用的,可以稱之為“人工直覺”,比如,圍棋中所謂的“神之一手”,就是典型的例子。
最后,本文指出,人類傾向于為AI系統的行為建構出理性和意義,這樣的解讀出自人類,也用于人類。人工智能必將全面進入人類的生活,這會不會打開潘多拉魔盒呢,沒有人知道。說到底,人工智能是人類的一面鏡子,人類的命運終究取決于自己。
改良頭腦風暴

這是最新一期的《哈佛商業評論》的封面文章,它提出進行頭腦風暴的更好的做法,是以問題為導向。作者Hal Gregersen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領導力研究中心的執行主任,是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的領導力和創新的資深講師。Gregersen認為,在我們利用頭腦風暴尋找創新想法的時候,聚焦于問題而不是解答,可以創造一個安全的空間,讓參與者得以更深入地探究,尋求有突破性的洞見,從而更有力地解決難題。
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這種方法得到廣泛支持的背后是,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新穎的問題往往可催生出創新的甚至是具變革性的洞見。心理學方面的研究表明,以問題為焦點進行頭腦風暴實際上是從多個視角,用全新的方式再次解構我們所面臨的挑戰,這樣做有助于我們摒棄既有的偏見,大膽探索未知領域。
本文作者將以問題為導向的頭腦風暴過程稱為“問題迸發”,它可總結為一個包括三個步驟的標準做法:第一,設定場景,也就是說,選擇你深度關切的挑戰,并邀請幾個人來幫助你從全新的視角來考慮它,要求參與者只能發問,不允許為難題設定框架;第二,進行頭腦風暴生成問題,設置定時器,用4分鐘集體對所面臨的挑戰提出盡可能多的問題,若參與者的情緒積極,可重復進行,否則就休息一下明天繼續;第三,找出一條思路,并付諸實踐,這說明至少有一個問題有效地重構了這個難題,提供了解決它的新視角,最后,致力于追求至少一個新的路徑,積極探索真相,并設計行動計劃,做好后續工作。本文認為,假如你在自己的組織中把這樣的頭腦風暴變成常規做法,你就可以培育出一種更強的集體解決難題和尋求真理的組織文化。
近些年來,頭腦風暴似乎不那么流行了,作為產生新想法的工具,它顯得食之無味,棄之可惜。這主要是因為在傳統的頭腦風暴中,要么參與者給出的解答了無新意,要么參與者迫于壓力不愿給出可能惹麻煩的解答。因此,在進行頭腦風暴的時候,我們不去試圖給出解答,而是尋求提出問題,這很可能是更有效的方式。
共享辦公的先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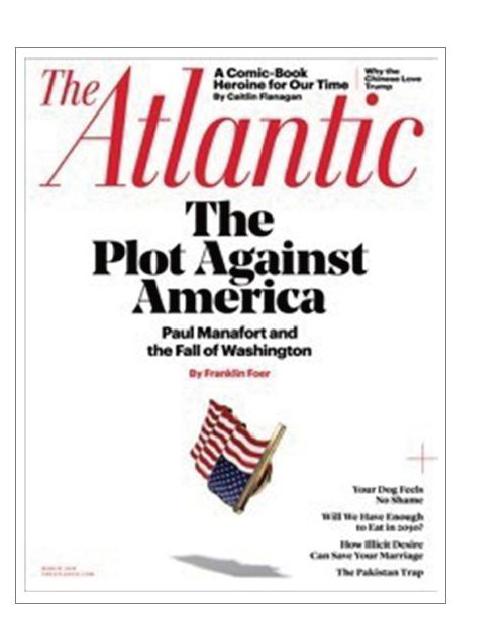
這篇《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介紹了WeWork全新的共享辦公模式。WeWork辦公園區散發著千禧一代的獨特氣息,廚房有手工釀造的啤酒和黃瓜水招待,公共混合區氣氛輕松,雖然辦公空間稍顯促狹,但是在這里,可以是一人一公司,人與人之間,公司與公司之間,都不再是涇渭分明。利用共享經濟的理念,WeWork想要把工作“人性化”,讓辦公室成為一個更有創造力的地方,有恰當的采光,恰當的零食,關鍵是,恰當的人。
WeWork代表著人類工作方式的未來,它的這種具有顛覆性和開創性的高大上定位贏得了千禧一代的認同。根據VentureSource所稱,WeWork是世界領先的提供聯合辦公空間的公司,去年它的估值達到200億美元,成為排名第六的最有價值的初創公司。這個估值令人咋舌,因為要說起來WeWork還只不過是一家出租短期寫字樓空間的公司而已,且主要針對中小企業和自由職業者。
本文指出,寫字樓轉租并不是什么數字時代的創新,不過,聯合辦公空間的概念,即一群觀念接近的租戶致力于形成一個社區,是直到最近才有的。2010年,Adam Neumann和Miguel McKelvey在紐約租下幾千平方英尺的SoHo場地,開始了第一處WeWork共享空間的運營。在WeWork社區內,人們很放松,這種持續的歡快氣氛,會鼓勵社區成員們參與社交,相互學習,分享工作經驗。很快,許多一流的大公司也成為WeWork的客戶,派出員工進駐到這里,包括Facebook、Salesforce、亞馬遜和匯豐銀行等。吸引大公司的不是這里的低成本,而更多是它的便利和時尚感。當然,WeWork提供的絕不只是輕松愜意的氛圍,它還有助于提高員工的生產率。
對WeWork的先進理念和高估值,有人持懷疑態度,認為它空有概念,無法變現。不過,本文在文末指出,WeWork的商業模式所依據的大都市中心區域產生的“創造性集聚”效應,是有著理論和數據支持的。更重要的是,這種模式恰好與新生代員工的工作態度相匹配,那就是,千禧一代希望在工作中尋求意義,同時感受到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