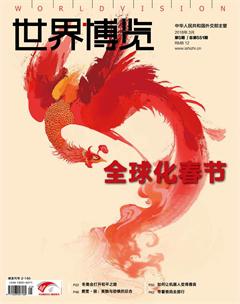當歷史人物聽錯了
張雷
導語:感謝沃爾特·迪斯尼讓《灰姑娘》變成了經典。但是佩羅版灰姑娘最顯著的特點,水晶鞋,可能是一個錯誤。

巴爾扎克推測,灰姑娘的故事可能是佩羅聽來的,講故事的人口頭說的是(松鼠毛鞋)pantoufles de vair,而佩羅誤以為是pantoufles de verre(玻璃鞋)。
1682年法蘭西文學院的秘書夏爾·佩羅(Charles Perrault)被解雇了,于是他決定將自己以后的生命都獻給文學。起初,他熱情投入了所謂“現代派與古典派的爭論”中,在《偉大路易的時代 》一文中他捍衛自己時代的優越性,也為他贏得了巨大的贊譽,但是他很快厭倦了這樣的宏大問題,開始轉向輕松些的東西,最終定下了重新整理童話故事的目標,當時的童話故事更多的是在成年人中流傳,孩子鮮少知悉。佩羅盡可能多地收集整理傳統故事,并以更“現代”的方式改寫它們。這些故事有些是他早年聽說過,記在腦海里的,有些則是從書中看到的,比如喬萬尼·薄伽丘的《十日談》,還有一些則是佩羅從朋友和鄰居處收集而來。晚年的佩羅以兒子的名義出版了《鵝媽媽的童話——那些來自舊日時光的故事》,正是這本書讓他后世留名。
《鵝媽媽的童話——那些來自舊日時光的故事》出版于1697年,書中有11個故事,8個是以散文的形式講述,3個是詩歌體例。這本書幾百年來全世界廣泛流傳,《小紅帽》、《小拇指》、《藍胡子》《穿靴子的貓》《睡美人》每一個都膾炙人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灰姑娘》。當然,這不是一個新的故事,但是佩羅的版本令人印象深刻,最為特別的就是,在書中灰姑娘第一次穿上了水晶鞋。
今天,幾乎每個人都知道佩羅改寫過的《灰姑娘》的故事,即使他們從未聽說過佩羅這個人。感謝沃爾特·迪斯尼讓《灰姑娘》變成了經典。但是佩羅版灰姑娘最顯著的特點,水晶鞋,可能是一個錯誤。
聲音是很脆弱的
在佩羅的童話出版一個半世紀后,巴爾扎克在為凱瑟琳·德·美第奇所做的傳記中思考了灰姑娘的鞋履問題。巴爾扎克無法理解為什么這個可憐的女孩穿這么奇怪的東西,他推測,灰姑娘的故事可能是佩羅聽來的,講故事的人口頭說的是(松鼠毛鞋) pantoufles de vair,而佩羅誤以為是pantoufles de verre(玻璃鞋)。
巴爾扎克提出了一個優雅的理論; 但現代學者對此常常提出質疑。 盡管灰姑娘的早期版本中可能穿的是松鼠毛鞋,但研究法國民間傳說的專家指出,到了佩羅所生活的17世紀后期,vair這個詞已經相當于是古語了,在童話故事中不太可能用,至少在巴黎不會有人用。 另外,在幻想的童話世界里,有人穿玻璃拖鞋并不奇怪。 畢竟,童話世界中有很多玻璃山,甚至玻璃橋的例子, 那為什么不能有玻璃鞋呢?
但巴爾扎克的理論卻凸顯了一個重要的觀點。雖然歷史學家早已認識到研究事物過去是如何被稱呼的很重要,但是研究事情是如何被誤解的,可能更能揭示真相。
聲音是很脆弱的。當我們說話的時候,一定的距離內的人才能聽到,有些字母比另一些更容易區分。在巴爾扎克完成凱瑟琳·德·美第奇的傳記大約30年后,德國語言學家奧斯卡·伍爾夫(Oscar Wolf)證明了,字母a在260步之外也能清楚地區分出來,但字母h在12步之外就聽不清楚了 。因此,一些以f和th開頭的詞很容易聽錯,聽成發音類似但含義卻完全不同的東西。比如說把Fan(扇子)聽成than(然后); pen(筆)聽成pan(平底鍋)。當我們誤聽的時候,我們不僅僅是把一個字誤認為是另一個字。而是有意或無意地,我們的大腦也在思索著所有的可能性,通過上下文來決定最可能的那個詞和意。我們聽錯的背后隱藏著我們對于別人所說話的期望。這些期望不僅受到語言規范的限制,而且受到我們更廣泛的社會,文化甚至政治態度的制約,歷史學家可以用歷史上聽錯的事例來洞察背后隱藏的態度和信仰。
誤聽可以成為觀察過去的巨大透鏡
以克里斯托弗·哥倫布為例。1492年11月23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在遠處發現了一個島(或可能是海角),船上的當地土著人稱這個島為波希奧(Bohio),他們說這里居住著食人族(Caniba)。后來安的列斯群島就和食人族建立了長期關系。但是哥倫布把Caniba錯聽成了Carib(加勒比)。所以,一開始哥倫布并不知道這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很快就想起了馬可波羅曾經寫過安達曼群島上的人喜歡吃人,這些人的頭,眼睛,牙齒長得像狗一樣。由于Carib很容易讓人想到拉丁文中的canis(狗),所以他認為波希奧人長得就像安達曼島民一樣,而且他們也有相同的美食口味。這是一個荒謬的聯想。但是,卻說明了哥倫布與新世界的接觸程度,甚至他所遵循的路線 - 都是以他讀過中世紀旅行者的奇幻故事為基礎的。
再來看看法國元帥雅克·圣·阿諾德。1851年12月2日拿破侖的侄子路易發動政變,圣·阿爾諾以國防部長的身份負責指揮軍事行動。盡管患有嚴重的感冒,他還是迅速占領了巴黎周邊幾個戰略要地。但是他的病情越來越嚴重了。就在一群人聚集到路障前時,他開始大聲咳嗽起來。當再次能順暢呼吸之后,他喊道“ma sacrée toux”(我這該死的咳嗽)。然而,他的士兵誤聽成了“massacrez tout”(屠殺每個人),然后就照做。假設這傳說不是杜撰的,這個血腥的故事表明,圣·阿爾諾的士兵不僅希望他們的指揮官命令他們殺死手無寸鐵的平民,而且還認為這是一件完全合法的事情。這件事不僅證明了第二帝國初期士兵與公民之間的緊張關系,而且也證明了軍隊缺乏戰爭倫理。
最有趣也最不為人所知的是保羅·艾利將軍的例子,在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1954-62)的大部分時間,他都擔任法國國防參謀長。在法阿沖突的高峰期,1958年5月,整個法國被所謂的阿爾及爾危機所震撼。由于擔心新任總理皮埃爾·普夫利姆林不會那么有力地捍衛殖民地,一些法國高級將領發動政變,要求戴高樂將軍出任總統。幾天之內,反政府武裝攻占了科西嘉島,計劃在此進攻法國。作為國防參謀長,艾利必須做好最壞的準備,他需要所有人的幫助。但他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把他最忠誠的指揮官之一,空軍將軍安德烈·馬丁作為叛徒逮捕了。因為在他們兩人最后一次碰面時,馬丁將軍提到他最近去了一趟Bonn(波恩),但艾利卻誤以為是位于阿爾及利亞的一個省B?ne(伯恩),并得出結論認為,馬丁一定是倒向了叛亂分子。艾利將軍相信像馬丁這樣值得信賴的人會加入政變,證明了法國軍隊最高層有多恐慌。艾利的錯誤,為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脆弱性以及軍隊內部缺乏凝聚力提供了有力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