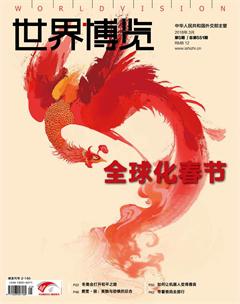莎士比亞的餐桌
顏漁家
莎士比亞不久為我們描繪了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英國(guó)的食物藍(lán)圖,也表現(xiàn)了當(dāng)時(shí)英國(guó)人的人生態(tài)度。

莎翁筆下的人物選擇了哪一種酒,同時(shí)也就告訴了讀者和觀眾他是哪樣的人。
哈姆雷特在母親的婚禮上抱怨: “葬禮上的烤肉尚有余溫就被端上了婚禮的宴席”的時(shí)候,他是責(zé)備母親,在父親尸骨未寒就又結(jié)婚了,這里的葬禮烤肉并不僅僅是葬禮中剩下來(lái)的殘羹冷炙,其實(shí)葬禮烤肉(coffin meat)實(shí)際上是一種曾經(jīng)很流行的食物,英語(yǔ)的棺材一詞coffin,不僅僅是指安葬尸體的容器還指保存肉類的容器。那些可食用的“棺材”是由糕點(diǎn)皮制成的,起到密封的作用,讓其內(nèi)的食物能保存得更久。這種糕點(diǎn)更像是保鮮盒,所以比較粗糙,常常是扔掉而不是被吃掉。
麥克白夫人提供的飲料非常講究:為了為謀殺國(guó)王掃清道路,她用有毒的蛋奶酒奪走了國(guó)王的馬車夫的性命。這種蛋奶酒是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餐桌上半食半飲的必需品。用葡萄酒,麥酒或西班牙雪利酒加奶油制作而成。所以說(shuō),要真正理解莎士比亞的飲食文化,我們需要揣摩西方食品史,甚至得研究一兩本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的食譜。
昂貴的雪莉酒是貴族的最愛(ài)
對(duì)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餐桌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更多地了解莎士比亞的戲劇,比如說(shuō),莎翁筆下的人物選擇了哪一種酒,同時(shí)也就告訴了讀者和觀眾他是怎樣的人。在伊麗莎白時(shí)代,昂貴的雪莉酒是非常流行的,莎翁這位吟游詩(shī)人筆下最著名的酒鬼福斯塔夫最愛(ài)雪莉酒,他曾發(fā)誓永世不沾酒。然而后來(lái)的場(chǎng)景中,他高呼如果他有一千個(gè)兒子,他所要教授的首要原則就是,戒絕那些單薄無(wú)味的酒,并終生效力于雪利酒。
而麥芽酒則低一階層,相對(duì)來(lái)說(shuō)味道淡,酒精含量低。在莎士比亞時(shí)代,麥芽酒和啤酒十分流行,尤其在城鎮(zhèn)。麥芽酒是一種傳統(tǒng)的啤酒,在那時(shí)麥芽酒在釀造中不加酒花,口味比較清淡。當(dāng)時(shí)的人們十分喜愛(ài)這種酒,早晚隨時(shí)都會(huì)喝,在《馴悍記》中,貴族們開(kāi)玩笑,把爛醉如泥的補(bǔ)鍋匠斯賴,從冰冷的街道地上抬到房子的床上。并且騙斯賴說(shuō)他是貴族,在其醒來(lái)的時(shí)候,準(zhǔn)備了白葡萄酒,黑葡萄酒蜜餞果子,出身低微的斯賴卻大喊一聲,看在上帝的面上,來(lái)一壺淡麥酒!
在莎士比亞的巔峰時(shí)期――16世紀(jì)后期,啤酒是溫暖、深色、混濁的。那時(shí)酒通常以濃烈程度進(jìn)行分類:烈啤酒、餐桌啤酒、船啤酒以及小啤酒。小啤酒酒性軟弱,把釀酒的剩余物用開(kāi)水洗凈、稀釋,經(jīng)第二次發(fā)酵釀制而成。許多人每頓飯都要飲用它。《亨利六世》中描寫(xiě)了成衣匠杰克·凱德帶著“穿著皮圍裙的人”(工匠)造反。承諾“要讓喝小啤酒成為重罪”。
在《亨利四世》中哈爾親王在喬裝打扮混跡街頭的時(shí)候,在“野豬頭酒館”時(shí)喝過(guò)。在劇中的關(guān)鍵時(shí)刻,哈爾親王坦陳他想喝一口小啤酒(Beer),卻遭到了朋友波因斯的阻撓:“一個(gè)王子不應(yīng)該這樣自習(xí)下流,想起這種淡而無(wú)味的賤物。”
某種特定的肉類與某人的“心情”、職業(yè)、乃至于國(guó)籍相關(guān)聯(lián)。例如,培根就被視為只適合讓工人和體力勞動(dòng)者吃,因?yàn)榕喔茈y被消化,而重體力勞動(dòng)可以促進(jìn)消化。而雞肉則更受人們喜愛(ài),有些人還把它當(dāng)作最適合給患者吃的食物。在莎士比亞時(shí)期,閹雞是一種更奢侈的肉——閹雞是約翰·法斯塔夫爵士最愛(ài)吃的肉,《維洛那二紳士》中朗斯(Launce)的狗從餐桌上偷過(guò)一條閹雞腿。牛肉使人愚昧,莎士比亞曾兩度提及這一點(diǎn)——《第十二夜》中,安德魯·艾古契克)說(shuō):“有時(shí)我覺(jué)得我跟一般基督徒和普通人一樣笨;我是個(gè)吃牛肉的老饕,我相信那對(duì)于我的聰慧很有妨害。”
餐桌產(chǎn)生戲劇沖突
很難找到一部在餐桌上沒(méi)有產(chǎn)生沖突的莎士比亞的戲劇。 用餐,是劇作家最好的借口,讓很多人同時(shí)聚集在同一個(gè)舞臺(tái)上,讓朋友和陌生人見(jiàn)面,在一個(gè)狹小的空間,所有的角色別無(wú)選擇,只能說(shuō)話和互動(dòng),從而創(chuàng)造戲劇性的緊張氣氛。
在《馴悍記》,中彼特魯喬想馴服任性的凱瑟麗娜,所以他在婚禮和招待會(huì)之間把她偷走,只最后讓她在沒(méi)有飯吃的饑餓中屈服。 在《皆大歡喜》中奧蘭多在森林盛宴發(fā)力,為最后的婚姻埋下伏筆。在《雅典的泰門》中,泰門像個(gè)幼稚的孩童用“設(shè)宴”請(qǐng)客的辦法,特設(shè)了一桌非同尋常的白開(kāi)水“宴席”,待舊日的朋友來(lái)“赴宴”時(shí),他把大碗的溫水潑在這群狼心狗肺者的嘴臉上,咒罵他們泯滅了人性的良知,然后,用碗碟將他們打跑,以此來(lái)羞辱、懲罰那些不義之徒。
在莎士比亞的時(shí)代,一個(gè)人吃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所處的階級(jí)決定。地主士紳,甚至是富有的商人都可以通過(guò)節(jié)日的宴會(huì),炫耀自己的財(cái)富,當(dāng)時(shí)盛宴的主角是蜜餞和由堅(jiān)果包裹的糖果。在《溫莎的風(fēng)流娘們》中福斯塔夫呼喚天上掉下“用來(lái)清新口氣的小甜點(diǎn)kissing comfits”。在莎士比亞的時(shí)代,宴會(huì)的主角不是各色飲食,而是甜點(diǎn)。或者說(shuō)是精心制作的糖果和甜品雕塑。那些條件允許的富豪,會(huì)在豪宅之外,建造單獨(dú)的宴會(huì)廳來(lái)招待客人。
在《馴悍記》中,彼特魯喬堅(jiān)持要縮短潑婦凱瑟麗娜(Katherine)的名字,叫她凱特Kate,而她堅(jiān)決反對(duì)。在兩人的斗智斗勇中,彼特魯喬用“佳肴cates”的雙關(guān)語(yǔ)把凱特變成了一個(gè)即將被人吞噬的美味佳肴。 “Cates”可以指任何食物,但通常指最精美的菜肴。
在《亨利四世》的第二部分中鄉(xiāng)村法官吩咐大衛(wèi):告訴廚子威廉,叫他預(yù)備幾只鴿子、一對(duì)矮腳母雞、一大塊羊肉,再做幾樣無(wú)論什么可口一點(diǎn)兒的菜(kickshaws)。 kickshaws一詞是莎士比亞從法語(yǔ)的quelquechose借來(lái)的,意思是“something”,這個(gè)詞涵蓋了一大堆美味的開(kāi)胃菜。
在哲瓦斯·馬克漢姆(Gervase Markham)1615年(莎士比亞在1616年去世)出版的書(shū)《英國(guó)女管家》(The English Huswife)中說(shuō),家庭自制kickshaws需要將雞蛋,奶油,黑醋栗,肉桂,丁香,菠菜,菊苣,萬(wàn)壽菊花和豬腳(雞腳)混合。但他也建議使用小鳥(niǎo),塊根,牡蠣,內(nèi)臟和檸檬。今天的烹飪書(shū),對(duì)于原料和做法有細(xì)致的測(cè)量和過(guò)度的解釋。但是和當(dāng)時(shí)所有的烹飪書(shū)籍一樣,馬克漢姆的指引更像是購(gòu)物清單。
莎士比亞不久為我們描繪了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英國(guó)的食物藍(lán)圖,也表現(xiàn)了當(dāng)時(shí)英國(guó)人的人生態(tài)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