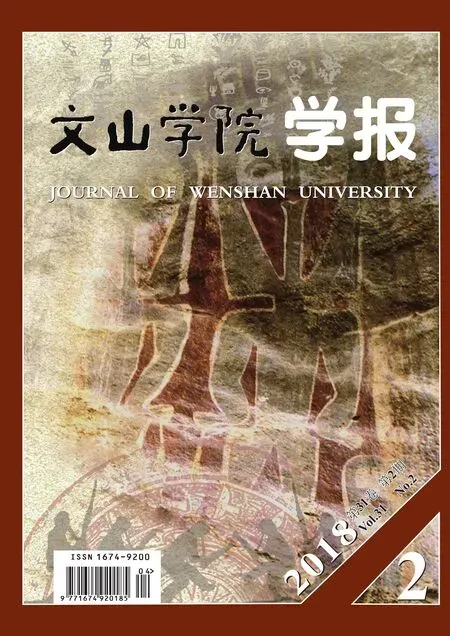西南官話武昆片語音特征的形成原因探究
牟成剛
(文山學院 人文學院,云南 文山663099)
西南官話武昆片的語音特點是中古入聲調今歸陽平,它是中古入聲調在西南官話今讀中的主體類型,其地域分布較廣,“西南官話75%的方言點都屬于此類型”[1]。但因受文獻資料不足等多種條件限制,學界至今對入聲調在武昆片中緣何能如此整齊地歸入陽平,卻討論甚少,或語焉不詳。筆者將根據現有的調查資料,參照周邊相關方言事實,結合一定的移民史實情況,運用語言接觸影響等相關理論,對武昆片入聲調歸讀陽平的緣由試做探究。
一、武昆片的語音特征及調型特點
根據研究,“武昆片”是指西南官話以武漢話和昆明話為代表的一個次方言片區[1],中古入聲調在該方言片區中已經消失,其突出的語音特點就是中古入聲今讀歸陽平,現以昆明話為例,如:“突定=徒定t h u31、福非=拂敷=服奉=符奉都f u31、六=爐l u31”等。入聲歸讀陽平是中古入聲在西南官話今讀中的主體類型(或稱典型類型),總體來看,西南官話中“凡是不屬于雅棉片、仁富片和江岷片的方言點,基本上均可歸入此類型”[1]。武昆片在西南官話中的所涉及的地理分布范圍非常廣泛,幾乎遍布西南官話各區域,主要集中分布于滇黔川渝鄂五省市,此外,陜南、湘西、湘南、桂北等也有分布,如昆明、武漢、成都、重慶、桂林、郴州等等是其代表方言點。根據統計,在西南官話共500余個方言點中,將近五分之四屬于武昆片[2]278。地理分布特點上,主要涉及的省市均以省府為中心,呈現出地域集團式連片分布的格局。武昆片不同的地域分布集團,其陽平的調值調型也會體現出相應不同的地域特點。
陽平調在西南官話中主要有四種調型:降調型、升調型、曲折型、平調型。降調型是西南官話陽平的典型調型,主要分布于云南、貴州、四川、陜南、廣西、鄂西北、鄂北、湘南等區域,調值上以中降調31調值為主(部分方言點的調查材料處理為21調值),但鄂西、鄂北主要體現為52調值的高降調;升調型主要分布于鄂中、湘西、湘北等區域,調值上主要體現為13(或12)調值的低升調型(只有荊門等少數方言點呈現出34調值的中升調型);平調型主要集中在鄂西南(如興山、巴東、秭歸、鳳凰、利川、宣恩、恩施等),此外,湘西北的保靖、吉首,廣西的富川等也屬于此類型,調值上較為一致,即為11調值的低平調型;曲折調型的方言點主要集中在鄂中南部一帶(如武漢、天門、當陽、江陵、武昌、漢口、漢陽等),此外,湖南靖縣、漢壽,四川萬縣,陜南鎮巴等也屬于此類型,調值體現為213(或313)的中降升調型。由此可見,陽平調在西南官話中,調型上具有地域差異性的特點。如表1:

表1 西南官話的陽平調型及其分布情況簡表
二、武昆片語音特征的形成原因
學界一般認為,入聲韻尾消失后,調值和調型的相似性是入聲歸派舒聲調的主要原因。但通過上面對陽平調在西南官話中的調值調型分析結果來看,陽平調在西南官話中的調型和調值均存在地域差異性,而且這種差異性還具有一定的區域連片特點。這說明,入聲在西南官話武昆片中歸讀陽平,除了具有調型相同(調值相近)的共同語音基礎之外,應該還存在其他相關因素(語言或非語言)的影響。下面參照周邊現存的與之相關方言點的調值調類情況,輔以韻書文獻考證和移民史實佐證,對西南官話入聲歸讀陽平的相關原因試做探究。
(一)語音特征的形成基礎擬探
漢語聲調在其合并演變中,如果忽視外因的影響,一般來說“調型越相似就越有可能發生合并”[3]。入聲和陽平在武昆片中合為一類,說明二者早期混同之前的調型和調值應該是相近的。因條件所限,歷史韻書對入聲和陽平在早期西南官話中的調型和具體調值,并未做明確的描述,下面將結合現有的語音記錄材料和移民史實,對之進行初步的構擬和探索。
根據研究,西南官話的形成與江淮湖廣一帶的移民關系密切,“明代的將領沐英平定大西南之后,江淮湖廣一帶漢人大量移居云、貴、川,于是形成了西南官話”[4]。這說明,江淮湖廣一帶是西南官話移民的主要來源地,那么西南官話與江淮官話和湖廣一帶的早期方言自然會有較大關系。通過語音對比分析,輔以移民史實材料考證,筆者認為西南官話是江淮官話“移民”西南地區以后繼續演變的結果,二者屬于同源關系,只因地域特點和語言接觸等因素的不同,導致西南官話的語音演變總體上要快于江淮官話罷了。[2]300南京話是江淮官話的主要代表,根據德國學者何美齡(Hemeling)的記載,南京話在19世紀末期的陽平為313調值[5],是一個中低降升的曲折調型,同屬江蘇的建湖、鹽城和鄂東的黃陂、黃岡等江淮官話方言點均屬此類型。據此,我們可以判斷早期的西南官話陽平也很有可能是一個中低降升的曲折調型。例如,鄂東的武漢話屬西南官話,但因其更靠近江淮官話,故其陽平至今仍保留著較早時期213調值的低降升的曲折調型[6],鄂中南的松滋,湘北的澧縣、漢壽、桑植,湘南的宜章,湘西的懷化、芷江、靖縣、晃縣、麻陽等方言點陽平的調值調型,與武漢相同。以上這些現象說明,把早期西南官話陽平擬為一個中低降升的曲折調,具有一定合理性。
既然擬定西南官話早期陽平是一個中低降升的曲折調型,那么意味著早期西南官話的入聲調型也應該與之相近,因為只有這樣,入聲和陽平混同才可能具有共同的語音基礎。據《漢音集字》(J.A.Ingle1899)記載①,一百年前的武漢話是有入聲的,但在引言中特別強調當時的入聲和下平(按:指陽平)有某些相混,這說明當時的漢口話的入聲作為一個調類已經開始與陽平混同,可惜的是該書缺乏對其入聲和陽平調值的記錄或描述;據《湖北方言調查報告》(1948)顯示,武漢地區至遲在20世紀30年代入聲就已完全歸讀陽平,而當時武昌、漢口、漢陽等方言點的陽平,均體現為中低降升的曲折調型(調值為313或213)。[7]49-144武漢話的陽平調值和調型,自20世紀30年代至今均較為穩定,即為213調值(寬式為313),這樣看來,武漢話早期的入聲與陽平應該具有相同的調型(調值相近)。關于這一推論的合理性,也可從周邊現存方言事實得以證實。武漢的東、北、南三面均存在江淮官話方言點,如孝感、羅田、英山、浠水、黃安等地的入聲就是213(或313)的曲折調型。另,云南的陸良、曲靖、沾益、劍川、鎮康等方言點的入聲調至今嚴式記音仍為312調值的曲折調型,四川的丹棱、青神也與之類似。特別是云南至今仍有保留曲折調型的獨立入聲調,是一個很好的側面例證。首先,“云南的漢語方言形成比較早,演變歷史比較長”[8],在西南三省中,云南的經濟文化歷來比較獨立,同時偏于一隅的地理環境,使得云南官話受外方言的影響較小。其次,云南在元初被重新統治之前,這里沒有漢語的地位,云南官話方言主要是隨移民于明代遷入而形成的②,這保證了漢語斷代層面的純潔性和原始性。最后,云南的漢族主要遷自江南的蘇、皖二省,今天蘇、皖二省以江淮官話為主,而鄂東的江淮官話入聲大多均為曲折調型。這些語音現象說明,入聲在早期西南官話中應與當時的陽平一樣,屬于一個曲折調型。
一般認為,調型相同或近似(調值相近),是聲調混同的內在語音基礎。在考證歷史韻書,輔以移民史實,參照方音實際的基礎上,我們傾向于認為,入聲和陽平在早期的西南官話中,他們的調型應該相同或近似(調值相近),均屬一個中低降升的曲折調型。
(二)語音特征的區域差異解釋
上面已經討論并構擬了入聲和陽平在早期西南官話中的調型,認為他們在當時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調型(大致均為曲折調),這是二者后來在存在混同趨勢的內在語音基礎。但陽平在武昆片中,除了如武漢等今讀為低降升的曲折調型外,還有降調型、升調型,甚至平調型,且這些不同的調型在分布上具有一定的連片格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語音內在“省力趨簡”演變的結果,另一方面也與當地其他漢語方音(或少數民族語音)的接觸影響有關。
調型中,“曲折調相對來說是一個較為不穩定的調型”[2]267,其在西南區演變為降調應該是其自身調值演變的結果。因為西南區的云貴川地理壞境相對封閉,而由一個曲折調演變為相應的降調,這符合發音省力的原則。但陽平在鄂中、湘西、湘北演變為升調則很可能是受湘語等相關方言的影響,因為湘方言中“陽平調主要為低升調13或12”[9]181,但這種情況在湘西南靠近西南官話區的部分方言點中,依然還殘留著低降升曲折調型的影子,湘西南漢語“陽平絕大多數方言點中為低升調13,或低降升調213”[10]。此外,贛方言也與湖廣官話毗鄰,其陽平也是以低平調或升調為主,鄂西南如宣恩陽平讀低平調型或許與其影響有關。下面結合語音自變和語言接觸的理論,探索中古入聲調在西南官話武昆片中歸讀陽平的原因。
湖廣地區早期為湘語區,這是肯定無疑的,而湘方言“若有入聲,則入聲調值一般為中升調24”[9]182,湖廣的西南官話的入聲為升調型,很可能與早期湘方言的影響有關,如武漢周圍的孝感、黃安一帶的入聲寬式記為13調值,嚴式仍為213。這里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現象,鄂東江淮官話都是有入聲的,但可能因入聲受湘語的影響而變成升調型,而其陽平則多為降調型(與西南三省的官話陽平調型相似),故其入聲從調型上很難混入陽平。但安陸、應城、孝感、云夢、禮山、黃陂有一部分全濁入聲歸陽平,我們認為這是早期的層次類型,當時應該是調型相同而混(很可能二者均為曲折調型),后來入聲受湘語等的影響而變升調型,陽平受后來由沿北方一線傳入的西南官話強勢影響而變成降調型③,故其入聲方才得以保留(但因其去分陰陽、入聲保留,故其不屬西南官話,為江淮官話[1])。西南三省區等的入聲調型則與湖廣區的升調型不同,它們屬于降調型。我們在前面探討陽平由曲折調變為降調時就說過,曲折調相對來說是一個較為不穩定的調型,而西南三省區多為少數民族聚居區,據統計此區域的少數民族語言聲調很少有曲折調,從音理上看,處于一個地理壞境較為封閉的西南腹地,在沒有其它強勢方言的干擾下,一個曲折調變讀為降調,符合發音省力的原則。此外,西南腹地的少數民族語言,在聲調上大多有松緊元音的對立,故當地早期的曲折型入聲變為今天的降調型,可能還與少數民族語音聲調的影響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系。如云南新平等地的彝語支“聲調有3個:55調、33調、21調。緊元音只出現21調和33調”[11]35;白語“聲調有8個:即33調、42調、31調、55調、35調、44調、32調、21調。元音松緊與聲調有一定的制約關系,緊元音只出現在44調、42調和21調”[11]50。據此可以看出,彝語和白語等少數民族語言的緊元音調值基本都為平調或降調,很少有升調的情況出現,這就與從外遷入的早期漢語的曲折型入聲有了共鳴點,即它們都有讀得短促的特點(甚至有學者說這少數民族語言的緊元音調就是這種語言的入聲④),在相互影響的過程中肯定是相較為簡單的類型占優勢,而作為曲折調型,演變為平調型顯然不如演變為降調型更為省力方便。值得注意的是,“彝族分布在云南、四川,貴州三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12]3,它是我國西南地區的勤勞勇敢、歷史悠久的少數民族,人口共有五百四十多萬人,而西南三省和廣西的西南官話入聲恰好主要就是降調型,這很難用巧合解釋。因此可以說,西南區環境的封閉性和語言接觸等因素,促成了今天西南官話入聲絕大多數演變為降調型,從而容易與已演變為降調型的陽平調相混同。現西南官話入聲存留型方言中,入聲調為降調的方言點基本都處于西南腹地的滇黔及與之毗鄰一帶(包括湖南東安和江西信豐等),就更能說明這一情況了。參看表2所示:

表2 西南官話入聲調今讀降調型的方言點例舉表
但需注意的是,四川西部存留入聲調的方言片區,其入聲調型主要是平調型(絕大多數為33調值,樂山、雅安一帶的部分方言點為55調值),這應當與該地區彝語北部方言的影響有關。因為,彝語北部方言主要分布在四川,“北部次方言的全部元音都分松緊兩套,但只在?33、?44兩調構成對立。南部次方言只有一部分元音分松緊兩套(如會理、布拖都只有?:??與u:u?兩套,只在?55調構成對立)[12]174,作為當初失去塞音韻尾而以帶緊喉為補充的入聲,受彝語等平調緊元音的影響,自然會向趨平調型的方向演變;此外,西南官話入聲原曲折點演變為讀平調,同樣符合音理簡化省力的原則,故川西入聲今讀平調型并不難以理解。
除此之外,湖北的宣恩、興山、來鳳和湖南的吉首、保靖等少數方言點的陽平,存在讀低平調的情況,這些方言點的陽平一般體現為11調值。實際上,陽平讀低平調的方言點在武昆片中的數量比較有限,其陽平讀低平調的原因,一方面是與語流音變的影響有關,另一方面也與調查者個人的音位處理有關。據《湖北方言調查報告》(1974)記載顯示,1936年的湖北武昌話“陽平由‘半低’降至‘低’再升至‘中’(213),寬式用低降升調(313)。兩陽平字連在一起或一個陽平字跟別的字連在一起,就很容易變成低平調(11)”[7]52,可見,陽平當時在武昌話中讀低平調,顯然屬于語流音變影響的結果。另,湖北來鳳“陽平是低平調11,但有時調尾也略升12”[7]456,利川“陽平是低平調11,有時也因語氣關系,讀成微降調21”[7]477;據《湖南方言調查報告》記錄,湖南吉首在1935年(當時稱乾城)的陽平調,嚴式記音為“低微降調(21),寬式一律作低平調(11)”[13],湖南保靖話的陽平在當時與吉首的情況相同。根據這些記音材料的表述,大致可以看出,這些方言點的陽平調其實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低平調,實際上絕大多數均為低降調。例如,李啟群在《吉首方言研究》(2002)音系中,把吉首話的陽平調標為11調值,但特別說明“陽平實際調值為21”[14]。因此,宣恩、吉首等這些方言點的陽平讀低平調,很可能是調查者對音位寬嚴的把握處理不同所致。
四、武昆片語音特征的類化影響
西南官話入聲存留型方言中,至今尚有104個方言點保留獨立的入聲調(已失去塞音韻尾)。[1]根據演變趨勢,可以推斷,西南官話今為入聲調存留型的方言點,除靠近雅棉片(其入聲可能會演變為陰平)和毗鄰仁富片(其入聲可能會演變為去聲)的方言點外,其余絕大部分方言點的入聲調都很有可能要向陽平調靠攏并混同。究其緣由,除部分方言點屬調型相似而歸并之外,還存在武昆型(入聲歸陽平)的強勢影響而類化所致的因素。關于入聲類化歸讀陽平的情況,曲靖地區方言入聲調的演變歸并趨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根據《云南方言報告》(1969)記載,20世紀40年代初期的曲靖、陸良和沾益,在滇中一帶形成一個曲折調型(312調值)的入聲方言島[15]695-673,但至遲到20世紀90年代末,沾益和曲靖的入聲便已歸讀陽平[16]。據《云南省志·漢語方言志》(1989)顯示,曲靖地區1市8縣的去聲均為213調值,目前僅有陸良一處存在入聲調,其調值為312,與20世紀40年代的入聲調值相同。據筆者本人于2010年的調查,曲靖市麒麟區的聲調情況是:陰平44、陽平是53、上聲42、去聲213、入聲312,麒麟區的入聲顯然仍屬于一個獨立的調類,它與陽平的調值區別明顯,反倒與入聲極為近似。按音理來說,曲靖地區的入聲應該與去聲相混,但依據已經相混的實際例子(如沾益等)來看,他們的未來演變只能混入陽平。因為,中古入聲調在云南方言中一般都混入陽平調,當地存在入聲調的方言點,受此類型的強勢影響,其入聲在未來演變中,必然會受到周邊方言的強勢而類化歸讀陽平。筆者2015年12月,曾對曲靖麒麟區茨營鄉海三凹村的語音進行實地調查,發現海三凹村的入聲已經歸讀陽平。從該地區的入聲嚴式和寬式的記音區別上我們已經能看出這種類化演變的端倪。據《云南方言報告》(1969)的記錄,1940年曲靖城內話的入聲是“低微降升調(312),寬式一律用低降調(31)”[15]730,其寬式31調值的記音,無論調型還是調值,均已與當時的陽平(42調值)趨同。由此可見,曲靖地區入聲調演變歸讀陽平調的現象,至遲在20世紀40年代便已經初現端倪。
通過曲靖地區入聲演變實例可以看出,武昆片入聲歸讀陽平的語音特點,因其分布范圍廣,在西南官話中有著較強的影響力,一直在影響并類化著西南官話絕大多數入聲調的演變方向。可以預計,在西南官話入聲存留型方言中,除靠近雅棉片(入聲歸陰平)和仁富片(入聲歸去聲)的方言點會出現少數例外之外,絕大多數方言點因受武昆片語音特征的強勢類化影響,其入聲不管今讀調型調值如何,他們未來都將呈現出向陽平調趨同的類化演變趨勢。
五、結語
武昆片在西南官話中的語音特征是入聲歸讀陽平,根據調型和調值相似歸并的原則,可知入聲和陽平在今武昆片方言較早時期未歸并前,他們應該有著相近的調型和調值,這是早期二者演變混同的基礎。但通過統計分析,發現陽平在武昆片中的今讀調值和調型還存在一定的地域差異(有平調、升調、降調、曲折調),這說明現在武昆片的語音特征雖然結果一致,可是他們的演變過程并不完全相同。論文以語言事實為基礎,通過韻書考證,參輔以移民史實并借助語言接觸等相關理論,認為陽平和失去塞音韻尾后的入聲,在西南官話的早期均是一個中低降升的曲折調,二者在調值上應非常相近,這是二者后來演變混同的基礎;至于武昆片陽平的今讀調型呈現出的區域性差異,除存在聲調“簡化”演變的內因外,應與湘語、贛語和少數民族語言等的接觸影響有關。此外,語音流變,照顧音系區別格局,甚至調查者個人的對同一音位處理把握標準不同等,均會導致陽平的今讀型調值產生差異。西南官話近五分之四的方言點屬于武昆片,它在西南官話中屬于強勢型方言,其語音特征總是在影響并類化著西南官話今入聲存留型方言點的演變方向和趨勢。
一直以來,因可資參考的韻書文獻有限,而僅存的歷史韻書因條件所限,其對當時調型調值的記錄又非常模糊,故人們很少討論西南官話武昆片語音特征的歷時演變。筆者于文中雖構擬了西南官話早期入聲和陽平的調型和調值,也分析了武昆片陽平今讀調型產生地域差異的原因,可對后者(即調型的地域差異)的歷史演變層次并未做深入探討。例如,陽平在不同地域所呈現出的調型差異,彼此之間是否存在演變層次的先后關系(抑或是平行演變),是入聲混入陽平后的演變還是入聲和陽平各自演變至調型相似再混同等,均需繼續探究。
注釋:
① 《漢音集字》(HAN KOWSYL LABARY)是美國人英格爾(J.A.Ingle)于1899年(清光緒二十五年)在漢口編錄、由“公興”(Kung Hing)刊印的一本漢口方言同音字匯,它記錄了100年前的漢口(即今武漢)方音。
② 葛劍雄《簡明中國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中指出:“自唐中葉南詔獨立以后,在長達六百年的時間內,云南處于中原王朝的版圖之外。到元代初年重新統治云南之前,這里已經沒有漢語的地位。明代初年,中央政府通過調撥軍隊戍守屯墾實施了對云南和貴州二地的移民,駐守云貴的軍士以蘇、皖二省籍為主……清代云、貴地區接受的移民主要來自四川、湖南和江西。”(第614頁)
③ 湘鄂地區西南官話陽平調值多為升調,但沿陜南接壤的鄂西北至鄂東,地域上與河南省和安徽省接壤這一狹長地帶,它們陽平調均為降調,這與西南三省的陽平調型相同,而與周邊方言的陽平調型異,這是很奇怪的,或許與西南官話的強勢影響有關。
④ 云南地方志編委會《云南省志·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提到:彝語“聲調都能與緊元音結合,但與緊元音結合的33調,一般是21調或55調的變調。緊元音調都比松元音調響亮且高一些。緊元音的21調,其調值是32短緊調。”(第34頁)
[1] 牟成剛.西南官話立區標準及內部分片依據的再探討[J].文山學院學報,2014(4):63-70.
[2] 牟成剛.西南官話音韻研究[D].廣州:中山大學,2012.
[3] 王士元.聲調發展方式一說[J].語文研究,1988(1):38-42.
[4] 李如龍.漢語方言特征詞研究[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16.
[5] Hemeling,K.The Nanking Kuan Hua[D].Shanghai:Printedat the German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House,Publishedat the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02.
[6] 北大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漢語方音字匯[M].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13.
[7] 趙元任.湖北方言調查報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48.
[8] 李藍.西南官話的分區(稿)[J].方言,2009(1):72-87.
[9] 陳暉.湘方言語音研究[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10]胡萍.湘西南漢語方言語音研究[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159.
[11]楊光遠,趙巖社.云南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概論[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12]陳士林,邊仕明,李秀清.彝語簡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13]楊時逢.湖南方言調查報告[M].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4:730.
[14]李啟群.吉首方言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17.
[15]楊時逢.云南方言調查報告[M].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9.
[16]云南地方志編委會.云南省志·漢語方言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