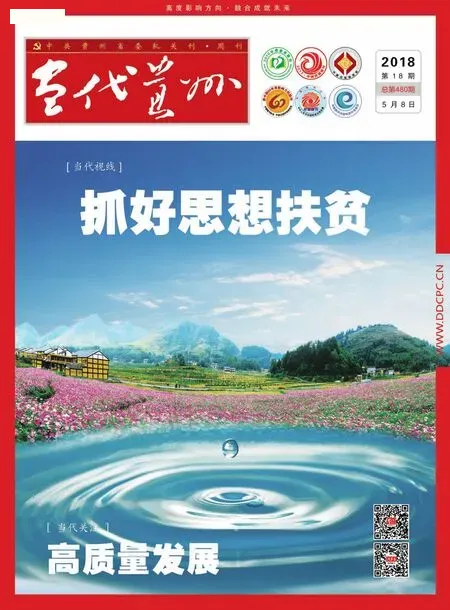追求“美善合一”

劉悅笛
魯迅先生曾有句名言:“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fā)展。”
中國的發(fā)展也是按照這個歷史邏輯走過來的,我們曾在艱難的國際環(huán)境當中活下來,然后在二戰(zhàn)與內(nèi)戰(zhàn)后讓民眾獲得溫飽,最后才是在基本條件滿足后獲得發(fā)展。這個歷史發(fā)展的邏輯,順序不能亂,也不可能亂,因為后一項的實現(xiàn),皆是以前一項的實現(xiàn)作為現(xiàn)實基礎的,從生存直接跨越到發(fā)展根本不可能,也不能倒著來,在這一點上還真是要講究所謂“吃飯哲學”的。
這句名言出自1925年5月8日,魯迅給剛創(chuàng)刊的《豫報周刊》兩位編輯呂琦和向培良的回信。他們是魯迅在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教書時的學生,想邀請魯迅給周刊投稿。盡管魯迅因力不從心而謝絕,卻寫下這一封著名的信札,史稱《北京通信》。該文發(fā)表于同年5月14日的《豫報副刊》,后收入著名的《華蓋集》。
從生存、溫飽到發(fā)展,這本是對于青年人的出路的回答,說給青年人的鼓勵之語,后來大而化為對整個國家而言。道理其實很簡單,誠如墨子所言:“食必常飽,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麗,居必常安,然后求樂。”這符合人類滿足的層層上升的金字塔結(jié)構,但每個人所停留的層級并不相同。
回信中,魯迅還說了一句至理箴言:“我之所謂生存,并不是茍活;所謂溫飽,并不是奢侈;所謂發(fā)展,也不是放縱。”
在發(fā)展的進程中,也會出現(xiàn)一些問題。比如,有了條件就一味追求享樂,有了盈余就一味地追求奢侈,有了滿足便一味地追求放縱。那些以為越貴就是越美的“奢侈品”買賣,恰恰以價格取代了價值;那些靠整容技術而成的“網(wǎng)紅臉”主流追求,往往犧牲了自然而過于人工;那些以欲望宣泄為目的“娛樂至死”的大眾文化,常常干脆混淆了美感與快感之分。我們?nèi)允前l(fā)展中國家,人均生產(chǎn)總值還很低,在如此條件下追求奢華、奢侈與奢靡,無疑不具有歷史的合法性。
我們已把“美好生活”區(qū)分為“美生活”與“好生活”,前者是有質(zhì)量的生活,后者則是有品質(zhì)的生活,二者必須是統(tǒng)一的。那么,如今部分人追求豪華和富豪式的文化與審美,恰恰是以一種極端的方式來追求“以奢侈為美”,而絲毫不顧及“好生活”才是“美生活”的現(xiàn)實根基。
當今中國的一些怪現(xiàn)象,仍是以“好生活”的極端標準,來壓倒甚至取替了“美生活”的標準,盡管它們還打著追求美的幌子,但卻出現(xiàn)了太多“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現(xiàn)象。這種以求富、求奢、求侈的大款式審美,恰恰是為了少數(shù)人服務的。這就忘記了,審美乃是為了每個人服務的。
審美為大眾服務,而不是源于簡化而造成美感不足,或者追求繁復而令人審美疲勞。我們一些建筑、社區(qū)與城市設計,就離開了“以人為本”的核心,一面是為了追求簡易做減法,許多小區(qū)道路被弄得橫平豎直,而民眾卻在草地上踩出一條更近的捷徑;另一面則是為了尋求復雜做加法,很多建筑的裝飾基本上皆為附加品,并未將審美與實用性結(jié)合起來。實際上,審美不是奢侈,越符合以人為本的設計,才越是“美善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