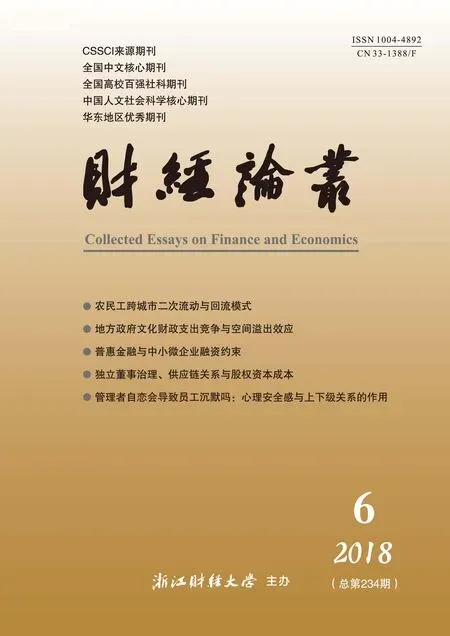貨幣政策對宏觀杠桿率缺口的影響研究
劉 穎
(北京大學經(jīng)濟學院,北京 100871)
一、引 言
近年來,我國宏觀杠桿率的快速上升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guān)注。分部門的分析發(fā)現(xiàn),我國主要是企業(yè)部門的杠桿率過高,政府和居民部門的杠桿率雖在逐步上升,但仍低于國際水平。不少學者擔心過高的杠桿率可能增加金融風險,甚至引發(fā)金融危機。相對樂觀的分析雖然不認為我國會很快發(fā)生金融危機,但也認為宏觀杠桿率已經(jīng)過高。如何降低中國宏觀杠桿率已成為政府部門和學界關(guān)心的重要問題。
一國宏觀杠桿率主要有三種衡量方式:一是各部門總債務(wù)與名義GDP的比值;二是社會融資余額與名義GDP的比值;三是廣義貨幣供應(yīng)量與名義GDP的比值。三種杠桿率是相通的,因為它們的增長路徑往往較為類似[1]。
近年來不少文獻研究了杠桿率對經(jīng)濟的影響,并提出了相應(yīng)的降杠桿措施。Schularick和Taylor(2009)基于新的歷史數(shù)據(jù)分析了14個發(fā)達國家1870~2008年貨幣、信貸和金融危機的關(guān)系,發(fā)現(xiàn)過快的信貸增長是金融危機的有力預測指標[2]。Elekdag和Wu(2011)對歷史上發(fā)達國家和新興經(jīng)濟體的99次信貸繁榮進行了事件研究,發(fā)現(xiàn)寬松貨幣政策可能導致信貸過快增長,而信貸的過快增長有可能引發(fā)金融危機[3]。Reinhart和Rogoff(2011)認為私人部門債務(wù)的迅速增長容易導致銀行危機[4]。Gertler 和Hofmann(2016)基于戰(zhàn)后46個經(jīng)濟體的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信貸增長是金融危機的重要領(lǐng)先指標[5]。
中國人民銀行杠桿率研究課題組(2014)認為,我國宏觀杠桿率總體可控,當前的最大風險是地方政府和非金融企業(yè)杠桿率較高的結(jié)構(gòu)性風險以及經(jīng)濟減速可能導致的償債風險。我國目前應(yīng)警惕高杠桿帶來的風險,但不可盲目采取去杠桿措施,而應(yīng)該利用仍然存在的杠桿率空間,優(yōu)化杠桿結(jié)構(gòu),在經(jīng)濟增長過程中逐漸降低杠桿率[6]。
紀敏、嚴寶玉、李宏瑾(2017)從MM定理的微觀視角和經(jīng)濟增長方式的宏觀視角出發(fā),研究了中國杠桿率結(jié)構(gòu)和水平的經(jīng)濟學機理及其與金融穩(wěn)定的關(guān)系,認為投資主導型經(jīng)濟增長模式導致了中國較高的杠桿率水平。盡管高杠桿可能影響金融穩(wěn)定,但各國杠桿率水平的風險閾值不同,債務(wù)效率和債務(wù)內(nèi)外結(jié)構(gòu)對債務(wù)可持續(xù)性從而金融穩(wěn)定有重要影響[7]。
宋國青(2000)研究了貨幣政策對于M2/GDP的影響,發(fā)現(xiàn)當積極貨幣政策導致M2增加時,GDP可能會增加得更快,從而導致M2/GDP下降;而緊縮的貨幣政策則可能導致M2/GDP上升[8]。宋國青將這一現(xiàn)象稱為“越少越多的貨幣”,原因在于以M2/GDP衡量的廣義貨幣流通速度具有順周期性。劉曉光、張杰平(2016)利用修正的動態(tài)隨機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了宋國青“越少越多的貨幣”的思想,理清了這一現(xiàn)象的作用機制,并發(fā)現(xiàn)在存在金融加速器效應(yīng)的情況下,這一影響機制還會得到進一步加強[1]。宋國青(2013)認為貨幣產(chǎn)出比的長期趨勢與資本產(chǎn)出比有關(guān),而短期貨幣增長率和貨幣產(chǎn)出比增長率可能有負的相關(guān)性[9]。
總結(jié)相關(guān)文獻可以看出,不少研究認為寬松的貨幣政策會導致信貸過快增長,從而引起宏觀杠桿率的上升。不過劉曉光、張杰平(2016)和宋國青(2000)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證實了積極貨幣政策可能降低宏觀杠桿率[1][8]。為什么會有這種差別?這可能是由于信貸利用的方式不同造成的。若信貸被用于過度消費或資產(chǎn)投機,則新增信貸不會帶來名義GDP的增長,反而可能引發(fā)金融危機,這就導致了杠桿率上升和金融危機的相關(guān)性。而中國的信貸增長大多用于實體經(jīng)濟生產(chǎn),這帶來了名義GDP的增長,也就可能降低杠桿率。
然而劉曉光、張杰平(2016)和宋國青(2000)的研究忽視了一國宏觀杠桿率可能有著自己的趨勢,貨幣政策影響的實際是宏觀杠桿率圍繞其趨勢的波動[1][8]。宋國青(2013)認識到了貨幣產(chǎn)出比的長期趨勢與資本產(chǎn)出比有關(guān),而短期貨幣增長率和貨幣產(chǎn)出比增長率可能有負的相關(guān)性,不過他沒有從模型和實證角度分析這一結(jié)論[9]。本文試圖在索洛增長模型中通過國家資產(chǎn)負債表的思想引入金融因素,以研究宏觀杠桿率的演化路徑以及貨幣政策對宏觀杠桿率缺口的影響。
二、從索洛增長模型看實際資本產(chǎn)出比趨勢
考慮加入產(chǎn)能利用率的索洛增長模型。設(shè)實際資本存量為K,總?cè)丝跒長,產(chǎn)能利用率為α,因此生產(chǎn)函數(shù)為Y=F(αK,L)。設(shè)y=Y/L,k=K/L,這樣生產(chǎn)函數(shù)可寫為人均的形式y(tǒng)=f(αk)。經(jīng)濟儲蓄率設(shè)為s,投資I=sY,人均投資為i=sy,經(jīng)濟折舊率為δ。考慮一個經(jīng)濟從很少的資本存量開始發(fā)展,逐漸達到穩(wěn)態(tài),則該經(jīng)濟的投資先是一直大于折舊,有sf(αk)>δk,達到穩(wěn)態(tài)時投資等于折舊,有i=sf(αk)=δk。這樣該經(jīng)濟的資本產(chǎn)出比k/f(αk)將從某個小于s/δ的值逐漸變大,在穩(wěn)定時等于s/δ,此后則保持穩(wěn)定。為了更直觀地展示這一結(jié)論,我們設(shè)定具體的函數(shù)形式和參數(shù)值,并繪出資本產(chǎn)出比的動態(tài)路徑。不妨設(shè)α=0.8,s=0.29,δ=0.0975,k1=4.57,y=(αk)0.6,由此可計算每一期資本產(chǎn)出比的數(shù)值(圖1)。
從圖1可以看出,在一國經(jīng)濟未達穩(wěn)態(tài)時,其實際資本產(chǎn)出比有一個時間趨勢,達到穩(wěn)態(tài)后資本產(chǎn)出比保持穩(wěn)定。一國經(jīng)濟如果從很少的資本存量開始發(fā)展,可能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才能達到穩(wěn)態(tài)。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資本存量很低,所以中國資本產(chǎn)出比應(yīng)當有著時間趨勢。我們簡單計算中國的實際資本產(chǎn)出比趨勢看是否符合理論預測。以1990年為基期,1990年的實際資本產(chǎn)出比設(shè)為2.1,固定資本折舊率取9.75%,所有數(shù)據(jù)取自《2016中國統(tǒng)計年鑒》,計算我國實際資本產(chǎn)出比趨勢(圖2)。

圖1 一國實際產(chǎn)出比時間趨勢

圖2 我國實際資本產(chǎn)出比
由圖2可知,我國資本產(chǎn)出比在1990~2007年保持略有上升的趨勢,2007年后變?yōu)檠杆偕仙1容^中國實際資本產(chǎn)出比的趨勢值和模擬值,可以發(fā)現(xiàn)2007年后中國資本產(chǎn)出比的上升比較符合理論預測,但這之前中國資本產(chǎn)出比只是略微上升。為什么中國實際資本產(chǎn)出比在2007年之前可以在較長時間內(nèi)基本保持穩(wěn)定而2007年之后卻迅速上升?本文認為存在著三個重要原因:一是農(nóng)業(yè)部門向非農(nóng)部門勞動力轉(zhuǎn)移率的變化,二是國內(nèi)投資占總儲蓄的變化,三是投資效率的變化。
先考慮勞動力轉(zhuǎn)移的作用。勞動力轉(zhuǎn)移相當于非農(nóng)部門的人口在短期內(nèi)可以大量增長,這使得非農(nóng)部門的資本產(chǎn)出比的上升趨勢大為減緩。不妨在以上例子中設(shè)定一些參數(shù)模擬這一機制。假設(shè)上述例子的設(shè)定代表非農(nóng)部門,并忽略農(nóng)業(yè)部門,設(shè)由勞動力轉(zhuǎn)移導致的非農(nóng)部門勞動力增長率為nt,這樣每期人均凈投資變?yōu)閗t-kt-1=syt-(δ+nt)kt-1。可見勞動力轉(zhuǎn)移的存在使每期人均凈投資減少,減少的數(shù)量取決于勞動力轉(zhuǎn)移的速度。在城市化初期,一個近似的假設(shè)是農(nóng)業(yè)部門在某一固定工資上有無限勞動力供給,這樣勞動力轉(zhuǎn)移速度取決于城市部門投資,并使得城市部門的人均凈投資不變。而隨著農(nóng)業(yè)部門剩余勞動力越來越少,非農(nóng)部門投資引起的勞動力轉(zhuǎn)移也越來越少,最終城市化完成,非農(nóng)部門勞動力不再增長[10]。由此,我們設(shè)定初始資本產(chǎn)出比為2.1,由s/(δ+n)=21,得每期勞動力轉(zhuǎn)移率為4%。假設(shè)此后勞動力轉(zhuǎn)移率每期減少0.025%,分20期減小到3.5%,此后每期減少0.5%,分7期減少到0,由此計算每期的資本產(chǎn)出比(圖3)。

圖3 存在勞動力轉(zhuǎn)移時一國實際產(chǎn)出比時間趨勢
由圖3模擬結(jié)果可見,存在勞動力轉(zhuǎn)移時,一國資本產(chǎn)出比上升幅度要小于原來趨勢。當勞動力轉(zhuǎn)移率很高時,一國資本產(chǎn)出比上升緩慢,而隨著勞動力轉(zhuǎn)移率的下降,一國資本產(chǎn)出比會迅速上升。下面我們計算中國的勞動力轉(zhuǎn)移率,看是否符合這種假說。簡單將勞動力轉(zhuǎn)移率定義為第二和第三產(chǎn)業(yè)的勞動力增長率,數(shù)據(jù)來源于CEIC數(shù)據(jù)庫,計算結(jié)果見圖4。需要指出的是1990年的數(shù)據(jù)相對于其他年份比較反常,胡景北(2008)指出這可能是由純粹的統(tǒng)計原因?qū)е碌模虼?990年的數(shù)據(jù)和其他年份不可比[11]。

圖4 中國勞動力轉(zhuǎn)移率
由圖4可以看出,中國勞動力轉(zhuǎn)移率在2007年之后確實下降了一個臺階,正如上文分析的,這對于我國2007年后資本產(chǎn)出比的快速上升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來考慮國內(nèi)投資占GDP比例的變化。以上模型假設(shè)本國儲蓄全部用于國內(nèi)投資,不過在開放經(jīng)濟條件下,一國儲蓄除了用于國內(nèi)投資還可用于出口。在儲蓄率不變的情況下,國內(nèi)投資占儲蓄的比例越高,一國國內(nèi)的資本產(chǎn)出比就越高。我國1990~2015年儲蓄率與投資率如圖5所示,數(shù)據(jù)取自《2016中國統(tǒng)計年鑒》。

圖5 我國儲蓄率與投資率
圖5顯示,2007年后我國儲蓄率較為穩(wěn)定,但國內(nèi)投資率大幅上升,這導致每一期的增量資本產(chǎn)出比上升。這些投資的資本持續(xù)存在于經(jīng)濟中,促使經(jīng)濟資本存量的大幅上升,對2007年后資本產(chǎn)出比的上升有重要促進作用。
第三則是投資效率的變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我國采取了大規(guī)模的經(jīng)濟刺激政策,導致經(jīng)濟增長率的短期上升,但刺激政策的效果衰退后,產(chǎn)出開始下滑。特別是近幾年來,民間投資持續(xù)下滑,政府投資成為總需求的重要支撐。然而相對于民間投資,政府投資的效率較低,這也是近幾年中國資本產(chǎn)出比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
當然,中國的資本產(chǎn)出比的上升可能還存在其他原因,不過以上三個原因可能是最重要的。本節(jié)的分析表明,中國的實際資本產(chǎn)出比確實存在著自己的趨勢,這是本文接下來研究的基礎(chǔ)。
以上分析沒有考慮金融因素,也就無法考慮宏觀杠桿率的變化。現(xiàn)我們從國家資產(chǎn)負債表的角度在上述模型中引入金融因素,建立宏觀杠桿率與實際資本產(chǎn)出比的關(guān)系。
三、從國家資產(chǎn)負債表看宏觀杠桿率

表1 初始經(jīng)濟國家資產(chǎn)負債表 單位:元

現(xiàn)向經(jīng)濟中引入銀行、企業(yè)。由于資本屬于家庭,企業(yè)部門要利用資本展開生產(chǎn)須先通過借貸方式從家庭獲得資本。企業(yè)有三種借貸方式,一是向家庭發(fā)行股票,設(shè)為St-1;二是向家庭發(fā)行企業(yè)債券,設(shè)為Bt-1;三是向銀行貸款,設(shè)為Dt-1。企業(yè)貸款后會得到相應(yīng)數(shù)量的存款,再用銀行存款與家庭交換其資本。通過以上步驟,家庭手中的資本就全部轉(zhuǎn)到企業(yè),家庭持有企業(yè)股權(quán)、債券、銀行存款作為企業(yè)的借貸憑證。資本轉(zhuǎn)移完成后國家資產(chǎn)負債表如表2所示。

表2 資本轉(zhuǎn)移后國家資產(chǎn)負債表 單位:元

由以上設(shè)定,所有債權(quán)資本的實際價值為Kdt-1,Dt-1+Bt-1=Kdt-1Pt-1,由此居民所得本期利息為:
Rt=(Dt-1+Bt-1)it
=Rdt+Rpt
(1)

由以上分析可知,若費雪效應(yīng)完全成立,則居民債權(quán)資產(chǎn)不會貶值,也沒有工資損失。否則,債權(quán)資產(chǎn)會出現(xiàn)貶值,貶值的部分變?yōu)楣善钡膬r值。居民工資的損失也會變成企業(yè)利潤。由于企業(yè)屬于居民,所以無論費雪效應(yīng)成立與否,居民的收入不變,都等于本期產(chǎn)出。居民的資產(chǎn)總值也不變,但會在股權(quán)和債權(quán)之間重新分配。
經(jīng)過生產(chǎn)和分配,居民名義收入為YtPt,設(shè)本期儲蓄率為st,則本期投資為I=stYt=stF(αKt-1,Lt)。本期儲蓄以銀行存款、企業(yè)債券及股權(quán)形式持有,即stYtPt=D1t+B1t+S1t。假設(shè)企業(yè)貸款支付用于彌補家庭債權(quán)資產(chǎn)貶值的利息Rpt,這樣本期結(jié)束時企業(yè)貸款和居民存款都為Dt=Dt-1+D1t+Rpt,企業(yè)債券為Bt=Bt-1+B1t,企業(yè)股票為St=St-1+S1t。這樣一輪生產(chǎn)后國家資產(chǎn)負債表如表3所示。

表3 一輪生產(chǎn)后的國家資產(chǎn)負債表 單位:元
注:當費雪效應(yīng)不完全時,債權(quán)人會有部分財富轉(zhuǎn)移到股權(quán)人,體現(xiàn)為股票St-1升值,以上資產(chǎn)負債表用的是股票的發(fā)行價St-1,沒有體現(xiàn)這種變化。
定義社會融資規(guī)模為AFt-1=Dt-1+Bt-1+St-1,包括債務(wù)融資和股權(quán)融資兩個部分,其中債務(wù)價值為DBt-1=Dt-1+Bt-1。注意到債務(wù)和股權(quán)融資比例的改變可以影響宏觀杠桿率,為了單純研究貨幣政策的影響,我們假設(shè)經(jīng)濟中每一期債務(wù)融資的比例為θ始終不變,有θ=B1t/stYtPt。再假設(shè)預期是理性的,費雪效應(yīng)始終成立,則存量債務(wù)也不會貶值,其和總資產(chǎn)的比例也一直為θ。這樣宏觀杠桿率為DBt-1/YtPt=Kdt-1Pt-1/YtPt=θKt-1Pt-1/YtPt=(Kt-1/Yt)(θPt-1/Pt)。
結(jié)合索洛模型的結(jié)論,若經(jīng)濟不處于穩(wěn)態(tài),但通脹穩(wěn)定,則宏觀杠桿率和實際資本產(chǎn)出比一樣,都會有一個趨勢,貨幣政策會導致宏觀杠桿率圍繞其趨勢波動。現(xiàn)考慮貨幣政策通過產(chǎn)能利用率和通貨膨脹渠道對宏觀杠桿率圍繞其趨勢波動的影響。積極貨幣政策會提高私人部門的產(chǎn)能利用率和經(jīng)濟的通貨膨脹,這導致本期名義產(chǎn)出增加,從而使得宏觀杠桿率向下偏離其趨勢。同理可知,緊縮的貨幣政策將使宏觀杠桿率向上偏離其趨勢。


=θKt-1/Yt+1/vt
(2)
如果經(jīng)濟繁榮時貨幣流通速度加快,則1/vt會減小。這樣等式右邊隨貨幣政策的寬松而減小,因此寬松貨幣政策會導致宏觀杠桿率向下偏離其趨勢。
四、實證分析
由上文分析可知一國擴張的貨幣政策將導致一國杠桿率向下偏離其趨勢,也即杠桿率缺口為負;相反,緊縮的貨幣政策則會產(chǎn)生正的杠桿率缺口。本節(jié)將利用VAR方法驗證這一結(jié)論。VAR模型設(shè)置如下:
(3)
其中,t代表時間,Yt為模型包括變量組成的向量,n為模型滯后階數(shù),εt為服從標準正態(tài)分布的隨機擾動,Γj(j=0,1,…,n) 為待估計參數(shù)。進入VAR模型的變量為貨幣政策代理變量和杠桿率缺口。為了與劉曉光、張杰平(2016)和宋國青(2000;2013)的研究互相參照,本文選取M2增長率作為貨幣政策代理變量,選取M2/GDP作為杠桿率的衡量指標[1][8][9]。M2和GDP數(shù)據(jù)為1990~2016年的年度數(shù)據(jù),數(shù)據(jù)來源于CEIC數(shù)據(jù)庫。M2增長率用對數(shù)差分法求得,記為gM2t。利用H-P濾波法得到M2/GDP的周期序列,根據(jù)M. O. Ravn和H. Uhlig(2002)的研究,年度數(shù)據(jù)可選參數(shù)λ等于6.25,這樣得到M2/GDP的周期序列,即為桿桿率缺口,記為(M2/GDP)ct[12]。中國M2環(huán)比與杠桿率缺口如圖6所示。可以看出,M2環(huán)比與杠桿率缺口之間可能有著負相關(guān)關(guān)系。
下面利用VAR方法分析貨幣政策對桿杠率缺口的影響。經(jīng)檢驗,gM2t和(M2/GDP)ct都是平穩(wěn)的,這樣兩個變量都可以直接進入VAR模型,Yt=(gM2t,(M2/GDP)ct)。利用Eviews軟件檢驗得到模型的最佳滯后階數(shù)為3階,最后得到杠桿率缺口對M2沖擊的脈沖響應(yīng)函數(shù)(圖7)。

圖6 中國M2環(huán)比與杠桿率缺口

圖7 杠桿率缺口對M2沖擊的脈沖響應(yīng)函數(shù)
從脈沖響應(yīng)函數(shù)可以看出,當受到M2增長率一單位正向沖擊時,杠桿率缺口先是略微上升,然后迅速下降,在接近2.5期的時候變?yōu)?,此后逐漸負向增大,在第三期下降到最低值,然后再開始上升,逐步向0回歸。這證實了本文模型的結(jié)論,即積極的貨幣政策將導致杠桿率向下偏離其趨勢。
五、結(jié) 論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宏觀杠桿率迅速上升。本文通過國家資產(chǎn)負債表的思想,在索洛增長模型中引入了金融因素。分析表明,一國經(jīng)濟在未達到穩(wěn)態(tài)之前,其杠桿率會有一個上升的趨勢,而一國積極貨幣政策會導致該國宏觀杠桿率從趨勢向下偏離。實證研究證實了這種猜測。本文對于我國貨幣政策有一定的啟示:其一,不應(yīng)貿(mào)然確定一個目標杠桿率,因為我國經(jīng)濟可能并未達到穩(wěn)態(tài),這樣我國宏觀杠桿率的上升就是經(jīng)濟的自然規(guī)律;其二,不應(yīng)試圖用緊縮貨幣的方法來降低杠桿率,如本文所證實的,過度緊縮的貨幣政策只會導致更高的杠桿率。
需要強調(diào)的是本文的結(jié)論是在假設(shè)封閉經(jīng)濟以及國家儲蓄率和融資結(jié)構(gòu)不變的情形下得出的。那么儲蓄率以及融資結(jié)構(gòu)的變化會如何影響本文的結(jié)論呢?先考慮儲蓄率的變化。如果我國經(jīng)濟由投資驅(qū)動轉(zhuǎn)型為消費驅(qū)動,由索洛增長模型知,一國穩(wěn)態(tài)資本產(chǎn)出比為k/f(αk)=s/δ,因此,即使融資結(jié)構(gòu)不變,一國儲蓄率的長期下降也將導致一國宏觀杠桿率下降。不過這不意味著短期內(nèi)通過改變儲蓄率來降低宏觀杠桿率是可行的,因為儲蓄率通常很難被短期政策改變。此外,儲蓄率下降導致的經(jīng)濟穩(wěn)態(tài)資本產(chǎn)出比的變化也可能需要較長時間。這是封閉經(jīng)濟下的結(jié)論。當一國可以出口商品時其儲蓄率和投資率就不再一致。如果中國將來出口增大,這可能導致國內(nèi)實際資本產(chǎn)出比上升趨勢減緩,相應(yīng)的也會導致以國內(nèi)總負債比GDP衡量的宏觀杠桿率的上升趨勢減緩。如果出口所得外匯在國內(nèi)結(jié)匯形成貨幣,那么以M2/GDP衡量的杠桿率的上升趨勢就未必會因出口增加而減緩了。最后考慮融資結(jié)構(gòu)的問題。如前文所分析的,不考慮交易貨幣的話,以市場價衡量的一國社會融資規(guī)模與名義產(chǎn)出的比等于實際資本產(chǎn)出比*這句話在采用市場價計算股票價值時才成立。本文定義的社會融資規(guī)模采用的是股票發(fā)行價,這樣定義的社會融資規(guī)模體現(xiàn)不出因費雪效應(yīng)不完全導致的股票升值,會導致社會融資規(guī)模與固定資產(chǎn)市值不一致,社會融資規(guī)模與名義GDP之比也就不再等于實際資本產(chǎn)出比。。這樣,當股權(quán)融資占存量社會融資規(guī)模的比例越大,債權(quán)融資的比例就越小,一國宏觀杠桿率也就越小。未預期通貨膨脹將導致債權(quán)財富損失,并轉(zhuǎn)變?yōu)楣蓹?quán)財富,實際上相當于存量股權(quán)融資增加,這也會導致杠桿率上升趨勢減緩。結(jié)合以上分析可知,長期來看降低我國宏觀杠桿率的合理方法是擴大總消費,減小國民儲蓄率并且逐步發(fā)展資本市場,擴大股權(quán)融資的比例。
一國在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不同階段有著不同的最優(yōu)融資結(jié)構(gòu)。在我國勞動密集型產(chǎn)業(yè)具有巨大比較優(yōu)勢的時候,對創(chuàng)新的需求并不緊迫,這使得以銀行為主的債權(quán)融資符合經(jīng)濟的需要,也導致我國宏觀杠桿率不斷上升。隨著我國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比較優(yōu)勢的逐漸喪失,產(chǎn)業(yè)升級的要求也越來越迫切,這就需要擴大股權(quán)融資的比例來支持經(jīng)濟中的創(chuàng)新。因此從融資結(jié)構(gòu)的角度看,我國確實需要不斷增加股權(quán)融資的比例。在我國出口增長潛力減小的情況下,這也是降低宏觀杠桿率最主要的方式。
參考文獻:
[1] 劉曉光,張杰平.中國杠桿率悖論——兼論貨幣政策“穩(wěn)增長”和“降杠桿”真的兩難嗎?[J]. 財貿(mào)經(jīng)濟,2016,(8):5-19.
[2] Schularick M.and Taylor A.M. Credit Booms Gone Bust:Monetary Policy,Leverage Cycles and Financial Crises,1870-2008[Z]. NBER Working Paper,2009,No.15512.
[3] Elekdag S.A. and Yiqun Wu. Rapid Credit Growth:Boon or Boom-bust?[Z]. IMF Working Paper,2011,No.11/241.
[4] Gertler P. and Hofmann B. Monetary Facts Revisited[Z]. BIS Working Paper,2016,No.556.
[5] Reinhart C. and Rogoff K.From Financial Crash to Debt Crisis[J].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2011,101(5):1676-1706.
[6] 中國人民銀行杠桿率研究課題組.中國經(jīng)濟杠桿率水平評估及潛在風險研究[J]. 金融監(jiān)管研究,2014,(5):23-38.
[7] 紀敏,嚴寶玉,李宏瑾.杠桿率結(jié)構(gòu)、水平和金融穩(wěn)定——理論分析框架和中國經(jīng)驗[J]. 金融研究,2017,(2):11-25.
[8] 宋國青.越少越多的貨幣[J]. 財經(jīng),2000,(2):37.
[9] 宋國青.從貨幣產(chǎn)出比與資本產(chǎn)出比看中國的投資與貨幣政策[J]. 中國市場,2013,(19):10-15.
[10] 黎德福,唐雪梅.勞動無限供給下中國的經(jīng)濟波動[J]. 經(jīng)濟學(季刊),2013,(3):823-846.
[11] 胡景北.度量農(nóng)業(yè)勞動力轉(zhuǎn)移:概念選擇和經(jīng)濟學意義[Z]. 同濟大學中德學院經(jīng)濟發(fā)展研究所經(jīng)濟發(fā)展文論,2008,(5):1-30.
[12] M.O.Ravn and H.Uhlig.On Adjusting the HP-filter for the Frequency of Observation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2,84(2):371-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