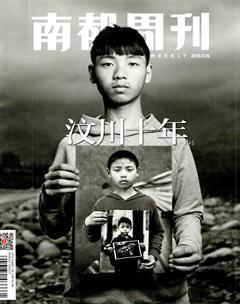是奧數天才的墜落,還是媒體的墮落?
張豐
現在,每個人都可以擁有自己的“媒體”,這讓記者這個職業變得尷尬。對一個記者來說,最尷尬的是你寫了一篇人物故事,卻被當事人打臉。《人物》的實習記者吳呈杰就遭遇到這樣的尷尬。他寫了一篇《奧數天才墜落之后》,結果當事人付云皓站出來說,“我沒有墜落,我正在腳踏實地處。”
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人肯定會站在當事人一邊:你們記者才是墮落啊。(比墜落更可怕)
坦白說,《奧數天才墜落之后》這篇文章,寫得還是很認真的。吳呈杰電話采訪了付云皓,還當面進行了長時間的采訪。除此之外,吳還采訪到了付的老師和同學,在當下的媒體狀況下,至少在態度上,這算是很嚴謹的。
付云皓的人生軌跡,其實非常簡單:他曾兩次獲得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IMO)的滿分金牌,被保送到北京大學數學科學學院。大家(很虛的詞)都期望他將來能從事數學研究,成為杰出的數學家,但是最終付云皓卻沒能從北大畢業,因為物理不及格,補考又不及格,失去了畢業的資格。現在,付云皓在廣東第二師范學院教數學。
從兩屆IMO金牌得主、北大高材生到給小學老師講數學,在吳呈杰看來,這無疑就是墜落了。
《奧數天才墜落之后》這篇文章在最核心的事實并沒有問題:第一,付云皓沒能從北大畢業;第二,他教未來的小學數學老師,不從事數學研究了。
有問題的是對這一事實的解釋。
在吳呈杰和《人物》看來,這樣的狀態就是一種“墜落”。“高處”確實是存在的,兩屆IMO滿分金牌得主,對很多人來說確實是高不可攀的成績。從高處到低處,可不是墜落嗎?
但是在當事人付云皓看來,教小學老師學數學,也是“腳踏實地”。讓未來的小學老師學好數學,影響到更多的孩子,這不是很“正能量”的事嗎?(他確實使用了正能量一詞。)
事實上,《人物》公號上這篇文章后面的網友評論,大多都是一片惋惜。很多人都認為,是奧數競賽和教育體制害了付云皓。對這樣狂熱的數學愛好者,北大當初也許應該設計一套更靈活的培養方案,因為物理不及格(兩次都是差一點點)被迫“肄業”,實在太可惜了。
付云皓的故事傳到《人物》編輯部,基本事實早已清晰,記者要做的,就是去刻畫他的人生軌跡,揭示其內心世界。
問題可能恰恰出在這里:記者已經事先在內心中畫好了墜落的軌跡,所以再選擇事實的時候,不自覺地帶有傾向性,比如付云皓高中嚴重偏科(暗示他不夠健全),大學迷上游戲(暗示他沒能好好學習),這些“事實”讓付云皓感到不快。
《人物》之所以選擇采訪付云皓,就是認定了他“有問題”,認定他的故事,具備某種價值。在記者心中,付云皓就是一個失敗者,他的采訪,就是想展示這個失敗者的傷口,以期給社會—點教訓。
一個兩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滿分金牌獲得者,應該成為數學家。一個北大畢業生,應該有高大上的前程。這就是吳呈杰和《人物》編輯部的價值觀,他們認為這也是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這確實有很大偏差。因為對很多IMO金牌獲得者和家長來說,這塊金牌只不過是保送的通行證而已,可以以此更方便地申請到國外的好大學,實在不行也可以保送到北大、清華。至于大學學什么,能不學數學當然更好。過去30年,中國有很多國際數理化奧賽金牌獲得者,最后成為知名科學家的其實很少。
但是,《人物》的另一個判斷,確實是說到了公眾的心坎上:一個北大畢業生,難道不應該更成功嗎?“北大高材生賣豬肉”之所以能成為新聞,就是因為公眾普遍認為他應該“更體面”才是。
付云皓和公眾的反應,估計讓《人物》的編輯和記者吃了一驚。或許,如今人們已經普遍接受“平平淡淡才是真”了。在當今這個時代,要成為數學家,或者一個“杰出校友”都太難了。大家都是使盡全身力氣,卻仍然過著普通生活而已。
這種反應真的讓人欣慰。我們不再那么勢利地看人了。一個“數學天才”,長大后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他可以教“二本”,可以賣豬肉,可以成為一個流浪歌手。
只要他開心并滿足,都應該受到我們的祝福。這樣看來,《人物》和它的記者,都犯了一個刻舟求劍的錯誤。他們以為公眾還那么狹隘,其實不過是自己狹隘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