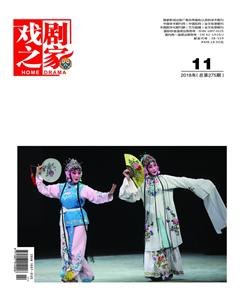清初女詩人、劇作家張蘩考論
郭浩
【摘 要】張蘩是活躍于清代初期的女性詩人和劇作家,其生卒、生平及著述情況在學術界存在爭議。從張蘩交游情況入手,考察其閨友的詩文集內容,確認基本情況。張蘩詩詞清婉俊逸,至性天然,在交游酬唱與家庭生活中展現出自身才華。其劇作《雙叩閽》脫離女性劇作家朦朧自我宣泄,將目光聚焦到更為廣闊社會層面,以女性獨特視角表達對社會的關懷及實事思考。
【關鍵詞】張蘩;生平交游;雙叩閽
中圖分類號:I207.3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8)11-0009-03
一、生平、交游與著述
張蘩,清初女劇作家,詩人,字采于,號衡棲老人,江蘇長洲人。其夫為貢生吳士安,在《吳縣志》中有云:“張蘩,字采于,吳縣人,歸貢生吳士安為室,性耽吟詠,襟懷澹雅。”①
張蘩之卒年不詳,各專著、論述中皆無考,僅在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中記載張蘩的卒年為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②。其生年存在爭議,張蘩在其劇作《雙叩閽》自序中提到于“丙戌秋”應征北上,設帳于王府,“辛卯端午月”完成劇作《雙叩閽》創作。鄧長風據此在《明清戲曲家考略續編》中推測張蘩生年在康熙四十年(1701)前后③,這種說法并不準確。《全清詞·順康卷》中提到張蘩為張循齋妹,吳士安室④。清代錢泳編著《履園叢話·下》中記載:“康熙癸卯,歲大饑,偕弟公遜設粥廠于南翔甫里,日計粟五十石,罄家賑濟。又仿京師舊制,與許香谷、張循齋、張晉侯諸先生設堂玄妙觀,以收棄嬰,各捐田百畝。”⑤由此可知,張循齋于康熙癸卯(1663)左右在蘇州設立育嬰堂并管理其事務,與當地士紳賑災。此時張循齋正值壯年,所以可以判斷張蘩生年不可能在康熙四十年(1701)。張蘩與清初閨閣詩人熊湄交往密切,二人詩作往來頻繁。熊湄在張蘩三十歲生日時送詩三首為其賀壽,其詩名為:“庚戌二月望日壽采于姊三十初度,康熙九年⑥。”由此可知,康熙九年(1670)農歷二月十五日張蘩三十歲,可推測出張蘩的生年月為明朝崇禎十三年(1640)農歷二月十五日。
張蘩才華離不開她良師益友。清初戲曲家尤侗(1618-1704),號西堂老人,為《林下詞選》《眾香詞》兩部女性詞選作序,他對女性文學贊賞和推崇,給予了女性創作極大支持。張蘩的才學得到尤侗肯定與推獎,成為他女弟子。王瓊在《寄呈袁簡齋先生書》中云:“乃閨閣成名,不少親師取友之益,而詩篇不朽,尤仗名公大人之知。若昭華之于西河,采于之于西堂,映玉之于松崖,芳佩之于堇浦,莫不籍青云而后顯,附驥尾而益彰也”。說明張蘩曾受教于尤侗,她在閨秀中為人所知,除了自身擁有的才學之外,與授業名師也是緊密相連。尤侗與王士祿相交,在《林下詞選》序中說道:“吾友新城王西樵,嘗輯《燃脂集》,匯羅大備,卷軸汗漫,迄未成書。”王士祿在編著《燃脂集》時,尤侗向他推薦了張蘩詞作,足以見得尤侗對張蘩肯定。張蘩寫下[燭影搖紅]《尤悔庵太史索新詞刻〈燃脂集〉中辭謝》表達了她對尤侗曾施與恩惠感謝,并且婉言謝絕了索要新詞請求。此外胡孝思編著《本朝名媛詩鈔》中記錄了尤侗對張蘩所寫詩詞評價,在《高陽閨秀遠惠采花乞畫賦此致謝》中,尤悔庵評:林下之風,閨房之秀,可謂兼之矣嘆絕;在《初夏喜大人到舍》中,尤悔庵評:情景俱真。可見尤侗對張蘩才華賞識及推舉。
張蘩生活在才女文化繁盛江南地區,張蘩與清代長洲許氏家族有著密切交往和聯系,張蘩與許氏家族交流呈現出才人家族性特點。周銘編著《林下詞選》中說道:“元方性癖書,博雅明通。一門風雅,咸出淵源。”許元方家中多才女,所以稱“一門風雅”,許元方妻子顧道喜,字靜菴,工詞,著有《松影菴詞》。許元方與顧道喜的兒子許虬為順治十五年(1658)進士,育有四女,長女許心榛,字山友,一字阿秦,長洲人,孝廉陸升枚室。張蘩為許心榛的舅母,并且與其稱為閨中詩友,在日常生活中相互酬唱,談詩論詞。
張蘩在文學創作上充分展示著自身才能,在詩詞和戲曲方面均有所涉獵,《蘇州戲曲志》中記載張蘩著有詞集《衡棲集》,但今未見。據筆者搜集整理到張蘩現存的詩詞一共20首,收錄在《本朝名媛詩鈔》《閨秀詩鈔》《國朝閨秀正始集》等箸作中。張蘩著有傳奇《雙叩閽》,全劇分上下兩卷,共25折,尾折《恩旌》殘缺,另外多出第十六折《改裝》和第十七折《投江》殘頁。該劇本現存版本為清寧府鈔本,留存在程硯秋玉霜簃戲曲抄本之中。除《雙叩閽》外,姚燮的《今樂考證》中記載了署名為衡棲老人所作《才星現》、衡棲老婦所作《醒蒲團》,《笠閣批評舊戲目》中也記載了署名為衡棲老婦所作《醒蒲團》,可見這兩部劇作可能是張蘩晚年創作。
二、詩詞創作
從張蘩的詩詞可以讀出她融入其中的細膩情感,她的詩主要以與尤侗交流、閨閣姊妹之間贈答、家庭生活描寫為主。其詩形式多樣,清婉俊逸,至性天然。周銘在其編著《林下詞選》中云:“其詞品似吳淑姬一流,當與陽春白雪并傳。”⑦可見周銘對張蘩詞極其賞識,認為她的詩詞能與宋代著名的女詞人吳淑姬相比。
張蘩注重生活情趣,區別于較多的男女相思相愛的題材,張蘩用數首詩詞描繪自己家庭生活,《戲為外子撥悶》中就體現了家庭生活中的真情流露:“失意休教苦自煎,為君把卷論前賢。兒頑自笑同王霸,婢鈍何須學鄭玄。滌器當壚情更洽,操舂舉案志猶堅。久藏賴有床頭醞,莫負梧桐月正圓。”⑧“外子”吳士安在官場失意,教育子女十分嚴厲,陷入“苦自煎”處境。張蘩用聊天方式品評先賢,希望丈夫不要過分要求自己,對待子女的教育應根據其資質決定。轉而說到家庭關系中最重要是夫妻間情投意合,拿出備好美酒夫妻二人對月共酌。詩中運用了大量歷史人物和典故,將典故化入構思,脫離單純抽象說理,使其詩意和諧自然,頗見張蘩學識。尤侗評價《戲為外子撥悶》云:“相如貰酒為文君撥悶,今反得此佳偶,難長貧賤足矣。”⑨
關于家庭與親人的詩詞還有與兄長張循齋相逢寫下的《擬古三十韻呈大兄》與在父親到訪而作《初夏喜大人到舍》,其中云:“屏跡多年與世違,偶貪花信到柴扉。典衣不惜沽春釀,掃石何妨待月輝。芍藥斂妝紅欲瘦,芰荷出水碧初肥。相看莫使花枝笑,沉醉休辭酒力微。”⑩
“欲”“初”二字體現了張蘩體物入微表現力,從表達父親不愿在世俗中浮沉的孤高品性到相聚時把酒言歡,最后希望父親盡享受天倫之樂。以景寄情,情景俱真。清初詩人沈德潛評價張蘩詩詞:“采于詩溫柔敦厚,得風人之旨。余尤愛其《初夏》一首,至性天然。”?
張蘩常與友人熊湄題贈唱和,留下許多酬唱贈答之作。張蘩的詩詞中有數首寫到與熊湄交往,表達自己對熊湄思念,體現二人深厚情誼。如這首《江城子·久雨憶滌菴姊》:“湘簾不卷雨濛濛。鏡臺封,曉粧慵。春山休染,一任淡眉峰。脈脈離情未曾慣,百里外,有人同。盈盈一水隔難通。思無窮,憶相逢。記得臨歧,
攜手話匆匆。欲倩春潮和淚點,流取去,到吳淞。?”久雨不晴的天氣使張蘩無心梳妝,還未習慣與熊湄離別,回憶起分別時場景,志同道合的二人此刻內心定是感同身受,濃濃的思念之情在雨水中蔓延開來。
張蘩還為熊湄的詩集《碧滄道人集》作序,序中云:“高者如孤云離岫,素鶴凌空;麗者如春葩競秀,秋月呈輝;遠者如叔度千頃,汪洋莫測;逸者如穆王八駿,馳聘無窮。雖變化百端,縱橫萬狀,莫不緣情隨事,因物賦形,而亦本性情,乞得以香奩小技目之??”
張蘩在序中對女性詩歌創作追求進行了論述,圍繞高、麗、遠、逸四個方面進行分析。指出女性在進行詩歌創作時應以性情為根本,以事為目,達到“緣情隨事,因物賦形”的詩歌才是最理想境界。
三、戲曲創作
《雙叩閽》是張蘩唯一一部留存劇作,周妙中認為張蘩是“清代有作品流傳的第一位女作家。”?《蘇州戲曲志》中記載張蘩活動于乾隆年間,著有傳奇《雙叩閽》。其中:“丙戌(乾隆三十一年)應征北上,設帳王府。”?周妙中也認為此處丙戌年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筆者認為皆有誤。《履園叢話》中記載張蘩的兄長張循齋于康熙癸卯(1663)年發生饑荒時與當地仕紳賑災,說明其兄長活動在康熙時期。?張蘩為尤侗的女弟子,尤侗向王士祿(1626-1673)推薦張蘩的詞作,刻錄在《燃脂集》中,張蘩作[燭影搖紅]《尤悔庵太史索新詞刻〈燃脂集〉中辭謝》。除了二人在詞之間交流,尤侗還為張蘩的詞作進行了評述,并且為《衡棲集》題詞,尤侗卒年在康熙四十三(1704)年,說明二人間交流在康熙年間。張蘩閨友熊湄為其三十歲生日賀壽作詩三首名為“庚戌二月望日壽采于姊三十初度,康熙九年。”?以上的資料可以得知,張蘩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應征北上,康熙五十年辛卯端午月(1711年5月)于錦帆涇書館題寫《雙叩閽》自序。“錦帆涇”在《吳邑志·長洲縣志》中有記載:錦帆涇,即城里沿城濠也。相傳吳王錦帆以游”?。可見張蘩在康熙五十年(1711)已回到長洲,《雙叩閽》創作時間介于1706-1711年之間。
《雙叩閽》的劇情極為曲折,劇演明朝武進士馬大騏為官清廉,升任四川成都府兵備兼知州事。任途中恰遇當地發生嚴重災荒,馬大騏重建大悲禪院,收容并救濟饑民。河道總管皇甫謙欲侵吞國帑,見馬大騏救濟災民,認為有利可圖,于是任馬大騏協助監督河工。馬大騏知曉此事后果斷拒絕,皇甫謙惱羞成怒,上疏誣告馬大騏修理河道時貪污帑銀,并串通官吏誣陷使其入獄。馬大騏聽聞皇帝南巡,于是設法越獄,攔下圣駕叩閽。皇帝得知真相后讓其回任待命,不料皇甫謙串通河官,又使其身陷囹圄。馬大騏的妻子汪氏知曉后,毅然獨自赴京,作血疏上奏叩閽,為馬大騏鳴冤。皇帝見其血疏,下圣旨徹查此案。皇甫謙被沒收家財,流放路途中被老虎咬死。馬大騏官任原職,操軍滅寇,兒子馬龍駒參加科舉高中進士,最終家人團聚,一門顯榮。
張蘩在《雙叩閽》自序中提到:“今春有姻親授余以馮氏伉儷叩閽情節,大聳耳目,屬余為劇以志之”,可見《雙叩閽》的故事來來源于當時發生的社會事件,但是為了避免招致無端的禍害,張蘩“稍避嫌于涉世”,采取了“易其朝代,更其姓氏”方式創作。
張蘩在其劇作《雙叩閽》中流露出滿腔社會責任感,字里行間中透露著對公平正義追求。身為蘇州人的張蘩活動于明末清初,正因如此,張蘩受到了蘇州派作家借以歷史人物表達個人情感影響。在其劇作《雙叩閽》中,除了馬大騏、皇甫謙二人忠奸斗爭外,還在實事中大力弘揚現實精神。張蘩在《雙叩閽》自序中就已明確表明了自己創作意圖。她通過戲曲來記錄社會實事,希望用戲曲這一藝術形式所表現出的感染力感化受眾,達到鋤奸護忠目的。
經歷前人不斷探索與嘗試,清初出現了以關注現實為特點蘇州派,但鮮有女性劇作家涉及時事劇。《雙叩閽》飽含著張蘩的對社會實事觀察與思考,反映了清初因治河而產生的忠奸斗爭,塑造了皇甫謙與馬大騏、汪氏等生動人物形象。張蘩并未簡單遵循歷史,而是對戲曲實事題材中的虛實關系有著自己真知灼見,用“戲者戲而已矣”來闡述戲曲文學本質。區別于男性劇作家所創作時事劇,《雙叩閽》在描寫忠奸斗爭的場面外還蘊涵著抒情一面,這是張蘩作為女性劇作家融入了自己情感生活和對理想家庭描繪。《雙叩閽》顯然已不再屬于女性劇作家朦朧自我宣泄,而是將目光聚焦到更為廣闊社會層面,以女性的獨特視角表達對實事看法和思考。《雙叩閽》出現豐富了女性戲曲作品內容與風格,具有鮮明時代特征,側面見證了女性戲曲作品中主體意識發展軌跡。
注釋:
①李根源.吳縣志[M].蘇州:蘇州文新公司,1933:33.
②http://www.zggds.pku.edu.cn/006/cbdb/CBDB.htm.
③鄧長風.明清戲曲家考略續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13.
④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全清詞·順康卷[M].北京:中華書局, 2002:7291.
⑤(清)錢泳撰,孟裴校點.履園叢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01.
⑥(清)熊湄.映閣詩草:一卷[M].清朱絲欄抄本.
⑦(清)周銘.林下詞選[M].濟南:齊魯書社.
⑧(清)清惲珠.國朝閨秀正始集[M].紅香館刻本.1831.
⑨(清)胡孝思.本朝名媛詩鈔[M].凌云閣刻本.1716.
⑩王延梯.中國古代女作家集[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676.
?徐世昌,聞石點校.晚清簃詩匯[M].北京:中華書局,1990:8189.
?(清)胡孝思.本朝名媛詩鈔[M].凌云閣刻本.1716.
?王英志.清代閨秀詩話叢刊[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538.
?周妙中.清代戲曲史[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273-274.
?蘇州市文化局,蘇州戲曲志編輯委員會.蘇州戲曲志.[M].蘇州:古吳軒出版社, 1998:477.
?(清)錢泳,孟裴校點.履園叢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01.
?(清)熊湄.映閣詩草:一卷[M].清朱絲欄抄本.
?(明)楊循吉,陳其弟點校.吳邑志.長洲縣志[M].揚州:廣陵書社, 200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