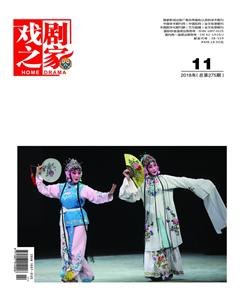近三年(2015—2017)明代文學研究綜述
吉曉凡
【摘 要】2015年至2017年,是明代文學研究蓬勃發展的三年,學界在相關領域取得了比較突出的成就,研究視角更新穎,研究材料更豐富,整體研究趨于多樣化與精細化。筆者對這三年明代文學的研究成果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整理與總結,分別從詩文研究、戲曲研究、小說研究和民歌研究等四個方面對研究成果進行了分類和說明,并提出了對明代文學未來研究之展望,以期為研究者們提供一些參考。
【關鍵詞】明代;詩文;戲曲;小說;民歌;綜述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8)11-0213-03
一、詩文研究
戲曲、小說等通俗文學的崛起使詩文的正統地位受到動搖,但數量并沒有減少。作家們自成一派,出現了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文人團體。據統計,近三年(2015-2017)來,研究明代詩文的論文約27篇。在這些論文中,研究詩人的居多,有王世貞、楊慎、趙貞吉等。有的研究者指出,王世貞作為后七子的領袖人物,通過模擬學習樂府詩,進行深刻思考,并對樂府詩進行創新,創作出獨樹一幟的“明樂府”,認為“王世貞的樂府詩思想有其獨到之處,他不拘泥于模擬求得的逼真和形似之作,而是注重在把握樂府曲調和法度的基礎上,融入自身感情,將創作與社會實際相結合,新事附古調,甚至是為了回歸到樂府詩原創時的‘田畯女紅之響,讓曲調和法度服從于真性情的表達,并通過樂府變的創作達到新創,從而尋找到一條適合‘明樂府創作的道路。”[1]
潘鏈鈺則在《明代經學與經學關系之初探》中總結了明代經學與詩學的關系。首先,明初宋濂認為詩文一家,但是明代主流詩學派認為詩文有異,是由各自情思特征決定的。經學轉型而成的心性之學與詩學體系相得益彰,深刻影響了詩學的發展軌跡。其次,在明王朝排除異端思想的政治環境下,詩人們提出“格調論”,學習古人之性情,創作出符合古典美學特征的詩歌。心學提倡致良知,他們希望在詩歌創作的過程中發現自我、展現自我、提升自我。第三,明朝之前,已然有唐詩和宋詩兩座高峰,明朝文士開始思考宗唐還是宗宋。尊崇唐詩的,被盛唐時期繁榮的詩學氣象折服,而宗宋之人更為注重發揮自身的主體性,尤其是個人心性的抒發,與心性之學不謀而合。無論是宗唐或宗宋,都體現了經學與詩學的能動互動。第四,明代出現的八股文作為一種文體,納入經學考試范圍,詩學與經學水乳交融。
明代是小品文創作的旺盛期,李超闡釋了李贄的“童心說”與晚明小品文的關聯性,她認為,李贄的哲學理論深刻影響了小品文的創作面貌。李贄的“童心”指的是“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就是說,進行文學活動要聽從本心和己意。“對于明中葉后小品文的發展提供了思想上的建構,他的相關論述,始終閃爍著生動犀利的精光,它猶如不滅的焰火,一直燃燒到民初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他的關于文學創作的論述,千古不磨,在今天依然有相當的借鑒意義。”[2]
臺閣文學出現于明朝永樂至成化年間,張仲謀總結出臺閣體詞的題材大致可分為三類,即述恩禮、紀祥瑞和詠節慶。臺閣詞人偏愛喜慶的詞調名,例如《滿庭芳》《清平樂》《應天長》等。他認為臺閣體詞的功能大多體現為歌頌盛世,“無論是寫節氣風光,還是紀宴游場面,往往以大部分篇幅描寫百辟咸沾恩澤、處處歡聲笑語的場面,而結尾處則歸于對皇上或王朝的美好祝愿。”[3]由此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雍容典雅的藝術風格。
二、戲曲研究
相較于詩文的后發之勢,明代戲曲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重點。近三年相關論文約計108篇。這些論文中,有以地域分布為根據研究明代戲劇文化的,如陳志勇的《明代湖北地區戲劇文化史料考釋》、賈三強的《明代陜西戲曲創作與表演述論》、錢曉紅的《運斤成風游刃余地——明代安徽戲曲題材探析》等。有將戲曲與宗元觀念結合認知的,所謂“宗元”,就是將元曲奉為圭臬。張小芳《宗元觀念與明代戲曲理論之建構》認為,明代曲壇的批評思潮與詩文復古風氣相通,前有“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文學論,后有李開先提出的戲曲應“以金、元為準”。明朝戲曲中的宗元觀念一方面體現在元曲上升為元代的象征性代表,在中國文學史上獲得了穩定的席位;另一方面,元曲的典型化和象征化,使其成為明代戲曲理論及戲劇創作的借鑒典范。以宗元為號召,總結及論證元代戲劇的創作思想,成為明代曲論家進行戲曲創作的衡量標桿,兩者的關系長久而深刻。
元劇接受史的構建可基于明代戲曲批評史基礎上,相反,明代戲劇理論的構建歷程也可基于元劇接受史基礎之上。劉建欣論述了戲曲選本與宗元觀念的聯系,她提出明人在進行戲曲選本時,將元雜劇中晦澀難懂之處進行了修正,使其受到廣泛的認可和接受。在元曲評論體系中,編選人將觀念和思想直接通過序跋和評點的方式體現,有利于確認和強化元曲的地位。這些觀點通過戲曲選本傳播到大眾中去,“宗元”思想得到廣泛普及。“明清戲曲創作基于宗元觀念的最大價值體現并非是元曲的收錄及傳播,元的建構及文本傳播過程中具有的潛在思想,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價值所在,而前者的收錄及傳播僅是最為基本的宗元的應用。”[4]
還有研究明代戲曲的美學精神的,祁志祥認為,明代戲曲美學論爭主要有三種,分別為本色論、情趣論、折中論的論爭,他詳細論述了上述論爭的美學思想。所謂本色論,一方面是指用淺顯易懂的語言進行創作;另一方面也指要按合律、入樂的要求作曲。
情趣論主要為湯顯祖提出,他提出戲曲創作應追求“至情”“意趣”“真色”,提倡寫虛幻之境。為此他與本色派代表沈璟發生過一場爭論,也就是著名的“湯沈之爭”。沈璟撰寫的《南詞全譜》,為文人作曲家在寫劇時提供了一個參考和遵守的標準。湯顯祖的《牡丹亭》引起巨大反響后,沈璟發現其內容完全不講究曲律,于是對不合曲律之處進行修訂改刪,湯顯祖對此不以為然。他們的言論之爭引起一片嘩然。黃仕忠在《凡文以意趣神色為主——再談“湯沈之爭”的戲曲史意義》中研究湯顯祖的戲劇時發現大多數戲劇家對于戲曲,僅是將其視作一項表達個人情感的娛樂方式。湯顯祖則是全身心投入到戲曲創作中,將傳奇作為個人情感抒發的新體裁,并一直秉承以情抗理的原則,他十分重視創作之“情”。
折中論代表有王世貞、屠隆、王驥德等。他們各抒己見,從王世貞開明代戲曲折中派的先聲,既肯定情趣論,又不反對本色論,到王驥德主張“大雅與當行參間”,最終奠定明代曲學的折中論。
除此以外,明代戲曲作為一種社會藝術形態,其教化功能也不容忽視。于凱認為,戲曲的教化功能具有兩重性。首先,在教化劇目的評價上,出現了文人反對的聲音。例如《伍倫全備》,王世貞和徐復祚認為其“不免腐爛”和“令人作嘔”。其次,戲曲的出現和興起并沒有受到嚴格查禁,“對于統治者而言,禁毀既是權力的彰顯之處,又是有意忽略的盲點所在;對于被統治者而言,違禁既是反抗的試探表露,又是其主動尋求的消解出口。”[5]到了明代晚期,隨著心學的傳播和商品經濟的繁榮發展,文人開始注重戲曲本身的藝術審美特征,并逐漸淡化社會教化功能。這一時期,戲曲發展繁榮,文人鐘情于戲曲創作,浪漫主義文藝思潮也從此得到發展。隨著晚明李贄“童心說”的提出,“文以自娛”之說得到了豐富和發展,戲曲理論達到質的飛躍。從此,古典戲曲在晚明時期發生了極大變化,戲曲的創作不再局限于高雅藝術,通俗文學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
在明清劇壇上,《鳴鳳記》歷來被視為時事劇的“開山之作”,但呂靖波對此表示質疑。他認為,要進一步探討這個命題,首先要確定“時事劇”的概念。目前學術界對這一概念持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時事”是發生在民間的新聞;另一種觀點認為,“時事劇”是反映政治事件的作品。呂靖波認同第二種觀點,且認為一部“時事劇”所具備的要素主要包含下述幾點。
第一,劇本應該具有鮮明的政治性,“此處所指的政治性與作家的政治觀點并無多大關系,但不失為一種政治道德立場的強烈宣示,只不過它很難超越‘忠孝節義的話語范圍。換言之,幾乎所有的明清時事劇都只是披著‘時事外衣的忠奸劇。”[6]第二,由于特殊的題材,“時事劇”應具有一定的真實可靠性。第三,劇作家創造的角色應為時事人物。
如何界定“時事”的時效性,目前出現了十年二十年的說法,但都缺乏充分依據。總的來說,要想透徹研究“時事劇”,應當搜集更廣泛的資料,進行更深刻的研討。
三、小說研究
小說在宋元說話藝術的基礎上發展到明代,呈現了一個空前繁榮的局面。這一時期,出現了《三國演義》等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影響深遠。據筆者統計,2015年至2017年,相關論文約187篇。
明代城市經濟發展繁榮,市民隊伍不斷壯大,社會風氣逐漸娛樂化,給通俗小說的生產與消費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明代通俗小說是在明代社會文化通俗化、民間化的潮流中,被書商和下層文人當作一種向民間社會普及各種文化知識的通俗讀物來生產的。它所構建、傳遞的文化知識主要包括歷史知識、宗教知識、法律知識、商業知識、倫理知識、時事知識等。”[7]歷史演義小說根據民間講史活動,再輔助史書編寫而成,目的是給大眾普及歷史知識;神魔小說則是三教合一思潮的成果,也是當時明朝宗教世俗化的體現;公案小說是針對民間對法律知識的需求出現的,是宣傳法律文化的產物。
明朝中期,倭寇橫行沿海,武裝走私,搶掠燒殺,成為日漸熾盛的禍患。在此背景下,出現了以抗倭為題材的文學作品,正面描寫和反映抗倭戰爭。這些作者有感于倭寇之亂,希望借助這類小說激發人民的抗爭斗志。萬晴川認為,抗倭小說的主題是揭露倭寇暴行,謳歌抗倭英雄,如戚繼光、胡宗憲等。“抗倭小說是明代的一件重大歷史事件,促使明代小說家關注現實問題,創作思想、審美趣味都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使得前期風行一時的歷史演義、神魔小說開始讓位于描寫當代事件的小說。”[8]
到了中后期,憑借小說素材的豐富積累以及發達的印刷技術,文壇上興盛起以內容的荒誕性和虛幻性為主要特征的志怪小說的匯編熱潮。劉天振研究了匯編者的動機和手段,他認為,隨著西方傳教士的到來,士人將鬼神作為對未知世界的探索,激發人們對自然世界的研究意識。除此之外,宗教界一直利用善惡果報、天人感應等觀念作為弘教方式,宗教意識與志怪小說有著說不清、道不明的密切關系。志怪小說還是文人抒發怨憤之情的載體,他們借助人鬼神故事來哀憤人生境遇和批判社會現實,以達到消遣娛樂的目的。
進入晚明以后,人們越來越關注社會現實,時事政治題材的作品不斷涌現。劉鶴巖總結出時事政治小說最顯著的特征是紀實性,這是由于許多文人用自己親身經歷的或耳聞目睹的事件當作寫作題材。“也正因為是當代時事,知情者甚多,許多當事人還在,作者無法虛構。一旦摻入過多的虛構內容,勢必引起當事人的反駁和讀者的質疑,會大大降低其影響力。”[9]
另有專門研究小說中有關清明敘事的,如陳鵬程的《明清小說中的清明描寫和敘事》;有研究王陽明及泰州學派促成的儒學平民化思潮與明代小說關系的,如陳才訓的《儒學平民化與明代通俗小說》;有論述明朝小說在江南地區發展進程的,如馮保善《明清通俗小說江南傳播及其經典化進程》《江南大眾娛樂文化與明清通俗小說的崛起——兼論明代通俗小說史“近兩百年空白”一說》。由此看來,目前明代小說研究已經取得了豐富的成果,除了學者們的不懈努力,還有小說自身發展規律所致。
四、民歌研究
民歌是一種運用通俗易懂的市井化語言,直接干脆表達感情的藝術形式,曾被贊譽為“我明一絕”,可見其歷史地位及影響。但是近三年,研究明代民歌的論文甚少,僅有7篇。周玉波比較系統地論述了明代民歌產生的原因及背景,他說明代民歌的興盛,一方面得益于李東陽、李夢陽和袁宏道等在民間具有影響力的文人對民歌的肯定與提倡,豐富了民歌的創作內容,擴大了社會影響力;另一方面,“典型者如‘異端思想與民歌的相互發明,此外社會風氣如消費潮流的變化也為民歌生長提供了適宜的土壤,直接促進了民歌的發展壯大。”[10]民歌自身能夠適應明朝社會的發展,成為它在民間經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徐文翔注意到了明代小說中增加的民歌元素,他認為,民歌之所以引用到白話小說中,與明代的文化背景有極其密切的關系。首先受到審美世俗化的影響,文學創作也朝著世俗化方向發展。白話小說作為通俗文學的一部分,時興民歌在作品中大展拳腳也是必然之事。其次是明代文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當代認同感,即使文壇興起復古潮流,文人們的當代意識也是極為濃厚的。他以《金瓶梅詞話》和“三言二拍”為例,闡述了明代民歌在小說創作中的作用。一方面,民歌能夠增加故事的真實感,虛構的情節讓讀者感覺仿佛發生在自己周圍,增強了吸引力。另一方面,民歌多被運用于話本小說“正話”中,更善于刻畫人物的內心活動。如《喻世明言》第十二卷柳永所作的《吳歌》:“肚里一團清趣,外頭包裹重重。有人吃著滋味,一時劈破難容。只圖口甜,那得知我心里苦?開花結子一場空。”這里的民歌雖然是明代的,卻能夠很好地表現柳永內心的困苦,即才華橫溢沒有伯樂發掘,只能到青樓去尋覓知音。
本文對近三年明代詩文、戲曲、小說和民歌進行了梳理,筆者認為,將來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一步研究明代文學。
其一,明代詩人各成一派,提出了許多理論主張,但是這些理論主觀性較強,缺乏一定的辯證性,而且沒有解決如何提高詩歌創作水平,反而讓詩文走向衰微,數量眾多卻缺乏傳世之作,歷來學者并沒有詳細分析和總結這種現象的成因。
其二,明代是戲曲發展的鼎盛期,學者通常對著名戲曲理論家(如何良俊、呂天成、李漁)給予更多的關注,但是相關研究往往有因襲之嫌。相比較而言,對其他地位不夠高、影響力不夠大的戲劇評論家缺乏深入研究。
其三,學界沒有足夠重視研究小說創作與小說批評之間的關系,這是有待于補充的一個方面。
其四,明代民歌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絕”,近三年相關研究成果卻較少,這是明代文學研究應予加強關注的一個領域。
參考文獻:
[1]賈飛.論王世貞的樂府詩及其“樂府變”的歷史地位[J].江蘇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43(2):58-63.
[2]李超.李贄的文學觀念與晚明小品文的勃興[J]. 江蘇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43(2):53-57.
[3]張仲謀.論明詞中的臺閣體[J]. 江蘇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42(2):55-65.
[4]劉建欣.明清戲曲選本與“宗元”觀念的建構[J].求是學刊,2017,44(2).
[5]于凱.明代戲曲——中國古代教化史上的變革性載體[J].學習與探索,2017,(3):159-166.
[6]呂靖波.《鳴鳳記》創作年代與“時事劇”之義界[J].江蘇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2):54-57.
[7]紀德君.明代通俗小說對民間知識體系的建構及影響[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7,(3):119-127.
[8]萬晴川.明清“抗倭小說”形態的多樣呈現及其小說史意義[J].文學評論,2015,(6):203-210.
[9]劉鶴巖.論晚明時事政治小說的紀實性及其形成原因[J].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5,(1):105-109.
[10]周玉波.明代民歌興起的動因與背景[J].江蘇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42(3):4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