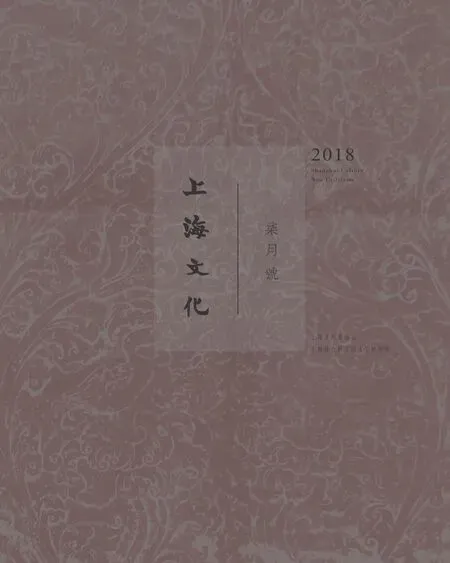魯迅的“博物學(xué)”愛好與切實寬博的精神
涂 昕
1 “說說較為切己的私事”
周氏兄弟自童年時期就表現(xiàn)出對“異端思想資源”的興趣。周作人在《魯迅的青年時代》中說其兄從小“對于‘正宗’的詩文總之都無什么興味,因此可以說他走的乃是‘旁門’”,“在喜歡六朝文,喜歡陶詩,喜歡各種雜著,而不看重李杜蘇黃等正宗大家,尤其看不起唐宋文這幾點上,周作人是和魯迅完全一致的,都是不走‘正宗’而走‘旁門’的路子。周作人顯然是從自幼讀書時,就從魯迅那里受到這種根本方向性的影響。”而兩兄弟的“旁門”興趣中,“博物學(xué)”方面的內(nèi)容占了相當(dāng)大的比重——在《阿長與〈山海經(jīng)〉》一文中,魯迅寫到好幾種自己少年時代渴慕、喜愛、后來多方搜集的圖書,比如《山海經(jīng)》、《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花鏡》、《爾雅音圖》、《毛詩品物圖考》等,都是“博物學(xué)”方面的著作——這種始自童年的共同興趣對他們后來的文學(xué)和思想有一些頗為深刻的影響。
魯迅很少直接解釋自己喜愛“博物學(xué)”的原因,好在周作人幾次三番在文中談及自己對草木蟲魚的熱愛,既然這是兩兄弟在同樣的生長環(huán)境中產(chǎn)生的共同興趣,且后者自幼讀書就受到其兄的影響,那我們不妨先看看周作人怎么說,來幫助我們理解魯迅的“博物學(xué)”愛好。
魯迅很少直接解釋自己喜愛“博物學(xué)”的原因,好在周作人幾次三番在文中談及自己對草木蟲魚的熱愛
周作人談自己的雜學(xué)時說,“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如嚴(yán)幾道古雅的譯語所云‘化中人位’,我們也是很想知道的,那么這條路略一拐彎便又一直引到進(jìn)化論與生物學(xué)那邊去了”。“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經(jīng)典,可以千百年來當(dāng)人類的教訓(xùn)的,只有記載生物的生活現(xiàn)象的比阿洛支,才可供我們參考,定人類行為的標(biāo)準(zhǔn)。這也可以翻過來說,經(jīng)典之可以作教訓(xùn)者,因其合于物理人情,即是由生物學(xué)通過之人生哲學(xué),故可貴也。”但同時他又說,其實對于這一方面的愛好,“說起來原因很遠(yuǎn),并非單純的為了化中人位的問題而引起的”,他說自己“所喜歡的舊書中有一部分是關(guān)于自然名物的”,并開列了長串中國傳統(tǒng)“博物學(xué)”方面的書籍,表明自己從小就愛好這些東西且“始終未變”——“因為最初有這種興趣,后來所以牽連開去,應(yīng)用在思想問題上面,否則即使為得要了解化中人位,生物學(xué)知識很是重要,卻也覺得麻煩,懶得去動手了吧”。
魯迅對一個人的思想言行是否“出于自己真實的內(nèi)心”一直非常看重
魯迅當(dāng)年讀到嚴(yán)復(fù)翻譯的《天演論》深感震動,繼而去搜求各種進(jìn)化學(xué)說,還將自己的部分閱讀所得編譯成論文《人之歷史》,介紹德國生物學(xué)家恩斯特·海克爾的種系發(fā)生學(xué),此學(xué)說是對達(dá)爾文生物進(jìn)化論的有力支持和補(bǔ)充。在這篇論文中反復(fù)提及的,就是各種生物都有一個共同的起源、都處在因果關(guān)系的鏈條當(dāng)中,而人作為生物之一種,也就與其他生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所以才有嚴(yán)復(fù)翻譯的所謂“化中人位”,這來自赫胥黎的一本書名,現(xiàn)在譯為《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后來魯迅購買大量生物學(xué)方面的專業(yè)著作(以植物學(xué)、動物學(xué)居多,也涉及古生物和微生物),也跟周作人一樣,是試圖去理解“化中人位”、由生物學(xué)通向人生諸問題這方面的原因吧。
然而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周作人強(qiáng)調(diào)自己這方面的興趣早在接觸西方進(jìn)化論和生物學(xué)之前就有了,并非單純?yōu)榱恕盎腥宋弧倍穑匾氖鞘甲酝甑摹⑻烊坏呐d趣與愛好。周作人的說法提示我們,同樣地,盡管我們可以為魯迅對“博物學(xué)”的關(guān)注找出各種各樣的理由,但最簡單也最根柢的,就是這原本就是出自天性的喜愛,并沒有——或者說最首要的并非來自——多么深奧的道理和明確的目的。
然而恰恰因為這出自天性,才顯得特別有意思。
在早年論文《破惡聲論》里,魯迅稱那些僅僅依據(jù)外來的時髦理論或一己私利而盲目指斥迷信的人為“偽士”、“澆季士夫”,批評他們“精神窒塞,唯膚薄之功利是尚,軀殼雖存,靈覺且失”,“昧人生有趣神軼之事,天物羅列,不關(guān)其心,自惟為稻粱折腰”,進(jìn)而呼吁“偽士當(dāng)去,迷信可存”。日本學(xué)者伊藤虎丸先生曾仔細(xì)解釋過魯迅所謂的“偽士”:“(1)其議論基于科學(xué)、進(jìn)化論等新的思想,是正確的;(2)但其精神態(tài)度卻如‘萬喙同鳴’,不是出于自己真實的內(nèi)心,唯順大勢而發(fā)聲;(3)同時,是如‘掩諸色以晦暗’,企圖扼殺他人的自我、個性的‘無信仰的知識人’。也就是,‘偽士’之所以‘偽’,是其所言正確(且新穎),但其正確性其實依據(jù)于多數(shù)或外來權(quán)威而非依據(jù)自己或民族的內(nèi)心。”
魯迅說與其聽這些“偽士”吹噓如何“善國善天下”,“則吾愿先聞其白心”。這里所說的“白心”,可以有兩種理解,一種是偏正結(jié)構(gòu),“純白無垢之心”;一種是動賓結(jié)構(gòu),“自白其心”,也就是坦露“自己真實的內(nèi)心”之意。魯迅對一個人的思想言行是否“出于自己真實的內(nèi)心”一直非常看重,文中類似的表述還有很多,比如“吾未絕大冀于方來,則思聆知者之心聲而相觀其內(nèi)曜”、“內(nèi)曜者,破黮暗者也;心聲者,離偽詐者也”“蓋惟聲發(fā)自心,朕歸于我,而人始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覺近矣”等。“聞其白心”、“內(nèi)曜”、“心聲”,強(qiáng)調(diào)的都是發(fā)出個人內(nèi)心最真實的聲音。
這層意思,他后來的文字中也多有流露。《墳·雜憶》中說:“報復(fù),誰來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執(zhí)行”;《華蓋集續(xù)編·記“發(fā)薪”》又有,“我現(xiàn)在只能說說較為切己的私事,至于冠冕堂皇如所謂‘公理’之類,就讓公理專家去消遣罷”;他給鄭振鐸的信中談及《北平箋譜》的印造,要對方不必事事跟他商量、自己定奪就是,“我是獨裁主義信徒也”——我們當(dāng)然不能僵化地按照字面來理解魯迅這些話,看似劍走偏鋒的背后,強(qiáng)調(diào)的是對事物的理解判斷不假外求,而要依據(jù)自我內(nèi)部最深切處。
上述態(tài)度是魯迅思想中非常核心的一部分,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再來回頭看魯迅對“博物學(xué)”這份自幼而生的興趣。正因其出自天性,才最能反映一個人的“心聲”、“內(nèi)曜”;而滋養(yǎng)培育自己天性中的愛好,也就是呵護(hù)一己的那顆“白心”。在“惟膚薄之功利是尚”的人眼中看來,花花草草、鳥獸蟲魚,似乎是沒有什么用處和意義的,然而在魯迅的價值體系里,還有什么是比“心聲”、“內(nèi)曜”、“白心”更要緊的呢?
已經(jīng)有一些研究者專門探討過魯迅筆下涉及的各種動物,比如作為自我形象投射的“狼”、“蛇”、“大象”,諂媚勢利之典型的“叭兒狗”,順從麻木、不敢反抗的“羊群”等——這些動物,是作為一種意象,在文本中承擔(dān)著一定的隱喻功能。而我想說的是另一種情況:有時候魯迅在他的文字里提及一些動植物,它們并不帶有明確的隱喻功能或者其它很刻意的目的,只是出于偏愛或者熟悉,就寫了下來而已。
“微言”未必有“大義”,但因其關(guān)聯(lián)著個人的情感記憶,自有一份價值和意義
魯迅每到一處都會特別留意到身邊的花草樹木,這些東西入眼入心,信手寫進(jìn)自己文章里,“微言”未必有“大義”,但因其關(guān)聯(lián)著個人的情感記憶,自有一份價值和意義。魯迅初到北京時,住在紹興會館藤花館西屋,后來又遷入西院的補(bǔ)樹書屋。藤花館自是有紫藤,補(bǔ)樹書屋的院子里則有一棵高不可攀的槐樹,“夏夜,蚊子多了,便搖著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里看那一點一點的晴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后來他把這“槐蠶”寫進(jìn)了《野草·復(fù)仇》中。
“紫藤”和“槐樹”則出現(xiàn)在《傷逝》里:男主人公涓生住在會館,破屋破窗,窗外有“半枯的槐樹和老紫藤”。跟子君約會時,窗外半枯的槐樹發(fā)了新葉,還有“掛在鐵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子君去世后,“我”重回兩人曾共同生活的小屋,看到窗外依然是“半枯的槐樹和老紫藤”。熱戀時,寫到開放的槐樹和紫藤,這兩種豆科植物,開花時都極為繁盛,大團(tuán)花串和馥郁香氣來得轟轟烈烈;戀愛失敗,再次寫到這兩種植物,秋冬時節(jié)綠葉凋盡,裸露出糾纏曲折的禿枝,特別給人蕭瑟零落之感——把極盛極衰對比強(qiáng)烈的植物放入小說,用來映照涓生和子君的愛情,可謂神來之筆。
魯迅買下阜成門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的房子,在“老虎尾巴”的后園種了丁香、碧桃、花椒、刺梅、榆梅、青楊,給友人寫信,他會告知對方丁香“活了”,榆葉梅“還未發(fā)芽”。從北京給在上海的許廣平寫信,特意說及“芍藥已開過,將謝了”。在廈門給李小峰寫信,也專門提到“住所門前有一株不認(rèn)識的植物,開著秋葵似的黃花”,“還有雞冠花,很細(xì)碎,和江浙的有些不同,也紅紅黃黃地永是這樣一盆一盆站著”,“然而荷葉卻早枯了;小草也有些萎黃”;一個半月之后再通信,又復(fù)提及:“天氣,確已冷了。草也比先前黃得多;然而我門前的秋葵似的黃花卻還在開著,山里也還有石榴花。”魯迅固然多多少少借助這些閃現(xiàn)在文字中的花草身影,傳遞一點個人的微妙情緒,但其間并無多少刻意經(jīng)營的成分,最根本的還是因為身邊的花草樹木對他來說,就是“切己”之物,如此種種,不過是“說說較為切己的私事”。
魯迅對“博物學(xué)”的喜愛,也處處印證出他對“實地經(jīng)驗”,對“生命親證”的看重和尋求
2 “博物學(xué)”中的實地經(jīng)驗,向低廣處看
我們在前一部分談及,魯迅厭惡“不是出于自己真實的內(nèi)心,唯順大勢而發(fā)聲”的“偽士”(后來又有“做戲的虛無黨”之說法),作為對“偽士”的拒絕和抵抗,他強(qiáng)調(diào)自己只愿“說說較為切己的私事”。而判斷事物是否“切己”、是否“出于自己真實的內(nèi)心”的依據(jù)是什么呢?魯迅的好友瞿秋白曾經(jīng)說,“文人對于宇宙間的一切現(xiàn)象,都不會有親切的了解,往往會把自己變成一大堆抽象名詞的化身。一切都有一個‘名詞’,但是沒有實感。……對于實際生活,總像是霧里看花似的,隔著一層膜。”所謂“實感”,也就是實際去接觸、體驗具體事物之后所獲得的感受。魯迅也有過類似的表述,早年在《摩羅詩力說》中就曾這樣說:“熱帶人未見冰前,為之語冰,雖喻以物理生理二學(xué),而不知水之能凝,冰之為冷如故;惟直示以冰,使之觸之,則雖不言質(zhì)力二性,而冰之為物,昭然在前,將直解無所疑沮。”后來在《讀書雜談》中也說,僅僅讀書、“腦子里給別人跑馬”還不行,思索者好一些,能用自己的腦力,“但還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觀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這一部活書。這是的確的,實地經(jīng)驗總比看,聽,空想確鑿。我先前吃過干荔支,罐頭荔支,陳年荔支,并且由這些推想過新鮮的好荔支。這回吃過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廣東來吃就永不會知道。”許壽裳稱魯迅的“思想方法,不是從抽象的理論出發(fā),而是從具體的事實出發(fā)的,在現(xiàn)實生活中得其結(jié)論”,也反應(yīng)出魯迅對“實感”的看重。
已經(jīng)有學(xué)者指出,章太炎對待思想學(xué)術(shù)的一個特殊之處在于,特別重視生命親證和正面承當(dāng),而這種態(tài)度對魯迅產(chǎn)生了至為深刻的影響。關(guān)于這個問題,前輩學(xué)者已有相當(dāng)精彩的闡發(fā),這里不再展開;我想探討的是,魯迅對“博物學(xué)”的喜愛,也處處印證出他對“實地經(jīng)驗”、對“生命親證”的看重和尋求。
我們知道“博物學(xué)”本身是一門與天地萬物相接相觸而生的學(xué)問,它在根柢上就離不開“實地經(jīng)驗”、離不開“生命親證”。周作人曾說中國人向來拙于觀察自然,傳統(tǒng)文化中沒有發(fā)展出獨立的植物學(xué)、動物學(xué),只附屬于經(jīng)學(xué)等別的門類,經(jīng)學(xué)家考名物往往只是在書齋里翻書,對草木蟲魚的注釋多依據(jù)前人而非自己的觀察,所以讀者看了也往往不得要領(lǐng)。而魯迅少年時代喜歡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雖然也是考名物以注經(jīng),但它不僅僅將重點放在“名”上、以別名訓(xùn)本名,而能注意到自然物本身、將“名”與“實”對應(yīng)起來,“在現(xiàn)實觀察的基礎(chǔ)上對動、植物形態(tài)詳細(xì)描述,并指出生長地及其效用”,“眼界已從經(jīng)的傳疏引向外在實際的自然界”。后來從日本歸來,在杭州浙江兩級師范學(xué)堂和紹興府學(xué)堂任教那幾年,魯迅抄錄了許多“博物學(xué)”方面的圖書,比如晉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狀》,唐代段公路的《北戶錄》、劉恂的《嶺表錄異》,宋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等,這些記錄廣東、廣西、云南等南方各地自然地理、風(fēng)土特產(chǎn)、草木蟲魚的著作,都是根據(jù)作者本人在當(dāng)?shù)刈龉倩蚋叭瓮局杏H聞目見并結(jié)合老百姓日常經(jīng)驗而來。郝懿行的《燕子春秋》、《蜂衙小記》、《記海錯》,則是關(guān)于小動物的著作:《燕子春秋》分十二個月描述燕子隨四季流轉(zhuǎn)而變換的生活習(xí)性;《蜂衙小記》則是對蜜蜂的生理和養(yǎng)蜂經(jīng)驗的總結(jié);而《記海錯》收錄了山東沿海四十余種海產(chǎn)品,每一則以品種名為題,詳述其形狀、產(chǎn)地、產(chǎn)時、烹飪藥店、風(fēng)味特色和儲存辦法等各方面。周作人曾專門寫過一文表達(dá)自己對郝懿行的欣賞,稱他的學(xué)術(shù)思想“切實而寬博”:郝氏自稱“少愛山澤,流觀魚鳥,旁涉夭條,靡不覃研鉆極,積歲經(jīng)年”,所以能“寬博”;而“蟲魚之注,非夫耳聞目驗,未容置喙其間”,故而“切實”——“他的箋注與眾不同,蓋其講蟲魚多依據(jù)耳聞目驗,如常引用民間知識及俗名,在別人書中殆不能見到也”。
草木蟲魚相關(guān)的“民間知識及俗名”,也是周氏兄弟多有留意的。他們都收藏了清代范寅的《越諺》,這部書專門研究紹興諺語,中卷釋名物,專門有草木果蔬的俗名及相關(guān)諺語、歌謠。周作人的博物小品文常常征引此書,比如《兩株樹》、《花草的俗名》等。魯迅在翻譯《小約翰》等作品的時候,除了查考動植物的學(xué)名,還會特意留心一下它們的俗名,比如有兩種昆蟲“鼠婦”和“馬陸”,魯迅說前者在他們紹興方言里稱為“臭婆娘”,而后者在廣州有俗名“地豬”。《小約翰·動植物譯名小記》中,魯迅還特意說:“經(jīng)學(xué)家對于《毛詩》上的鳥獸草木蟲魚,小學(xué)家對于《爾雅》上的釋草釋木之類,醫(yī)學(xué)家對于《本草》上的許多動植,一向就終于注釋不明白,雖然大家也七手八腳寫下了許多書。我想,將來如果有專心的生物學(xué)家,單是對于名目,除采取可用的舊名之外,還須博訪各處的俗名,擇其較通行而合用者,定為正名,不足,又益以新制,則別的且不說,單是譯書就便當(dāng)?shù)眠h(yuǎn)了。”他晚年翻譯《藥用植物》,里面多涉與植物相關(guān)的民俗和傳說,試舉兩例:
葛,為自生于山野的落葉藤本,夏秋之候,開紫紅色的蝶形花。秋季掘根而干燥之,謂之葛根,漢方以為發(fā)汗解熱的要藥。古來以感冒藥著名的葛根湯,就是混合葛根、麻黃、生姜、大棗、桂枝、芍藥、甘草這七味的。關(guān)于那藥效,可參照麻黃條。葛根又以供葛淀粉的制造原料。葛淀粉雖風(fēng)味佳良,但因價貴,故現(xiàn)今出產(chǎn)殊少,市場上所販賣的葛淀粉者,乃是馬鈴薯淀粉也。
何首烏,是自生于中國及日本各地的多年性蔓草,根稱何首烏,漢方以為強(qiáng)壯藥,謂有長生不老之效。約十年以前,在日本也非常流行。何首烏者,令何氏的發(fā)變黑之意,是起于“昔何公服之,白發(fā)變黑,故號何首烏”的故事的。
從古至今,草木蟲魚一直參與著人類的日常生活,是一時一地風(fēng)土民情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的俗名,跟它們相關(guān)的故事、傳說,土生土長,帶著濃郁的生活氣息和活潑的生命質(zhì)感。在書本上看到某個動物、植物的學(xué)名,可能你的腦中空空如也,因為它對你來說,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沒有任何切實的經(jīng)驗與之相對應(yīng);而與生活世界根柢相連的地方俗名,卻往往能喚起我們親切的情感記憶。周氏兄弟留意動植物的土俗名和相關(guān)的民間傳說,看重的也是其中所包藏的“實的生活”之豐富信息吧。
魯迅愛好的“博物學(xué)”書籍中有一類是文字之外還帶有圖畫的,比如《爾雅音圖》、《毛詩品物圖考》、《花鏡》、《野菜譜》等。《爾雅音圖》的畫譜由清代姚之麟繪,總共六百五十幅,其中下卷的《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所占比重最大,尤以《釋草》篇最詳備,繪圖多達(dá)一百七十六幅。日本岡元鳳所著《毛詩品物圖考》分七卷考釋《詩經(jīng)》中的動植物,草部二卷,木部、鳥部、獸部、蟲部、魚部各一卷,共有二百一十一幅用筆精細(xì)的圖譜,周作人曾回憶說魯迅當(dāng)年從書店買來發(fā)現(xiàn)偶有破損或墨污,就三番五次拿去調(diào)換,以至于被書店伙計戲弄說,“這比姊妹的面孔還白呢,何必?fù)Q掉”,不好再換就減價賣給同窗,又貼補(bǔ)一角新買一部——對此書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而魯迅自稱“最愛看”的《花鏡》有不同的版本,據(jù)說圖譜最多的版本為花說堂版,共三百二十二幅,最少的為善成堂版,共一百四十四幅,魯迅當(dāng)年買回的版本有多少圖不得而知,但他自己的記憶反正是“上面有許多圖”的。除了搜求和購買,魯迅還喜歡影寫畫譜,其中就有明代王磐的《野菜譜》,此書所集都是作者親自嘗驗而來的可以度荒的草木,總共繪制了五十二幅圖譜,每張圖譜上面都有簡單的文字介紹,標(biāo)明采食的時間和方法,還附有以菜名起興的樂府短詩。魯迅當(dāng)年從家中書櫥中找到這一本,從頭到尾仔細(xì)抄繪了一遍;周作人說,照理自家的書是不必抄的,之所以如此,“實在只是對于《野菜譜》特別的喜歡”。
除了上述這類圖文相配的書籍,魯迅還喜歡收藏各種博物畫譜和花鳥圖冊。比如宋代宋伯仁撰繪的、我國第一部專門描繪梅花種種情態(tài)的木刻畫譜《梅花喜神譜》,清代畫家改琦的墨筆梅花圖《小百梅集》,陳叔通收集明清兩代各家畫派所繪梅花而成的《百梅集》,日本明治時期畫家幸野梅嶺的花鳥繪集《梅嶺百鳥畫譜》,還有明代徐渭、陳淳,清代蔣廷錫、金農(nóng)、陳洪綬、吳昌碩等名家的各種草木蟲魚花果圖冊。
特別值得一說的還有魯迅對花鳥箋譜的愛好。居住北京的十幾年間,他一直是琉璃廠的常客,除卻購買書籍和畫冊,也搜集各種箋紙。鄭振鐸曾經(jīng)寄贈魯迅一套《百花詩箋譜》,收入清代畫家張兆祥花卉圖一百幅。張氏認(rèn)為要畫出好的植物圖,必須本人親自養(yǎng)花,所以他專門辟出一片花圃,每日觀察揣摩、對照實物寫生,筆下百卉色彩生動、細(xì)節(jié)精確。這套箋譜深得魯迅喜愛,并促使他決定自己編一套箋譜集,他跟鄭振鐸分工策劃此事,由當(dāng)時在北平的鄭振鐸負(fù)責(zé)搜購箋紙樣張、聯(lián)系印刷裝訂,在上海的魯迅負(fù)責(zé)樣張的取舍、書本的格式體例等,最終選出三百三十二幅箋紙付印,定名為《北平箋譜》。這三百三十二幅箋紙圖案中,花木蔬果鳥獸禽蟲多達(dá)二百一十一幅,剩余一百二十一幅為山水、人物等。《北平箋譜》之后,他們又重印了明代胡正言所編《十竹齋箋譜》,成書之后魯迅致信鄭振鐸,認(rèn)為“《十竹齋》箋樣花卉最好,這種畫法,今之名人就無此手腕”。
中國“博物學(xué)”傳統(tǒng)中考釋名物這一脈往往陷入以書注書的循環(huán),缺乏實際經(jīng)驗的支撐
中國“博物學(xué)”傳統(tǒng)中考釋名物這一脈往往陷入以書注書的循環(huán),缺乏實際經(jīng)驗的支撐,“征引了一大堆到底仍舊不知道原物是什么”;而某種意義上,美術(shù)中的草木蟲魚,對傳統(tǒng)“博物學(xué)”這方面的缺失是一個很好的補(bǔ)充。因繪者本身需要對所繪之物有一個真切的感受,才能用線條和色彩將其呈現(xiàn)于紙上,這自然是帶著繪者的“實感”的;而對于觀者來說,圖畫比文字更加有形、具體,能給人以直觀的印象,也就更容易通向“名”與“實”的對應(yīng)。我們知道魯迅從小就喜歡美術(shù),這也與他天性和稟賦跟美術(shù)這種藝術(shù)形式的特殊性相貼近有關(guān)吧。


世人熟知魯迅戰(zhàn)斗的一面,但或許這悉心選畫所流露出的溫柔敦厚,才是他生命的底色吧
從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古籍中的“博物學(xué)”也好,美術(shù)中的“博物學(xué)”也好,魯迅評判的一個重要標(biāo)準(zhǔn),就是背后是否有切身的“實感經(jīng)驗”作支撐。更重要的是,魯迅本人對“博物學(xué)”的喜愛方式,也有著他自己的“實感經(jīng)驗”參與其中。



輯錄古籍的選擇標(biāo)準(zhǔn)、對動植物俗名的看重、博物圖譜和花鳥畫冊的搜求,以及在自己故鄉(xiāng)的土地上尋采植物等等,所有這一切都體現(xiàn)出魯迅向“低的廣的方面”尋求實感經(jīng)驗的努力。“低”、“廣”,也就是周作人稱贊郝懿行所用的“切實”而“寬博”吧。可以說,魯迅對“博物學(xué)”的喜好,是他通向“切實而寬博”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途徑。

“重新回到這個世界的日常性中來”、恢復(fù)“與他置身的環(huán)境”的“有機(jī)的聯(lián)系”,正與我們剛才所說的向“低的廣的方面”尋求實感經(jīng)驗、“切實而寬博”的精神相互溝通


?周作人:《魯迅讀古書》,《魯迅的青年時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72頁。
?舒蕪:《魯迅、周作人失和以前的兄弟關(guān)系》,《周作人的是非功過》,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315頁。
?周作人:《自然》,《周作人文類編·人與蟲》,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1—2頁。
?參見《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18頁。
? 魯迅:《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30頁。
? 伊藤虎丸:《亞洲的“近代”與“現(xiàn)代”》,《魯迅、創(chuàng)造社與日本文學(xué)》,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7頁。
?魯迅:《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5頁。
?魯迅:《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5頁。
? 魯迅:《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5、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