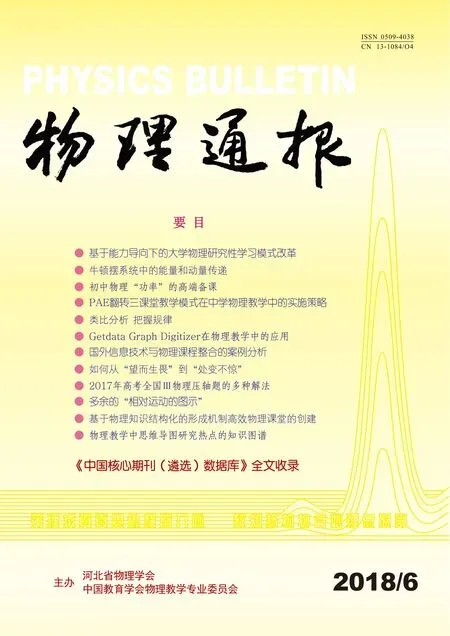初中物理“功率”的高端備課
關艷麗
(首都師范大學物理系 北京 100048)
邢紅軍
(首都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 北京 100048)
功率是初中物理學生學習“功”的概念之后的又一個新的概念.功作為一個過程量,在物體做功過程中伴隨著時間的變化,因此功的概念必然存在做功快慢的問題,于是功率的概念就應運而生.從這個意義上講,功率概念建立的出發點在于比較做功快慢的意義而不是單純比較做功的大小.由此,如何基于初中生的認知發展水平建立功率的概念,并進一步幫助學生理解功率的物理意義,就成為本節課教學的重中之重.
1 現行教材功率概念編寫研究
現行教材[1]功率概念的編寫通常設置如下物理情境:一個大人和一個小孩一起爬相同的樓梯,再結合比較做功快慢的兩種觀點,從而引入功率概念.第一種觀點認為:不同的物體做相同的功,所用的時間可能不同,時間短的做功快,時間長的做功慢.第二種觀點認為:不同的物體做功的時間相同,它們做功的多少可能不同,在相同的時間內,做功多的物體做功快,反之做功比較慢.而后教材采用類比的方式指出,就像速度表示運動的快慢一樣,功率表示做功的快慢,從而直接給出功率的定義:功與做功所用時間之比叫做功率,它在數值上等于單位時間內所做的功.最后,教材給出功率的表達式及其單位.至此完成對功率概念的建構.
筆者認為,教材功率一節的編寫存在一些有待商榷的問題.
第一,教材直接提出了兩種比較做功快慢的方法:控制做功相同,比較所用時間長短;控制時間相同,比較做功多少.這種方法把多因素問題變成多個單因素問題,通過改變其中某一個因素,從而研究該因素對事物的影響.其優點在于降低了問題的難度,缺點是定義建構的意義不甚明朗.具體而言,雖然做功快慢與做功的多少及時間有關,并且可以通過只改變一個變量進行比較得出結論,但是做功與時間比值關系的必要性并沒有從邏輯上順理成章地給出解釋.
第二,教材直接給出“一個大人和一個小孩一起爬相同的樓梯,做功是否相同,做功快慢是否相同的問題”,進而帶領學生直接比較分析,意欲引導學生自主選擇以上兩種觀點從而得出比較的結論.然而,這種方法并不是特別理想的方法.這是因為,初中學生的物理思維基本上還處于具體運算階段和前運算階段[2].處于這個階段的初中生需要借助具體事物的支持,才能進行抽象思維運算.因而,筆者認為,在比較方法與思維運算之間,缺乏具體事物的支持.
第三,教材缺乏對功率物理意義的深入剖析.教材提出:就像用速度表示運動的快慢一樣,在物理學中,用功率表示做功的快慢.功與做功所用時間之比叫做功率.這樣就忽視了比值定義法的本質——為什么要用兩個物理量的比值定義一個新的物理量[3].由于對功率的物理意義闡述不清,從而導致學生不能深刻理解功率的物理意義,并容易與機械效率的概念相混淆.
2 功率的高端備課
通過對現行教材功率概念編寫的研究,我們按照比值定義法的邏輯,展開對初中物理“功率”概念的高端備課,并提出以下教學設計思路.
2.1 直接比較做功的多少
新課引入設定情境如下:
情境1:臺北的101大樓擁有曾列入世界吉尼斯紀錄的快速電梯,其上行最高速率可達每分鐘1 010 m,相當于時速60 km,假設Norbert Lechner乘電梯從1樓到91樓高390 m的室外觀景臺,用時大概40 s.
情境2:臺北101國際登高賽(Taipei 101 Run Up)是一場每年固定以臺北101大樓作為比賽場地的登高賽.所有參賽者必須征服1至91樓共2 046個臺階、390 m的高難度挑戰.圖1為2014年臺北101國際登高賽時參賽者Norbert Lechner(中)以13 min56 s的成績登頂,隨即累得跪倒在地的圖片.

圖1 2014年臺北101國際登高賽照片
根據以上具體事例,假設Norbert Lechner的質量為75 kg,教師引導學生計算兩種情境下電梯和人做的功.
根據式W=Fs計算可知,電梯對Norbert Lechner做的功和Norbert Lechner自己攀登到91樓所做的功相同,都為292 500 J,但是做功的意義卻完全不一樣.乘電梯到達91樓的Norbert Lechner可以悠閑地觀景,而參加登高比賽的Norbert Lechner到達91樓時卻累得跪倒在地.
顯然,在做功相同的情況下,卻產生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因此,只比較做功的多少并沒有意義,還要考慮做功所用的時間才有意義.
2.2 選取相同的時間標準繼續比較做功
重新審視情境,可以發現相關因素還有時間不同,于是教師引導學生選取相同的時間標準繼續比較電梯和人做的功.

2.3 進一步詮釋比值的物理意義

回顧高端備課的過程不難發現,在功率概念的建立過程中,對做功結果的討論是順利得出功率概念的關鍵.正是由于參賽者Norbert Lechner以兩種方式到達觀景臺的結果大相徑庭,才使得學生發現,僅通過比較做功的多少并不足以衡量做功的意義,于是功率概念建立的必要性才凸顯出來.也就是說,電梯的功率大,在相同的時間內做功多,可以快速完成使Norbert Lechner到達91層所做的功.而Norbert Lechner本人的功率小,所以要做相同的功就需要耗費更多的時間,由于做功消耗了他的能量,所以就產生了累倒在地的結果.相同的做功卻造成不同結果的原因,歸根結底就在于功率的不同,從而說明了功率概念建立的必要性.
3 高端備課的啟示
3.1 注重物理概念意義詮釋
物理意義指一個物理量的全部內涵與外延及其反變關系[5].物理意義一方面指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描述物理量,另一方面指引入該物理量的作用.前者意指物理量本身或者多組物理量重組后對其物理量本質的理解,后者意指建立此物理量的原因.如果說前者可以幫助學生理解物理概念的含義,那么后者則可以更好地幫助學生牢記物理量并且避免與其他物理量混淆.例如,在功率概念的教學中,從比較功的本身出發,發現僅通過比較做功多少并不足以彰顯做功的價值與意義,由此引入功率的概念就十分必要.這也就充分說明,功率概念物理意義的闡述是引入功率概念的關鍵.通過對功率概念引入原因的理解,學生就可以避免將功率概念與功的概念混淆.此外,注重物理概念意義的教學,也為物理概念教學提供了新的思路,并給出了物理概念教學邏輯闡述的范例.
3.2 運用科學方法顯化教學
科學方法顯化教學指在教學過程中不僅使學生體驗科學方法,還要向學生明示科學方法.通過告訴學生探究過程中所使用的科學方法,使學生掌握科學方法的本質,獲得探求物理知識的工具,便于在今后的學習過程中運用科學方法得出物理知識.比如,在功率的教學設計中,按照比值定義法的步驟選擇比較對象,在比較過程中發現問題,從而將做功所用的時間作為比較的標準,并最終得出功率的定義式.顯然,學生只有顯化科學方法進行探索和嘗試,才能形成有序的知識結構.
3.3 體現物理教學設計創新
以往運用比值定義法定義物理概念時,兩個比較對象的設定往往是不一樣的.如在密度概念的教學中,首先比較兩個不同質量的物體,發現直接比較得出的結果有悖于學生的日常經驗,于是將兩個質量不同的物體的體積變成相同后繼續比較它們的質量,從而得出密度的表達式,壓強和速度概念的得出亦如此.而在功率概念的教學中,選取的比較對象卻是做功相同的不同情境,并以做功意義的不同作為引發認知沖突的著眼點,于是將時間作為比較的標準,從而順理成章地得出功率的定義式.顯然,正是由比較對象的“不同”到比較對象“相同”的轉變,才能在遵循比值定義法內涵的前提下,實現教學設計的創新.這樣的教學設計,突破了以往比值定義法教學的邏輯思路,為比值定義法的教學開辟了新的途徑,從而體現了物理教學設計的創新.
參 考 文 獻
1 人民教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物理課程教材研究開發中心.物理(八年級下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65~66
2 喬際平,邢紅軍.物理教育心理學.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2.27~115
3 邢紅軍.初中物理科學方法教育.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8
4 侏羅·齊澤維茨著.科學發現者 物理原理與問題(中冊).錢振華,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8.277
5 陽玉崗.關于物理意義的教學.樂山師范學院學報,1994(2):4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