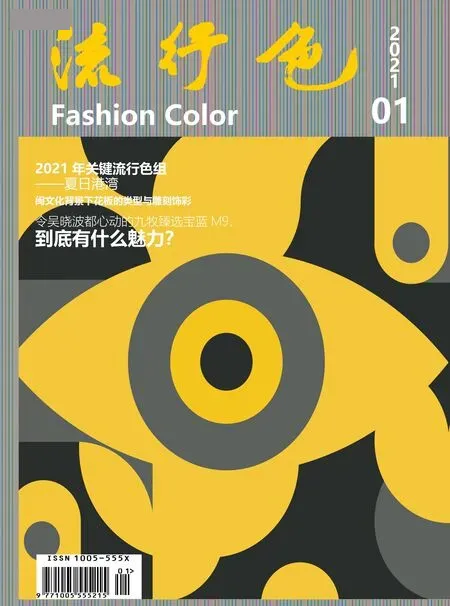淺析田中一光招貼設計中色彩風格的表現形式
張夢曉
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 上海 200072
一、田中一光簡介
田中一光作為日本平面設計協會和AGI 的成員,在世界平面設計界中享有很高的榮譽。他的作品根植于日本傳統美學文化,將現代的觀念帶入傳統的文化中。他給“日本平面設計”賦予了明確的方向性,他提出“手法可以借鑒,概念絕不混搭”的明晰理念。在田中一光的招貼作品中采用的色彩基本上都是素色,以色造型,色和形相輔相成。最為常見的就是白、黑、青、赤四種基本顏色,表現出濃厚的民族特色,同時又具有現代感。他對于傳統色彩獨特的思路和表現手法使得其在國際上斬獲眾多獎項,是日本設計史中首屈一指的大師。
二、田中一光招貼設計中色彩風格的形成背景
1.日本獨有用色文化背景的熏陶
日本的文化發展是基于大量吸收外國文明的精華基礎上的,這些精華在加以消化和融合日本本身的文明傳統、特殊的地理環境、獨特的社會結構后,使得日本的文化、經濟、政治都與眾不同。日本的設計,也是基于這種模式發展起來的 。田中一光的設計文化背景與他長期生活的文化環境有很大的關系。日本設計在用色方面非常在意其色彩的文化含義,在歷史上日本人獨愛自然色,特別是白、黑、赤、青四個顏色。在田中一光的用色風格中能夠看到從中體現出日本傳統色彩的獨特性,還有日本人特有的審美觀念。
2.浮世繪色彩創作形式的影響
“浮世繪”是日本的風俗畫或者稱作版畫,它是在日本江戶時代興起的一種獨特的傳統藝術文化。是指以轉喻、諧音等比附的手法,構成具有某種吉祥意味的裝飾紋樣,代表著傳統的民風民俗 。田中一光的海報設計在色彩等方面可以看出浮世繪獨有的創作形式,例如兩者的設計中在色彩的對比上與浮世繪色彩單一相協調,在用色上都飽滿厚重,富有裝飾性意味,同時也飽含很多象征意義,以及注重平面裝飾感的特征。
3.瑞林留白藝術魅力的感染
不可否認作為日本傳統藝術代表之一的浮世繪確實為日本平面設計師提供了大量的靈感和素材,但是,相對于以江戶時代普通人為對象進行創作的浮世繪,主要以京都的貴族宮廷文化為中心進行“物的設計”的“琳派”藝術而言,其特有的日本獨特的著色方式,以及最大限度的“留白”等都在日本現代海報設計中被大量采用。田中一光是承襲琳派傳統藝術風格的代表設計師,其主題選擇和設計風格中可以看出琳派藝術對其的影響。
三、田中一光招貼設計中色彩風格的表現形式
當人們通過海報進行溝通時,在設計上的獨特性和普遍性就會被各種不同的感情表達出來。本文主要從用色習慣、造型、符號、意境四個方面來分析和借鑒在招貼設計中對日本傳統色彩進行的演繹、延伸和發揚。
1.傳統用色習慣在設計中的應用
每個民族使用色彩的習慣都是不同的,通過其對色彩的運用,可以表達出相應的民族感情。色彩的敘事意義是象征性的、暗示性的,面對同樣的顏色,人們會因為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導致體驗到不同的感受。受禪宗思想的影響,日本設計作品在用色的時候崇尚素色,大多不會使用艷麗的顏色,從日本最早期的設計作品中就可以看出這種用色習慣,日本最早開始使用的是白、青、赤、黑四種顏色,在田中一光的招貼作品中就大量的使用了這幾個顏色,并且在設計中強調裝飾性和象征性等東方式色手法,透露出對禪宗思想的深入理解,充滿了濃烈的民族地域色彩。在田中一光的作品中,通過用色彩進行造型、以及借鑒傳統色彩,使得他的作品在表現傳統主題時既古樸淡雅又充滿了現代元素,在海報設計中色彩的運用被賦予了民族和地域性質。如圖-1《札幌冬季奧運會》參考日本“琳派”的名作《日月屏風》的構局方式,海報大面積色彩的使用上運用了白、黑、赤這三種顏,整體的色調是灰色調。由于日本的國旗是赤色的,在這幅海報中,赤色就代表了日本,黑色則象征著連綿的山脈,白色則代表這日本最富有盛名的富士山,這些用色都于日本禪宗的觀念信仰有關。

圖-1 田中一光海報《札幌冬季奧運會》,(來源:網絡)
2.傳統幾何造型與色彩的組合
傳統的日本造型呈現出幾何化,不僅源于日本傳統的理性設計美學,還源于歐洲構成主義所造成的影響,而規整的幾何圖形同樣也是田中一光的重要設計風格之一。圖-2《日本舞蹈》中田中一光將歌舞伎的臉用幾何等分,通過將兩個代表眼睛的半圓向內傾斜來簡單地表達舞者極其豐富的表情,畫面以簡單幾何造型達到了造型表現的目的,并且主要以黑色和赤色為主,旁邊的輔色可以對主色起到突出作用,并營造出一種立體感和空間感。堪稱日本設計中傳統幾何化風格的典范,用簡單的幾個顏色組成的色塊來表現海報的活力,幾何的設計能夠最大限度的呈現出色彩,幾何與色彩也是相輔相成的關系,整個海報正是日本傳統幾何造型與傳統色彩的完美融合的體現。
3.傳統符號上色彩的體現
田中一光的海報大量地應用了日本本土的傳統符號,并將日本能劇、舞蹈等傳統藝術當做主題。他用這些傳統的符號作為自己創作的載體以此展現出日本民族簡潔的藝術氣質和獨有的特征。在田中一光能劇海報作品中絕大部分都直接把能面作為主體,面具上使用的色彩都是極度簡潔的,除了眼睛和嘴巴大多使用紅色外,基本不會出現明度純度過分飽和的色彩。在《第二十八回產經觀世能》中將能劇“楊貴妃”本身的能面形象進行簡化,形成了純粹的白底,而眼睛還有鼻子都使用了赤色也就是紅色,達到了高度的單純和精煉,也可以更加烘托出楊貴妃的美貌,從簡化的能面形象中不難看出日本對待色彩獨有的民族用法。
4.傳統意境中留白的表達
意境,指的藝術作品通過借助形象索傳達出的情感和境界,在日本宗教問題上,由于信奉禪宗佛教的原因,設計師想要傳達一種簡單而樸實的觀念,強調精神世界的美好。圖-3《第五回產經觀世能》便很好地意境這一獨特的表現形式,田中一光在空間設計上進行色彩的單純化和強烈對比。并將能面形象進行去繁化簡,使上半部出現了一塊留白,白色跟灰色一樣被稱為無彩色,它們缺乏彩度的變化,只有明度上的區別,這個留白主要在心理層面有著調節情緒的用途,白色可以跟人帶來安靜、虛無、單純、樸實的心理感受,通過白色這種在日本有著圣神意義的顏色,通過海報中在超自然的寂靜中表達了一種超出人類世界的無法的悲傷,也展現出來能劇不可言傳只可意會的意境世界。
結論
綜上所述,田中一光所處的時代非常特殊,經歷了日本傳統和西方思潮不斷碰撞和交流的年代,在他的招貼設計作品中,我們既可以看到現代派對他設計風格所產生的影響,同時也不乏日本傳統藝術的特點。通過上文對于色彩風格表現形式的簡單分析可以看出其設計用色重點主要是直接源自或基于日本傳統白、黑、赤、青四個顏色。并通過調整色彩與現實之間的關系,將規則的幾何形狀和傳統元素進行了隨性變化組合,這種色彩風格繼承了日本傳統文化的精華,還與現代主義的設計風格相結合,創新出了獨有的視覺形象語言,飽含對日本民族色彩和傳統文化的深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