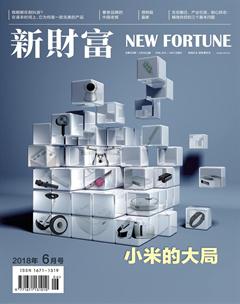美國選擇雙邊談判策略,沖擊WTO多邊貿易機制
丁安華
中美貿易爭議從雙邊談判到多邊場合兩條戰線同時上演。5月4日,中美首輪貿易談判美方提出了一個涉及廣泛的訴求清單,市場關注的焦點集中在美方要求縮減中美之間的貿易赤字規模和要求中國停止對“中國制造2025”相關產業的補貼之上,對幾項涉及多邊貿易機制特別是WTO的申訴案件的關注較少。5月8日,中美雙方貿易代表在日內瓦舉行的世貿組織總理事會會議上再次針鋒相對,議題相對集中而言辭激烈。5月17日,中美就經貿問題進行第二輪磋商并取得成果。
面對這場備受矚目的談判,或許我們應該梳理一下中美爭論的緣由和可能的演變趨勢,這關乎WTO多邊機制的前途并取得成果。
美方在中美貿易談判中提到的幾項WTO申訴案件
今年3月23日,美國向WTO提訴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相關措施,即DS542案。美國主要援引《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認為中國剝奪了外國知識產權持有者的權力,據此提出磋商要求。作為回應,中國在4月4日也向WTO提出了申訴,即DS543號案件,針對美國以中國竊取美國知識產權為由宣布將向中國商品加征關稅的做法,向美方提出磋商。中國認為美國的301調查違反WTO的最惠國待遇原則,訴諸單邊行動而非通過WTO爭端解決程序。
從首輪談判流傳出來的文件看,美方提出了關于WTO的幾項案件的訴求。美方要求中方按照DS542美方提出的要求,于年內刪除《中國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及《中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當中的相關條款,此舉等于不經WTO爭端解決程序、要求中國直接接受美國提出的申訴要求。而有關中國控訴美國的DS543案,美方要求中方在7月1日之前撤回控訴,并承諾不就該內容再次上訴。
此外,美國要求中國撤訴的案件還包括中國在2016年提出的DS515案和DS516案,分別是針對美國和歐盟的關于價格比較方法的控訴,目前分別處于磋商和專家小組調查階段,即WTO爭端解決機制的第一和第二步。這兩個案件涉及前幾年比較受關注的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美國(和歐盟)不認可中國加入WTO相關文件中關于中國入世15年后自動獲得“市場經濟地位”的“日落條款”。
美國為何會在雙邊談判中提出涉及WTO爭端解決機制的案件?
一個顯而易見的回答是,美國對WTO的多邊機制失去耐心。1995年至今訴至WTO的543個爭端案件當中,中國作為申訴方(complainant)有16起案件(其中11件針對美國,5件針對歐盟);作為應訴方(respondent) 有40個案件(其中22件來自美國,8件來自歐盟)。中國被訴案件涉及的法律點相對集中,主要是補貼與反補貼、進出口許可和征稅、傾銷和反傾銷、貿易相關的投資等。在已經終結的30起被訴案件中,有15起敗訴,另有15起在磋商階段達成和解。
拋開雙方的理據不論,美方針對的貿易爭端的解決途徑,取態已經明顯改變:那就是舍棄多邊機制,付諸雙邊貿易談判。也就是說,美國不想看到這些案件在WTO爭端解決機制當中被拖延太久,也不想得到任何不滿意的結果。無論是美方勝算大還是贏面小的案件,特朗普的貿易政策團隊都希望通過雙邊談判直接施壓而迅速終結爭議。可見,多邊機制顯然不是特朗普政府青睞的問題解決途徑。從這點看,在與中國的首輪貿易談判中提到幾起涉及多邊機制的案件,就不難理解了。
美國對WTO多邊機制有何不滿?
美國與多邊貿易機制的關系從來就不單是經濟政策決定的,更重要的因素是國內政策和外交戰略。美國傳統的建制派政治精英在二戰后推行多邊自由貿易的主要目的很清晰:一是促進資本主義價值觀和自由市場信條在全世界傳播;二是促進國與國之間的貨物貿易相互關聯,通過經濟融合從而防止戰爭;第三是助力美國企業在全球的擴展布局,維護美國的商業利益。
戰后美國貿易政策的制定權,有一個從國會到總統的演變過程。在1974年之前主要是由國會主導貿易政策。受制于選區選票的民粹壓力,國會議員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嚴重,那時美國的平均關稅一直比較高。而1974年的《貿易法》為總統開通了快速通道,總統可以不經過國會同意便同別國進行貿易談判,有權根據互惠對等原則降低甚至取消關稅。自此,總統擁有的“快軌權力”(fast track negotiating authority)成為了美國貿易政策分權制衡中的主導力量。1994年國會在強烈保護主義氣氛下曾拒絕延長“快軌權力”。在2002年又恢復了此項權力,并改稱為“貿易促進權力”(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在擺脫民粹的制約之后,美國建制派精英主導的行政部門致力于推進多邊自由貿易,不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執政,總統和行政部門傾向于支持自由貿易和多邊貿易體系。美國的加權有效關稅稅率由1970年的6%,下降到1975年的3.7%,再到現在只剩1.3%。
特朗普是一個另類,他顛覆了建制派精英長期以來所堅持的多邊自由貿易理念。在特朗普的貿易政策目標中,所謂“美國優先”可以理解為不講政治、只講利益。特朗普一直對WTO怨念有加,他認為正是WTO,特別是中國加入WTO這件事,造成了美國制造業職位的流失。特朗普政府還指責WTO未能為全球貿易談判達成新的規則,將美國禁錮在不合理關稅承諾當中。WTO成立之前,美國與別國的貿易糾紛主要是通過雙邊談判解決,而美國往往能夠如愿以償。而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建立使得大部分國家選擇通過多邊機制來解決糾紛,美國作為應訴方被訴共計137次,是所有成員國當中最多的。由于WTO專家組的決定通常同情申訴國立場,美國的多項貿易政策被WTO裁決為違反國際貿易法,包括小布什總統的鋼鐵關稅。可以說,WTO多邊協調機制程序對美國貿易政策帶來了一定的制約。
多邊機制的流程和時間也是WTO受到詬病的原因。WTO的爭端解決機制雖然比起國際法庭等其他多邊機制效率更高,但平均結案時間也要在一年以上,這個時間相對于美國國內的政治周期來說仍然過長。美國政府無意去改進這個問題:特朗普對WTO的一項重創在于否決了填補由7名成員組成的WTO上訴機構空缺席位的人選,目前只剩4名成員處理不斷出現的貿易爭端案件,將拖慢甚至凍結全球貿易爭端解決機制。WTO爭端解決機制需要針對具體的某個問題提出上訴;美國通過雙邊談判就可以將各種要求“一籃子”提出,這無疑更符合美國慣用的談判策略。
WTO多邊機制面臨嚴峻挑戰
中國的崛起,使得美國原本支持多邊貿易的條件加速改變。即使是美國傳統建制派的政治人物,也開始對美國推行的多邊貿易體系產生懷疑。2016年奧巴馬政府曾阻止韓國法官在WTO上訴機構的連任。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在2010年發文指出,世界已經深刻變化,那種認為國際體系需要去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追趕西方國家的思路已經完全過時了。
問題的核心還在于,美國需要在WTO擁有和保持的是絕對領導力。美國曾經一度努力將WTO保持為一個親美國的或是由美國主導和規范的多邊機構。歷史數據反映出,美國通過WTO爭端解決機制處理問題的效果比其他談判機制更好,但美國依然著眼于其受到的政策約束和非優待地位,特別是現在的WTO體系和談判中,美國并沒有特別的優勢。于是,特朗普選擇遠離和打擊多邊機制,轉向美國擅長的雙邊直接對話。
誠然,WTO多邊機制在解決雙邊問題,特別是中美這樣存在復雜關系的大國的雙邊貿易不平衡上存在諸多不足,不難理解美國想和中國單獨談。在解決雙邊復雜的貿易問題上,多邊機制力有不逮,特定的雙邊談判仍是必要的。不過,WTO多邊爭端解決機制若被架空甚或是凍結,對于全球貿易的打擊無疑是巨大而深遠的,這種可能似乎越來越大,我們應該心中有數。
對于本文內容您有任何評論或欲查看其他資本圈精英評論,請掃描版權頁二維碼,關注“新財富雜志”微信公眾號和我們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