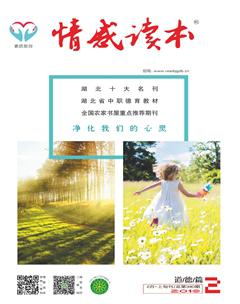學(xué)會成為一個依賴別人的人
拉姆·達斯 王國平
從靈魂的角度看待肉體,你會發(fā)現(xiàn),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并不只為了生存,也不僅是為了吃穿用度、關(guān)心別人和要別人關(guān)心,而在于映照彼此的內(nèi)心。
依賴別人是多數(shù)人的一大心理障礙,尤其是按我們這個社會的價值觀來評判。由于人們看重的是自主和獨立,依賴別人、需要幫助會給人一種渺小、脆弱的感覺。我們鼓勵幫助別人,卻不愿接受別人的幫助。
自從得了中風(fēng)后,我確實碰到過不少這樣的問題,切身體會到“自我”給我制造的麻煩。一開始我覺得無所適從,只能面對讓我想躲起來、不愿接受別人幫助的局面,“自我”的固執(zhí)和倔強最后發(fā)展成“兩歲小兒”的階段,也就是拒絕父母的幫助,但這一階段不知不覺間被帶到了晚年。
如果你從來不知道如何尋求幫助,這就成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要是羞于啟齒,你會想方設(shè)法否認(rèn)這一需求。你非但不肯接受別人伸出的援手,反倒在有這一需要時閉口不提,難以生出感恩之心,讓大家覺得生活了無樂趣。我發(fā)現(xiàn),在我們真正付出和得到時,助人者和受助者、有能力者和無能為力者之間的這條界限就消失了。
成了一個依賴別人的人,對你我來說是一個人生的轉(zhuǎn)折點。反過來說,如果你對這事推三拖四,或者是怒不可遏,不僅是在自尋煩惱,還叫照顧你的人心生不快。想想這樣的場面著實滑稽,雙方不僅難以真誠地交流,反倒裝著自己什么事都沒有。
要是你必須依靠別人,何不快快樂樂地去依去靠。這雖說不容易,但我做到了。是不能開車讓我做到了這一點。我一向是個愛車的人。一位朋友有輛漂亮的寶馬,我喜歡開著這輛車去旅行。最終我從她手上買下了這輛車,只可惜我得了中風(fēng),沒法開。我曾幻想著有朝一日能開這輛車,修理它,但后來倒是我自己被“修理了”。照顧我的人說,開這樣的好車真爽,聽到他們這么說,我心里很高興,可后來我發(fā)現(xiàn),我要想坐車,必須得有人做我的司機。想到這一點,我有點不開心,開始妒忌那些能開車的人來。這樣一來,他們反倒不自在了,好像做我不能做的事,有愧似的。
有一天,我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轉(zhuǎn)變,我沒有說:“唉,我開不了車。”而是這么想:“好啊,伙計!我的寶馬有司機了。這回我可以好好欣賞一下風(fēng)景了。”我對這段旅程津津樂道,為我開車的人也樂此不疲。我快樂,對方也快樂。
如果從靈魂的角度看待依賴別人這件事,你會有一種釋然感。你看到的不是深陷在無能中不能自拔的“自我”,而是靈魂間相互付出關(guān)愛。與其恨自己依賴別人,自責(zé)不能像從前一樣獨立,倒不如將這一處境當(dāng)作增進親情和友情的機會。
中風(fēng)前,我做夢都沒想到自己能這樣坦然地接受別人的照顧,或者說能允許別人這樣“侵犯我的隱私”,但這些經(jīng)歷給了我很深的感觸。這就是我們稱之為不幸的矛盾之處:大不幸往往是你的大幸。我這么說并不是要你盲目樂觀,沒有人希望什么都要依賴別人,或希望自己生活不能自理。我不過是承認(rèn),這一角色每每發(fā)生了轉(zhuǎn)變,我們往往會驚嘆這意想不到的益處和其中深奧的知識。
當(dāng)你見到一位需要幫助卻又不自憐、不自怨自艾的人,你會發(fā)現(xiàn)幫助他是一件輕松愉快的事。幫助這樣的人會讓你覺得自己收到了一份禮物。這不正是人與人之間的追求嗎?相互道別時,你們都會認(rèn)為自己從這次交流中受益匪淺。
從靈魂的角度看待肉體,你會發(fā)現(xiàn),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并不只為了生存,也不僅是為了吃穿用度、關(guān)心別人和要別人關(guān)心,而在于映照彼此的內(nèi)心。其他的一切不過是個點綴,是交流的媒介。羅伯·李曼(Rob Lehman)是我的一位摯友,他在給我的信中寫道:“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相互幫助、互相支持,乃大愛。”
需要別人的幫助無須諱言,對到老時不斷變化的需求坦誠以待,需要鈴木禪師所謂的“小學(xué)生心態(tài)”:不帶偏見、不抱幻想,對每一刻都感到新奇的能力。
我們不愿開口尋求幫助,往往是因為不想麻煩別人。但“麻煩”或被需要的人“麻煩”到底又是個什么概念?要想關(guān)注自己和身邊人的需求,我們必須反省自認(rèn)為理應(yīng)如此的事,以及“我是誰”“我應(yīng)該怎么做”的思維方式。
我越過了這道坎,是因為父親病得生活不能自理,繼母要我過去幫忙照顧他。一開始,我總認(rèn)為是父親的病打亂了我的生活,許多事想做都做不成。我有計劃、有打算,唯獨照顧父親不在此列。但我又不能推卸責(zé)任:父親給了我生命,如今他需要人照顧。盡管我已五十多歲,只是我沒成家,改變生活方式比其他兄弟姐妹要容易些。但這不是簡單的放棄。從六十年代開始,我想盡辦法和家人保持距離。每次從印度修完高強度的靈修課程回來,父親都會問我有沒有找到工作。我認(rèn)為他永遠也不了解我這個兒子。但如今他已八十多歲,年老體衰,需要我去照顧。
于是我搬到父親和繼母家的一間地下室。剛開始我是滿肚子的怨氣,總想著自己做出的“犧牲”,但聽著人家夸我是個好兒子,把父親照顧得這么周到,心里又很受用。日子一天天地過去,我對孝順兒子這一頭銜的興趣逐漸消退了。最后,我和父親只是兩個待在一起的人,確切地說是父與子,甚至可以說是兩個互敬互愛的靈魂。此時,誰依靠誰已不再重要。
父親去世時,我發(fā)現(xiàn)自己得到了一份厚禮,感謝上天讓我不再迷戀表面上的“自由”,以及自認(rèn)為理所當(dāng)然的生活方式。我們之間發(fā)生的一切似乎再恰當(dāng)不過,我小的時候父親照顧我,父親年邁時我照顧父親,這段經(jīng)歷給了我一種和諧與成就感。
孔羽摘自《學(xué)習(xí)做一個會老的人》
(吉林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