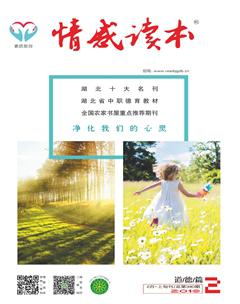蹣跚而行
弗朗西斯卡·馬丁內斯 孫開元
當我的目光不再關注自己所沒有的東西,而是關注于自己已經擁有的東西、自己能做的事情以及自己那么多因禍得福的幸運時,我的生活就會因此而漸入佳境。
我知道,大部分人寧愿讓一位醉了酒的牙醫做根管手術,也不愿意上臺表演單口喜劇。但是說實話,能給別人帶來歡笑是一件幸福的事。對于我來說,喜劇表演不止一次改變了我的生活。我直到三歲才開始蹣跚學步,這讓我興奮極了。再加一把勁兒,我居然學會了“跑步”。只是我掌握不好平衡,不能想跑多快就跑多快,不過大人們還是一邊親吻著我,一邊不停地夸我。
但是沒過多久,我就體會到了什么叫“悲慘”。醫生診斷我得了腦癱,在這之后我感覺到,很多大人見到我時,好像眼睛里總是有一點異樣的目光,他們會朝我擠出一些做作的笑容,然后就是接二連三地發出幾聲帶著憐憫的“唉”。我不能肯定他們為何會這樣,但是我感覺到了他們是在可憐我,這讓我很是不解,因為我覺得生活到處都是快樂,全家人都拿我當掌上明珠。我不喜歡那些人的同情,一點兒也不喜歡。所以,我覺得最好的回應辦法是活得可愛一些。我相信,如果我能讓那些一見到我就愁眉苦臉的大人笑出來,他們肯定就會瞧得起我,就不會再以可憐加遺憾的目光來看我——那表情和踩到蝸牛時一樣。
我越來越有幽默感,有時候我一張嘴說話,大人們就會爆發出笑聲。我很快發現,一個走路搖搖晃晃的漂亮女孩,說話過頭一些也沒人在意,于是我索性盡情發揮這一優勢。當然最重要的是將所有人對我的可憐,都消滅于笑聲之中。
我的這一策略很好使,不過到了十幾歲時壓力來了,我越來越感到,我的幽默充其量不過就是躲避別人敵意的一種無奈之舉。所以我放棄了以幽默博人一笑,而是大著膽子向別人喊:“請你喜歡我……拜托!”但是這一招讓我一敗涂地。高中畢業時,伙伴們在黑板上寫下的對我的低度評價讓我覺得自己有些可悲。
20歲時,我開始涉足喜劇表演。對于我來說,這是一次人生突破。第一次上臺時太緊張了,我甚至擔心自己的身體會在某些時候失控,但是那次上臺也讓我體會到,喜劇表演有很大的發揮自由。走上舞臺,讓我再一次真誠地看待自己,不再逃避別人對我的歧視或偏見,而是以一種輕松而友好的方式抬頭面對他們。我再次認識了年少時的自己,也找回了那種能夠打破恐懼與可憐的神奇的幽默感。我開始參加全國性的演出,信心日增。所有那些曾經讓我對自己感到低人一等并且拼命想要掩蓋的問題,我站在臺上面對眾多觀眾都講了出來。我是怎樣走路的,我需要讓別人給我把食物切碎了再吃,我需要用吸管喝水,諸如此類,無所不談。很多健全人經常是習慣以一種居高臨下的目光看待殘疾人,我想通過自己幽默的講述,讓觀眾逐漸改變他們的固有看法。
你不必因為人們的膚淺認識而讓自己信心全無,進而覺得舉步維艱。追求不切實際的目標并不會真正地對我們有好處,不是嗎?我們經常聽別人說,物質上的滿足能給人帶來快樂和自信,其實并非如此。當我的目光不再關注自己所沒有的東西,而是關注于自己已經擁有的東西、自己能做的事情以及自己那么多因禍得福的幸運時,我的生活就會因此而漸入佳境。
站在臺上探究這些想法,我發現,每個人都是不同的。一旦你意識到沒有一個人是百分之百地“正常”,意識到自信和快樂來自于自我接納,就會停止對無益目標的汲汲追求。
表演單口喜劇給了我一個機會,讓我能夠進行反思,能夠將不良價值觀拒之門外,然后以自己的智慧確定人生目標。化苦惱為幽默,讓我找回了自我感覺,讓我知道了我無法成為任何別的什么人,只能做我自己。所以,我喜歡我那步履蹣跚的身影,它讓我能夠行走在世間,即便蹣跚。
劉念摘自《時代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