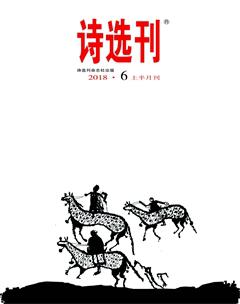冬天的妖嬈(組章)
2018-06-28 07:26:38英倫
詩選刊
2018年6期
英倫
枯荷
1
這個季節來看你,是我春天就許下的一個愿。
不用看你手相我就知道,你命里缺火,缺能燒炭打鐵焚心添欲的火。而我卻是寧可被火燒死,也不愿被流水溺死的人。再大的火遲早也會熄滅,而流水則是蛇,會永無止境地纏繞你,直至你在柔軟中麻痹,窒息。
而柔軟是愛情的良藥,鋒利也是。
而麻痹是愛情的通病,窒息也是。
火總是試著接近另一種物質,而又羞于說出初衷——
占有它,烤化它,吞噬它,蒸發它!
并習慣借助鉆木取火的典故,讓自己既膽戰心驚,又快樂無比。既內心空虛,又肉體震顫。甚至既有中求無,又無中生有。
火焰在快感中除了尖叫還是尖叫,沒有別的。而喜歡尖叫的都是神經質,都裹挾著一場愛恨,來去迅猛。這完全是對你命相的虛構,其實你還是有火的,盡管微弱,它遍布你的皮膚腳趾和嘴唇,你眼睛里的,還不足以點燃我和你的龐大世界——
一旦點燃就難以熄滅。
一旦熄滅就不再是你我。
而你心尖尖上的,我最想舔舐。
2
就這樣賴著,賴在一方塵世里,傾倒,斷折,纏繞,牽絆,借一層薄冰,倒映出往死里美的蕪雜之景。
銷蝕的激情己枯成毒蠱,懷揣解藥的人,正坐等鴨掌發出策馬而來的嫩綠旗語。
詩人借此以凌亂起旬,平仄傷感。
畫家則擯棄了十字和三角構圖,采用焦墨堆積的畫法,讓干枯豐沛,讓衰弱飽滿。
正如所有的存在都事出有因,你的愛藏得再深,也能挖出殘恨。
我的心胸再開闊,也是從狹窄的骨縫里,愛過你的那一顆。
何況,我又剛剛患過一場嚴重的風寒,虛弱,燥熱,即使被水泡著,還是口渴難耐,腳趾著火。……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散文詩(青年版)(2022年4期)2022-04-25 23:52:34
都市(2022年1期)2022-03-08 02:23:30
云南畫報(2021年8期)2021-12-02 02:46:08
文苑(2020年10期)2020-11-07 03:15:26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8期)2019-09-23 02:12:26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6期)2019-07-24 08:13:46
天津詩人(2017年2期)2017-11-29 01:24:12
視野(2015年6期)2015-10-13 00:43:11
海峽姐妹(2014年5期)2014-02-27 15:09:38
意林(2011年1期)2011-05-14 07:4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