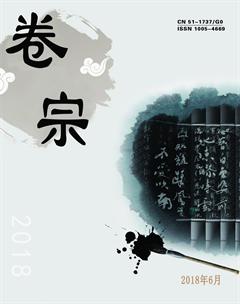系統論應如何同史學研究結合
王渤菡
摘 要:20世紀80年代在史學界掀起的系統論思潮是自然科學同史學研究理論結合的典型代表并由此形成了系統史觀。系統論甚至是自然科學在與史學研究結合時應堅持唯物史觀,同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并且加強對系統理論的認識和研究,保證理論的正確性;最后應堅持以史學研究為主,自然科學為輔。
關鍵詞:系統史觀、超穩定結構、自然科學、史學研究
1 金觀濤夫婦的超穩定結構說
20世紀80年代金觀濤夫婦首先發表了《中國歷史上封建社會的結構:一個超穩定系統》一文,初步提出了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超穩定系統的觀點,其后在《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1]一書中,金觀濤先生通過分析中國封建社會的結構及其作用機制,將中國封建社會作為一個大系統,而具體的分析了其下政治、經濟、思想三個子系統之間的內部關系及相互作用,并得出了這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使中國封建社會具備了內在調節機制,正是這種特殊的機制使它每隔兩三百年就發生一次周期性的崩潰,消滅或壓抑了系統中的不穩定因素并恢復舊有結構。金觀濤指出控制論把這種系統稱為超穩定系統,其特征就是穩定性和周期性振蕩,因此可以說中國封建社會實際上就是一個超穩定結構,這也是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
這一理論,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和激烈討論。一方面,部分學者對此持稱贊和贊同的態度,如1981年陳平年發表了《社會傳統和經濟結構的關系》[2]一文,引入了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對我國經濟結構進行剖析,得出了我國經濟結構類似于力學中的“亞穩態結構”的結論。在政治角度上,1982年李桂海發表的文章[3],運用了控制論的方法對中國政治結構中的反饋調節機制、反饋調節機制的阻礙而導致的政治結構的僵化、以及反饋調節的周期性震蕩的分析,贊同了金觀濤的超穩定結構說。
另一方面,對此持批評態度的人也不在少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比如康建文的作品[4],他認為控制論和系統論的思想實質上都能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得到徹底的解釋,作者并不反對將控制論及其他的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運用于史學研究,但是絕不能企圖用控制論來代替馬克思主義,也不能將社會結構作為歷史研究的主要對象。而在1990年魯小兵的評論中則對金觀濤所用的是否為系統論、控制論方法提出了質疑,他認為金觀濤的超穩定結構說實際上是一種傳統的封閉系統方法,同現代科學的系統論與控制論是對立的。
筆者認為金觀濤先生的書中確實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問題。比如作者在論述為什么中國封建社會沒有步入新的社會結構時說:“中國封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很有點象西西弗斯推石頭……在王朝崩潰行瓦解時,就象大石頭從山頂滾到山下,新王朝不得不重新開始積累。”[1][P153],其對于中國封建社會的論述更像是一種運動陷入了循環往復的過程,他認為中國封建社會是一種停滯狀態,也因此稱它為超穩定的。但事實上,每次王朝的更迭和動亂確實對整個社會政治、經濟造成了巨大影響,但這并不是說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是一種循環往復式的停滯狀態,雖然中國古代社會一直沒有跳出和沖破封建社會的牢籠,但其一直是不斷的積累的前進的。每次動亂和破壞確實會對其發展造成中斷,但也并不是一種清空再重新累積的狀態。
同時,作者的論述實質上仍是以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結構的特點出發所進行的一系列論述,作者論述的關鍵點在于中國封建社會為什么會出現周期性波動,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就是中國封建社會自身政治、經濟、文化因素的影響。因此“中國封建社會的停滯是不是由于他正好是一個超穩定系統”[1][P8]實際上是一個偽命題,作者實質上仍是從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結構來論述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的原因,而通過中國封建社會的這些特征與其認為的“超穩定結構”有著形式上的相似,即周期性波動以及結構上長期停滯,得出了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超穩定結構。同時,由于超穩定結構本身涉及到數學模型的問題,我們不能僅僅因為其特征的相似性而論述其結構的相似性,因此中國封建社會究竟是否是系統論、控制論下所說的“超穩定結構”還有待商榷。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本著作不僅引起了史學界對于系統論的關注,更推動了自然科學同史學研究的結合。同時書中新穎的視角,為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提供了許多新思路,推動了史學界思想的解放,就這點而言,它雖然是金觀濤夫婦第一部論述系統論、控制論與中國封建社會關系的書籍,是還不成熟的結果,但已經起到了其作用和效果。
2 超穩定結構對于史學研究的啟示
通過對金觀濤夫婦超穩定結構的評論,我們可以從中看到系統論甚至是自然科學究竟應該如何同史學研究結合起來。
首先,是系統論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系。實際上,唯物史觀確實是我們研究歷史必須堅持的理論指導,其地位是不可動搖的,系統論不能取代馬克思主義,但其本身卻可以促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和進步,系統論是對馬克思主義一般規律的一種補充和理解。實際上,馬克思主義本身就十分重視聯系的觀點、辯證的觀點,馬克思主義正是唯物論同辯證法的有機結合,系統論實際上是對其中聯系、整體的觀點的深化。正如吳廷嘉教授所說:“歷史是一個由社會運動各個方面有機組織起來的大系統運動,要有復雜的立體式的網絡關系,而不是機械歷史唯物論所規定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那種三段式塔式結構。”[5]也就是說在歷史的發展運動之中,一切事物都是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只是這些因素的力量是不平衡的,有大或小。將系統論的觀點運用于史學研究,同歷史唯物主義有機結合起來,能更準確地幫助我們運用唯物史觀進行歷史研究。
其次,系統論作為自然科學的內容,將其運用在史學研究中本身就涉及到兩個交叉學科的運用,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對兩者都有較為深入的了解才能運用得當,就如苗東升先生在評價金觀濤的超穩定結構時認為其實質上與阿希貝的超穩定性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是一種自創的理論,這就提醒我們在將系統論用于史學研究時必須更加謹慎求證。同時,由于自然科學往往涉及到數學模型,一方面對研究者的能力要求較高,另一方面,歷史作為一門人文學科其中存在的許多因素本身是不能完全量化的,而且本身歷史事件本身包含著許多復雜的不可控的因素,這也是為何將系統論運用于中國封建社會研究時模型十分難以建立的原因。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具備運用的能力,更要在運用時嚴格思考哪些因素可以進行定量分析,哪些因素不可進行定量分析,將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結合起來,才能更加準確地剖析歷史事件的本質。
最后,我們可以預見隨著系統論在史學領域的運用,自然科學對史學領域的滲透本身是不可阻擋的趨勢,自然科學的運用對史學來說無疑會是一大助力,但同時在史學這個領域的研究中我們仍然要堅持的是以傳統的治史方法為主,而自然科學的運用比如統計學、計量學等等都是作為一種輔助工具,方便我們進行史學研究的工具來運用。在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下,通過旁通一些其他領域的知識來開闊我們歷史研究的思維,幫助我們更深入的了解歷史的本質。
參考文獻
[1]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
[2]陳平:《社會傳統和經濟結構的關系》[J],《學習與探索》,1981年第1期。
[3]李桂海:《從控制論的角度看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結構的僵化》[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2期.
[4]康建文:《歷史研究中的非馬克思主義傾向——簡析<中國歷史上封建社會的結構:一個超穩定系統>》[J],《貴陽師范學院學報》,1981年第4期.
[5]吳廷嘉:《論系統論在歷史學研究中的運用及其必然性》[J],《北京輕工業學院院報》,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