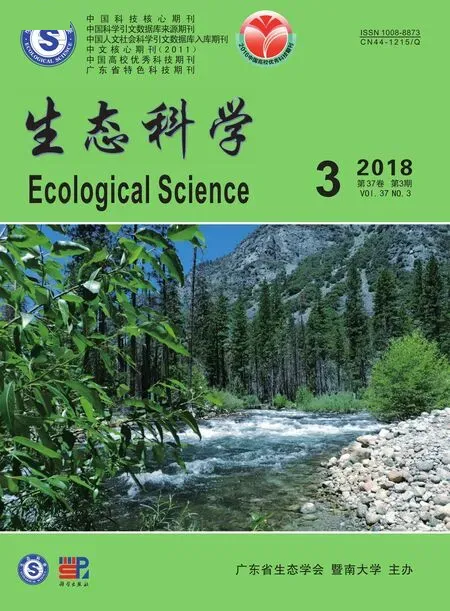合肥市土地利用變化及其生態系統響應研究
季軍民, 劉慶廣, 王愛
1. 合肥學院生物與環境工程學院, 合肥 230601
2. 合肥學院旅游系, 合肥 230601
3. 安徽師范大學國土資源與旅游學院, 蕪湖 241002
1 前言
生態系統服務是指通過生態系統的結構、過程和功能直接或間接得到的生命支持產品和服務, 其價值評估是生態環境保護、生態功能區劃、環境經濟核算和生態補償決策的重要依據和基礎[1]。1997年Costanza等對全球生態系統進行分類并估算其服務價值, 使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有了相對科學的研究方法[2]。我國學者將此方法應用到不同區域取得了許多成果[3-9], 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謝高地提出的中國生態系統單位面積生態服務價值當量表[10],目前我國的相關研究多是在謝高地的理論基礎上結合研究區實際情況進行深入分析與討論。
土地利用/覆蓋變化(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 LUCC)是全球變化的重要原因和驅動因子之一[11], 人類通過改變土地利用方式影響生態系統運行狀況, 改變區域生態系統向社會提供產品和服務的能力, 因而土地利用變化對生態系統的影響逐漸成為生態學研究的核心內容之一。近10年來, 隨著“中部崛起”、“濱湖新區”、“合肥都市圈”以及融入長三角的“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等重大戰略出臺, 合肥市的土地利用方式發生劇變,亟需對土地利用格局進行分析, 評價各土地利用類型的生態服務價值, 進而探討二者的響應情況, 為今后合肥市土地利用規劃和生態環境保護提供理論參考, 推動生態城市建設與可持續發展。
2 研究區概況及研究方法
2.1 研究區概況與數據來源
合肥, 簡稱廬或合, 是安徽省省會, 合肥都市圈中心城市, 皖江城市帶核心城市之一, 也是長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 國家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現代制造業基地和綜合交通樞紐。地處中國華東地區、江淮之間, 受亞熱帶氣候的影響, 全年平均氣溫15 ℃—16 ℃, 年降水量約1000 mm, 農作物以水稻、玉米、小麥、大豆、油菜為主。截至2014年底, 全市總人口為712.81萬人,GDP總值為5180.56億元, 同比增長10.6%, 人均生產總值67689元。合肥市下轄4區4縣1縣級市, 研究區確定為瑤海區、廬陽區、包河區、蜀山區。
土地利用數據主要來源合肥市國土資源局2004—2014年合肥市土地利用變更調查數據。為使研究數據統一, 將合肥市土地利用類型分為耕地、林地、園地、水域、建設用地和未利用地6類(表1)。
2.2 研究方法
單一土地利用類型動態度[12]是表示某研究區一定時間范圍內某種土地利用類型的數量變化情況,

圖1 研究區Fig. 1 Research area

表1 土地利用分類Tab. 1 Classification of land use
其表達式為:

式 1中,k為研究時段內某一土地利用類型動態度;Ua、Ub為研究始末土地利用類型面積大小;T為研究時間長度; 當把T以年計算時,K的值則為相應的年變化率。
2.2.2 生態服務功能價值
謝高地[13]提出糧食生產的單位面積價值量為884.9元·hm-2, 安徽省的修正因子為1.17,修正得到合肥市1個當量因子的經濟價值量為1035.33元。各類土地利用類型在計算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時按以下原則: 耕地對應農田, 林地對應森林, 園地對應草地,水域對應河流與湖泊, 未利用地對應荒地, 將建設用地的生態服務價值賦值為0, 進而編制出合肥市生態系統單位面積服務功能價值核算表(表2)。
利用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核算表, 應用 Costanza等[2]提出的估計研究區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變化的估算公式, 計算公式如下:
表2 合肥市生態系統單位面積服務功能價值核算表(元·hm)Tab. 2 Hefei ecological system unit area service function value accounting table

表2 合肥市生態系統單位面積服務功能價值核算表(元·hm)Tab. 2 Hefei ecological system unit area service function value accounting table
生態服務類型 耕地 林地 園地 水域 未利用地氣體調節 745.44 4472.63 1553.00 528.02 62.12氣候調節 1004.27 4213.79 1615.11 2130.78 134.59水源涵養 797.20 4234.50 1573.70 19433.14 72.47土壤形成與保護 1521.94 4162.03 2319.14 424.49 176.01廢物處理 1439.11 1780.77 1366.64 15374.65 269.19生物多樣性保護 1056.04 4669.34 1936.07 3551.18 414.13食物生產 1035.33 341.66 445.19 548.72 20.71原材料 403.78 3085.28 372.72 362.37 41.41娛樂文化 176.01 2153.49 900.74 4596.87 248.48總計 8179.11 29113.48 12082.30 46952.22 1439.11

式2中,ESV表示探究領域內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總價值;Ak表示的是探究領域內第k種用地類型的面積;VCk表示的是第k種用地類型的單位面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k=l,2,…,n,表示土地利用類型。
突出提升飲水安全水質保障能力這個環節。針對前些年實施的部分農村飲水安全工程未按規范要求配套凈化消毒設施、水質檢測設備和能力不足、未合理劃定水源保護區和飲水安全工程保護范圍等問題,水利部聯合國家發展改革委、衛生計生委和環境保護部下發了《關于加強農村飲水安全工程水質檢測能力建設的指導意見》,從能力建設任務、量化考核指標、檢測頻次、運行經費等方面提出明確要求。指導各省編制了總體建設方案,2014年將啟動第一批縣級水質檢測中心建設,為保障水質安全奠定基礎。開展了農村生活排水專題調研。
2.2.3 生態系統敏感性分析
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敏感性指數[14](The coefficient of sensitivity, CS)是為了驗證生態系統類型對于土地利用類型的代表性以及生態價值系數的準確性而引入的。CS數值越大, 則說明VC對ESV影響程度越大,ESV對于VC的變化越敏感。當CS<1, 表明 l%的自變量變動將引起因變量小于 1%的變動,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缺乏彈性, 其結果可信; 當CS>1, 表明l%的自變量變動將引起因變量大1%的變動, 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富有彈性, 則結果準確度較差和可信度較低。本文將合肥市各種土地利用類型的VC分別上下調整50%來計算CS, 從而剖析合肥市VC對ESV的影響程度。具體公式如下:

CS為敏感性指數;ESVi為初始生態系統服務總價值;ESVj為調整后生態系統服務總價值;VCik為研究區第K種用地類型的初始價值系數;VCjk為研究區第K種用地類型調整后的價值系數。
3 結果與分析
3.1 合肥市土地利用變化分析
2004—2014年合肥市各種土地利用類型面積的變化如表 3所示, 土地利用格局變化顯著, 主要表現為“1減5增”。耕地面積以年均0.06%的速度減少了 3112 hm2, 是唯一減少的用地類型。林地、園地、水域、建設用地和未利用地呈增長態勢; 其中園地面積增長幅度最大, 凈增加了11490 hm2, 年均增長 19.24%; 建設用地面積增加最多, 共增加了96051 hm2, 年均增長8.38% ; 林地的比重有所下降,動態度為 1.7%; 未利用地增加了 33242 hm2, 動態度為4.56%。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10年間合肥市處于擴張階段, 用地面積不斷增加。由于合肥市人口和經濟不斷集聚, 建設用地增加顯著, 主要由耕地轉化而來。水域面積10年間凈增加3575 hm2,主要是因為新建成大房郢水庫所致; 另一方面在郊區和農村地區開挖一些坑塘和小型水庫用來蓄水灌溉。合肥市城市園林綠地增加明顯, 體現了合肥市在城市建設時重視城市綠化與環境改善工作。而林地的大幅增加與全社會參與的大量的植樹造林工程密不可分,使生態城市建設的工作取得顯著成效。
3.2 合肥市生態服務價值變化分析

表3 2004—2014年合肥市土地利用變化Tab. 3 Urban land use change in Hefei from 2004 to2014
由表 4可以看出, 唯有耕地的生態服務價值在下降, 這是由耕地面積減少導致, 但耕地展總面積一半以上, 因此其提供的生態服務價值仍為第一;水域面積凈增3575 hm2, 且其單位面積生態服務價值最大, 水域的生態服務價值增加到 1678.54×105元; 林地單位面積生態服務價值僅次于水域, 由面積增加所帶來的收益達 1664.71×105元; 園地的生態服務價值增了 1388.25×105元, 則是園地用地面積的大幅度增長帶來的; 建設用地增量巨大, 占用了大量生態用地, 導致生態服務價值總體增長較為緩慢。

表4 各用地類型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變化Tab. 4 Various types of land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change

表5 各生態服務類型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變化Tab. 5 Various type of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change
上述分析可知, 耕地、水域和林地提供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占 96%以上, 耕地所帶來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始終最大, 說明合肥市生態系統結構較單一, 在保護耕地的基礎上調整用地結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的增長量主要是由水域、林地和園地帶來的, 但水域、林地和園地面積比例都比較小, 所以生態服務價值總量遠不及耕地, 表明合肥市在今后發展過程中,還需要提高綠化率,加強河流、湖泊濕地的保護, 擴大水域用地面積, 讓合肥市生態服務總價值不斷提高。
通過表5可知, 合肥市單項生態服務系統的生態服務價值都在增長,其中水源涵養的服務價值量增加最多; 食物生產提供的服務價值增長最少。從比重看,水源涵養、娛樂文化和生物多樣性保護增幅較大, 食物生產、土壤形成與保護和氣候調節比重下降較大,其他生態服務類型比重變化不大。廢物處理、土壤形成與保護和水源涵養對生態系統的服務價值貢獻最大, 其次是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氣候調節。
據此可知, 土地利用變化與生態服務價值有明顯的關聯性。水域對水源涵養和廢物處理的生態服務價值起決定作用, 林地對原材料的生態服務價值其決定作用; 氣體調節和土壤形成與保護的生態服務價值主要取決于林地和園地面積的變化, 娛樂文化的生態服務價值主要取決于水域和林地的面積變化;氣候調節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生態服務價值變化則是林地、水域和園地三者共同作用的結果; 食物生產的生態服務價值主要來源于耕地, 因此其生態服務價值增加最少。
3.3 敏感性分析
通過表 6可知, 合肥市生態系統對各類用地的敏感性指數均小于 1, 表明生態系統服務總價值對于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系數是缺乏彈性的, 也證明了研究結果是可信的。敏感性指數依次為耕地>林地>水域>園地>未利用地, 其中園地的敏感性指數變化最大, 當其生態價值系數增加1%時, 生態系統服務總價值變化由2004年增加1.08%到2014年增加2.95%; 耕地的敏感性指數最高, 這主要是由于耕地面積最大和較高的單位面積生態服務價值; 敏感性指數的最低的為未利用地, 這表明未利用地生態價值系數的變化對生態系統服務總價值的影響較小。
對敏感性分析表明, 園地、水域和林地生態系統價值系數的改變會對生態系統服務總價值產生明顯的放大作用, 這與合肥市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變化是相對應的; 耕地的敏感性指數下降, 則由于表明耕地面積逐年減少。

表6 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敏感性分析Tab. 6 Analysis of sensitivity of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4 結論與討論
(1)2004—2014年合肥市土地利用結構有所變化, 耕地小幅度減少, 其他用地都有所增加。其中建設用地面積增加最為顯著, 這反映了10年間合肥市由于經濟發展和人口積聚等因素推動城市用地規模不斷擴大, 建設用地大量增加以滿足社會的用地需求。林地和園地面積持續增加, 這與合肥市實施退耕還林、大力開展植樹造林工程、增加園林綠地打造綠色城市和生態城市有關。水域面積的增加主要因為水庫建設造成的。
(2)區域土地利用變化不僅改變了土地利用類型、結構和數量, 還將對生態系統產生影響。從用地類型看, 單位面積耕地能提供較多的生態服務價值,今后應注重對耕地的保護與合理變更; 未利用地對生態系統的貢獻最小, 對此要加快向林地、園地轉變,以提高總的生態服務價值; 鑒于水域對生態服務功能的強大貢獻, 可以合理擴大水域用地面積。
(3)從單項生態服務類型看, 水源涵養和廢物處理所提供的生態服務價值較大, 在合理擴大水域面積的同時注重改善水質, 避免水域的生態服務功能下降; 建設用地大量占用生態用地, 致使城市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下降, 因此土地利用要更加集約,推動園林城市和生態城市建設, 維持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土壤形成于保護的生態功能; 娛樂文化的服務價值在城市生態系統中還有提高的潛在可能, 如在城市近郊推行農村生活體驗的方式來提高耕地在娛樂文化生態服務中的生態價值。
(4)敏感性指數都小于 1, 表明研究結果可信,能夠為城市的土地規劃和利用提供指導。因此要注重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研究, 為土地利用規劃提供科學指導, 確保城市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改善生態環境, 實現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協調發展。
[1] 謝高地, 張彩霞, 張雷明, 等. 基于單位面積價值當量因子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化方法改進[J]. 自然資源學報,2015, 30(8): 1243-1254.
[2] COSTANNZA R, D’ARGE R, GROOT R D, et al. 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e capital[J]. Nature, 1997, 387(1): 3-15.
[3] 陳仲新, 張新時. 中國生態系統效益的價值[J]. 科學通報, 2000, 45(1): 17-22.
[4] 謝高地, 張釔鋰, 魯春霞, 等. 中國自然草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J]. 自然資源學報, 2001, 16(1): 47-53.
[5] 石培禮, 李文華, 何維明, 等. 川西天然林生態服務功能的經濟價值[J]. 山地學報, 2002, 20(1): 75-79.
[6] 楊清偉, 藍崇鈺, 辛琨. 廣東-海南海岸帶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J]. 海洋環境科學, 2003,22(4):25-29.
[7] 謝高地, 魯春霞, 冷允法, 等. 青藏高原生態資產的價值評估[J]. 自然資源學報, 2003, 18(2): 189-196.
[8] 王宗明, 張柏, 張樹清. 吉林省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變化研究[J]. 自然資源學報, 2004, 19(1): 55-61.
[9] 歐陽志云, 王效科, 苗鴻. 中國陸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及其生態經濟價值的初步研究[J]. 生態學報, 1999 ,19(5):607-613.
[10] 謝高地, 甄霖, 魯春霞, 等. 一個基于專家知識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化方法[J]. 自然資源學報, 2008, 23(5): 911-919.
[11] 宋戈, 李娜, 李靜, 等. 建三江墾區土地利用/覆蓋變化與生態環境效應作用機理研究[J]. 經濟地理, 2011, 31(5):816-821.
[12] 司慧娟, 袁春, 周偉. 青海省土地利用變化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影響研究[J]. 干旱地區農業研究, 2016, 34(3):254-260.
[13] 謝高地, 肖玉, 甄霖, 等. 我國糧食生產的生態服務價值研究[J]. 中國生態農業學報, 2005, 13(3): 10-13.
[14] 國洪磊, 周啟剛. 三峽庫區蓄水前后土地利用變化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影響[J]. 水土保持研究, 2016, 23(5):222-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