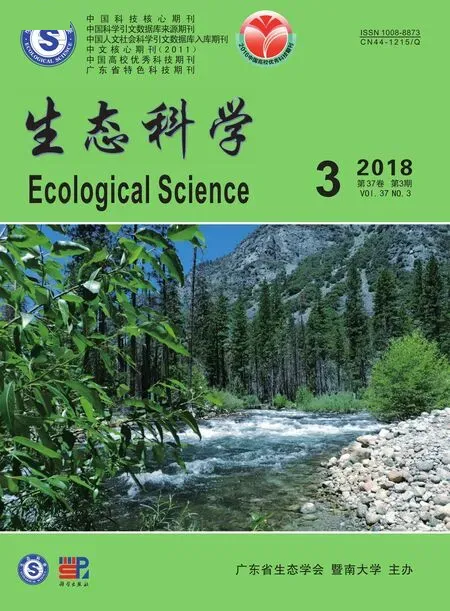濱海鹽漬土地區水稻田C、N及生物量動態變化的模擬與應用
李強, 李建國, , 張忠啟,
1. 江蘇師范大學地理測繪與城鄉規劃學院, 徐州 221116
2. 南京大學國土資源與旅游學系, 南京 210093
3. 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土壤與農業可持續發展國家重點實驗室, 南京 21008
1 前言
濱海鹽漬土的圍墾開發是目前我國后備土地資源開發的主要對象, 是緩解東部土地資源供需矛盾,糧食安全問題和經濟發展壓力的重要舉措[1-2]。濱海灘涂開發方式多樣, 耕作、養殖、保護區、居民點、港口和工業園區等開發方式都存在。其中, 農業耕作是較為常見的開發方式。以江蘇為例, 國務院2009年通過的《江蘇沿海灘涂開發規劃》明確規定農業、工業和生態用地的比例嚴格限定為6:2:2[3-4]。沿海土壤中廣泛富集的鈉離子等鹽分離子可以引起植物生理性缺水, 抑制作物對其他養分的吸收, 導致作物發育不良進而導致減產或死亡。大面積灘涂土地通過在灘地上圈筑圍堤墾殖, 經引淡淋洗、蓄淡養清、種植耐鹽作物等措施, 加速土壤脫鹽, 使得有機碳積累, 將鹽漬土改良為具有良好土壤肥力的土地, 成為中國重要的耕地后備資源之一。濱海灘涂鹽漬土農業改良的關鍵是在降低土壤鹽分的同時,提升土壤的C、N含量, 促進糧食產量的快速提升。總而言之, 要快速提升土壤的生產供給能力。而鹽漬土的生產供給能力受到氣候、鹽分、土壤養分、外源物質等因素的影響。溫度與濕度為代表的氣候因子變化會引起土壤微生物生理活性與一系列物理、化學性狀(如:土壤容積、壓力、氧化還原電位、分子間力、擴散力和表層張力)變化, 從而影響鹽漬土的碳氮循環及其生物量富集[5]; 土壤有機碳作為土壤質量的重要組成部分, 是評價土壤質量和影響作物產量的重要指標, 在土壤肥力、環境保護、農業可持續發展等方面均起極為重要的作用[6]; 外源有機物來源于作物秸稈、綠肥、廄肥、凋落物等農業耕作與管理行為, 不同的農業管理行為與習慣導致土壤中的有機碳組分和土壤理化環境差異巨大,影響有機殘體在土壤中的分解轉化, 成為養分循環的重要組分[7]。探求濱海鹽漬土改良過程中碳氮的循環累積過程及其與作物產量之間的關系對于理解灘涂鹽漬土改良與熟化的過程, 揭示耕作行為與碳氮循環及生物量之間的關系具有重要的意義。
隨著陸地生態系統模型的發展, 運用模型工具對土壤主要養分元素和生物量進行模擬與刻畫是目前較為有效的方法, 目前已有10多個相關模型發表,較成熟的有 DNDC[8]、Century[9]、Biome-BGC[10]、RothC[11]和NCSOIL[12]等。生態系統模型均可成熟應用于土壤長期定位實驗觀測數據的模擬與刻畫, 而這些模型中, DNDC模型是基于生物地球化學過程,以模擬輻射、溫度、濕度、pH、Eh以及濃度梯度等為主的環境因子來反映氣候、土壤、植被和人類活動 4種基本的生態驅動力[13], 具有多尺度, 高精度以及良好的適用性。在鹽漬土改良過程中, 傳統的水稻種植具有較好的脫鹽效果和有機碳累積速率,是灘涂墾區鹽漬土中廣泛種植的農作物。本研究以江蘇省如東縣的灘涂墾區長期觀測水稻田為例, 通過收集水稻田的施肥、灌溉、土壤理化屬性、區域氣候條件以及生物量等數據, 借助DNDC模型刻畫與模擬研究區水稻田在一個完整生長周期下土壤C、N及生物量變化過程。檢驗DNDC模型在沿海鹽漬土生物地球化學循環的適用性, 并對其精度進行評估。這對于研究濱海鹽漬土改良過程中土壤質量提升的策略, 揭示土壤養分元素循環累積過程與規律具有重要意義。對于制定未來科學合理的鹽漬土改良方案提供重要參考依據。
2 材料與方法
2.1 田間實驗
2.1.1 試驗區概況
試驗田位于江蘇省南通市如東縣四橋村(北緯32°22′15.46′, 東經 121°22′26.64′), 氣候屬亞熱帶海洋性季風氣候, 受海洋的調節和季風環流影響, 四季分明, 氣候溫和, 降水充沛, 光照充足。春季氣溫高, 夏季無酷暑, 秋季氣溫低, 冬季暖冬。年平均氣溫15 ℃, 平均日照時間超過2000 h, 無霜期達230天, 平均降雨量1042 mm, 降雨量年內分配不均, 汛期為6—9月, 雨量相對集中。如東縣境內地勢平坦,從西南略向東南傾斜, 西北部高程為 4—5 m, 東南部高程在3.2 m左右。試驗田地理位置如圖1所示。

圖1 試驗田區位Fig. 1 Location of experimental field
研究區鹽漬土廣布, 屬于潮鹽土亞類, 水稻—小麥輪作種植歷史超過100年, 土壤含鹽量在1 g·kg-1左右, 主要成分是NaCl。該地淺層地下水為咸水或微咸水, 礦化度高, 農田灌溉一般采用當地微咸水或引周圍河水灌溉。根據田間實測結果, 研究區土壤理化性質如表1所示。
2.1.2 試驗與方法
試驗于2016年6—11月水稻生長期開展, 研究區試驗田長為 51 m, 寬為23.5 m, 共計約 1.76畝,種植的水稻品種為寧稻13。試驗期間于6月10日、7月13日、8月11日、9月24日和10月30日采用九點法對田中土表0—10 cm土層采集土樣, 為確保每個土樣代表性良好, 采樣時在每個采樣點中心及東南西北4個方向上約30 cm處各采一個點, 將五個點采集的土樣混合, 作為該樣點土樣[14], 待土樣自然風干后, 除去石塊等雜物, 研磨后通過0.149 mm篩面過篩, 用四分法取約 10 g作為待測樣品, 使用碳氮儀測其有機碳與全氮含量, 測定方法見參考文獻[15]。水稻成熟后, 按照五點法在試驗田內均勻布置5個測產點, 每個測產點使用1 m2測產框量1 m2水稻將其連根挖出作為一組樣品, 并量出該點的 11行行距、11株株距, 5個測產點的行距與株距取平均,得出平均行距與平均株距, 測算田中水稻總棵數[16]。將 5組水稻樣品收割后曬干, 測算根、莖、葉、果實水稻各個部分的生物量。采樣結果作為與模型結果比對依據。
2.1.3 模型輸入參數確定

表1 試驗田土壤理化性質Tab. 1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experimental field
DNDC模型輸入參數包括氣候數據、土壤數據、作物數據和管理數據。其中, 氣象數據來自南通市如東縣氣象站點數據。土壤參數包括土壤質地、容重、pH、田間持水量等, 為田間實測數據(見表2)。如東縣土壤屬于東部濱海堆積平原沙壤鹽土, 對應模型中粘粒比0.06的Loamy Sand土壤質地值; 土壤容重使用環刀法進行測定, 在水稻種植前測定耕作層容重, 測量值為 1.78 g·cm-3; 土壤酸堿度使用電位測定法測定, 測量值為 7.8; 田間持水量使用鐵框法進行測定, 測定土壤自然含水量、飽和含水量和灌溉深度, 計算田間持水量為 27%; 土壤萎蔫點在水稻收割前測得, 作物萎蔫時土壤中尚存留的水分含量為 13%; 土表初始有機碳含量在水稻種植前采樣, 使用碳氮儀測得, 值為9.3 g·kg-1。作物數據使用模型定義的水稻數據, 見表3, 包括最大生物量、生物量比、生物量碳氮比、生長積溫等參數。管理數據為田間實測數據, 試驗期間共灌水 4次、施肥 4次(見表 4), 所施化肥種類為總氮大于 46.4%, 粒度范圍為0.85—2.80 mm的尿素, 施肥時間、化肥種類和用量詳見表4。
2.2 模擬計算
2.2.1 DNDC模型簡介
DNDC(denitrification—decomposition “脫氮—分解”)模型, 是目前國際上最成功的生物地球化學模型之一[17], 用于模擬農業生態系統中碳和氮的生物地球化學循環。DNDC模型包括 6個子模型, 分別用于模擬土壤氣候、農作物生長、有機質分解、硝化作用、反硝化作用和發酵過程[18]。該模型是對土壤碳、氮循環過程進行全面描述的機理模型, 適用于點位和區域尺度的任何氣候帶的農業生態系統的模擬[19]。目前, 世界上已經有很多國家的科學家使用DNDC模型進行應用研究, 如在美國愛荷華州馬斯凱丁縣對玉米生長過程的模擬[20]、在美國夏威夷對甘蔗的生長模擬[21]、中國東北遼寧對玉米產量進行模擬和分析[22]、英國帝國大學和農業研究所利用DNDC模型對英國種植的楊樹進行了7年的模擬研究[23]。2000年結束的亞太地區全球變化國際研討會上, DNDC模型被指定為在亞太地區進行推廣的首選生物地球化學模型[24]。

表2 輸入土壤參數Tab. 2 Soil parameters of model input

表3 輸入水稻參數Tab. 3 Rice parameters of model input

表4 水稻生育期灌溉與施肥措施Tab. 4 Irrigation and Fertilization quota during rice growing period
2.2.2 模型驗證與誤差評價
使用DNDC模型模擬2016年試驗田水稻生長期內碳、氮以及生物量動態變化。輸入參數包括逐日氣象數據、試驗田土壤理化性質數據、灌溉資料、施肥資料、作物參數等初始條件。輸出結果包括不同土層的有機碳和氮含量、水稻各部分生物量、作物水需求與水脅迫、氮需求與氮脅迫和溫室氣體排放等。對模型精度采用均方根誤差(RMSE)和相對誤差(RE)進行評價:

式中,Pi為第i個模擬值;Oi為第i個實測值;N為實測值個數。
3 結果與分析
3.1 土壤剖面有機碳模擬
利用DNDC模型模擬0—50 cm土壤有機碳分層狀況。如圖2所示, 在水稻種植期間, 0—50 cm各土層的土壤有機碳含量都隨著水稻種植時間的推移而減少。從播種到收獲, 試驗田0—10 cm有機碳減少 0.154 g·kg-1; 10—20 cm 減少 0.088 g·kg-1; 20—30 cm 減少 0.049 g·kg-1; 30—40 cm 減少 0.025 g·kg-1;40—50 cm減少0.012 g·kg-1。根據實測的驗證數據,試驗田在0—10 cm在整個模擬期SOC的RMSE為0.069。可以看出, 水稻生育期SOC下降程度由表層到深層遞減。水稻生育期0—50 cm各土層土壤有機碳平均含量都表現為由表層到深層遞減的規律,0—10 cm有機碳含量平均為9.165 g·kg-1; 10—20 cm為 9.234 g·kg-1; 20—30 cm 為 5.57 g·kg-1; 30—40 cm為 2.968 g·kg-1; 40—50 cm 為 1.58 g·kg-1。但模擬結果表明 0—10 cm平均 SOC要比 10—20 cm的低0.068 g·kg-1, 這主要是由于水稻田表層長時間處于浸水狀態而缺氧, 加之根系與微生物活動容易形成有機物質的富集層, 而長期灌水后 Eh迅速下降至100—200 mV, 土表經水的淋洗產生淋溶層, 有機質等養分經淋溶作用淋洗下移在犁底層以上土層聚集,造成10—20 cm土層SOC較0—10 cm土層稍高, 這與大量的水稻田實測結果相一致[25-28]。
3.2 土壤剖面銨態氮、硝態氮模擬

圖2 各土層SOC變化Fig. 2 SOC variation of soil layers
借助DNDC模型模擬濱海鹽漬土水稻種植期間土壤中尿素水平、銨態氮和硝態氮在水稻種植期間動態變化。如圖3所示, 水稻生育期0—50 cm尿素水平、銨態氮、硝態氮總體呈先升后降的趨勢, 但波動較為劇烈。以0—10 cm為例, 第150—190天期間銨態氮增加較為緩慢; 第190—284天驟然增加且起伏波動劇烈, 在第 194、205、232天分別出現三個明顯峰值; 第284—304天驟然降低。其余土層銨態氮變化趨勢與0—10 cm類似。這主要由于銨態氮含量變化受施肥控制的尿素水平影響較大。尿素是土壤氮重要的外源氮素, 常伴隨化肥的施用進入土壤表層, 土壤中尿素水平常伴隨施肥事件而顯著增加, 曲線突變比較明顯, 在沒有施肥事件的天數,土壤中尿素水平趨近于 0。土壤中尿素含量于第189、201、229天出現三個明顯的峰值, 這三天對應著水稻生長期間3次施肥事件的日期, 即2016年的7月9日、7月22日和8月17日。根據DNDC模型模擬結果, 三次施肥所施加氮肥數量轉化為土壤尿素的效率分別為69.68%、49.50%、43.05%。土壤0—10 cm銨態氮含量與尿素水平呈明顯的高度一致變化趨勢(圖3)。在模型模擬中, 通常當尿素水平峰值出現2至4天后, 土壤中銨態氮含量會出現一個峰值, 且銨態氮峰值過后, 銨態氮含量相比上一次施肥后顯著增加。如在水稻種植期(第207—228天),土壤中銨態氮呈相對緩慢的增加趨勢, 平均含量4.96 g·kg-1; 在 8 月 17 日(第 229 天)添加尿素后, 土壤尿素水平出現峰值(6.98 g·kg-1), 土壤銨態氮含量在此2天后(第 231)也出現峰值(10.28 g·kg-1); 峰值出現后, 土壤中銨態氮含量平均為5.89 g·kg-1, 比施肥前增加18.75%。
從土壤剖面情況來看, 隨土層深度的增加,銨態氮、硝態氮含量逐漸減少。0—10 cm銨態氮從平均 4.18 g·kg-1減少至 0.251 g·kg-1(40—50 cm);硝態氮從平均0.977 g·kg-1(0—10 cm)減少至0.004 g·kg-1(40—50 cm)。硝態氮隨深度增加減少量最為顯著, 因為淺層土壤相比于深層土壤更容易接觸空氣, 加之硝化細菌與反硝化細菌多活動于土表,故淺層土壤中硝化反應與反硝化反應速率比深層土壤大, 淺層硝態氮變化比深層更加顯著[29], 以致到 40—50 cm 土層僅含有微量硝態氮(平均0.004 g·kg-1)。同時可以看出, 土壤中硝態氮含量與土壤水含量變化有顯著負相關表現, 相關系數達-0.881(圖4)。硝態氮在土壤中的含量出現了兩個峰值, 第一個峰值為第 217天(8月 5日), 硝態氮含量為5.12 g·kg-1; 第二個峰值為第299天(10月26日), 為3.92 g·kg-1。這兩次峰值出現依次對應7月末至8月初烤田、10月末烤田(該次烤田于水稻成熟期晚期, 為方便收割, 田中不再灌水)。在烤田時段, 土壤水含量逐漸減少, 硝態氮含量增加。硝態氮和土壤水相關性顯著是由于硝態氮極易被水運移, 且硝態氮水平運移速率受土壤含水量的影響較大, 硝態氮水平運移濃度與含水量具有明顯的相關性[30], 土壤含水量大, 更多的硝態氮被淋洗, 土壤中硝態氮的含量減少; 反之, 當土壤水含量少時, 沒有足夠的水淋洗硝態氮, 從而土壤中硝態氮含量增加。再者, 硝態氮相對銨態氮具有滯后性, 且含量上呈現此消彼長的特點。如0—10 cm土層中(圖3), 銨態氮含量于第202—209天峰值過后, 硝態氮含量于第207—229天才出現峰值, 而在此期間銨態氮含量明顯減少; 又如種植期末期第284—304天, 硝態氮含量在銨態氮含量顯著減少后 1天增加, 此后銨態氮含量明顯降低。主要原因是由施肥進入土壤的尿素先水解為銨態氮, 土壤 pH升高, 硝化效率增大[31], 但在好氧條件下, 外源碳的存在使得硝化反應相對滯后,好氧環境下盡管硝態氮充足, 但反硝化所需氮源往往不足[32], 導致圖3中硝態氮含量增加的滯后性。

圖3 氮素變化曲線Fig. 3 Nitrogen change curve

圖4 土壤水和硝態氮對應關系Fig. 4 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 water and nitrate nitrogen
3.3 水稻各部分生物量模擬
經測產實驗, 由式(1)、(2)計算得出(表5), 可以看出試驗區水稻根、莖、葉、果實與總生物量實測分別為 2485.3、2824.9、2548.4、7215與 15073.5 kg·ha-1, 模擬的結果分別為 2036.9、2800.7、2800.7、7223.9與 14862.2 kg·ha-1, RMSE 分別為 337.27、207.28、464.30、447.36與397.92。經測算每畝水稻田中總生物量模擬值與實測值誤差為-1056.33 kg·ha-1, 相對于總生物量每畝可達2000 kg的水稻田,每畝實際誤差為70.42 kg, 誤差很小。根、莖、葉、果實生物量相對誤差基本都分布在實測產量20%誤差范圍以內。5組水稻樣本實際與模擬產量相對誤差結果如表6所示。五組樣本根生物量的相對誤差絕對值在 5.89%—19.97%之間; 莖生物量為 2.34%—8.23%; 葉生物量為 13.99%—26.4%; 果實為0.46%—8.23%。平均值分別為 13.57%、7.34%、18.59%、6.20%。可以看出模型模擬對于水稻果實的模擬結果最好, 水稻莖次之, 根和葉的模擬結果誤差最大, 其中以根的模擬最甚。試驗中根與葉的誤差較大可能是由于水稻生長過程和試驗采樣過程中, 一部分的根、葉會損壞或腐爛于泥土中,導致根、葉的實測值比模擬值偏低, 相對誤差較大,若將腐爛于地和采樣時損壞的根葉記入實際產量,根、葉的相對誤差會相對減小。

表5 試驗田水稻田模擬精度Tab. 5 Simulation precision of text field

表6 水稻產量模擬值與實測值比較Tab. 6 Comparison of simulated and observed values for rice yield
4 討論
4.1 與其他研究區模擬結果比較
由模擬結果所知(表6), DNDC模型在模擬濱海水稻田土壤碳、硝態氮、銨態氮以及生物量的模擬均方根誤差均小于20%, 其中SOC、莖生物量、果實生物量與總生物量均方根誤差小于10%。對比該模型在我國各個地區不同作物下模擬結果(表 7)。DNDC模型在我國東北、華北、西南以及太湖地區都表現出較好的精度, RMSE皆小于20%。將模擬地區與同是鹽土的公主嶺、松嫩平原、曲周縣相比, 研究區和公主嶺SOC模擬精度小于10%, 模擬精度好,而作物產量模擬精度在10%—15%之間, 模擬較好。其中, 位于東北的公主嶺、松嫩平原土壤類型屬于鹽堿土, 華北曲周縣土壤類型屬次生鹽漬土, 而重慶市與太湖地區屬非鹽漬土地區。可見在鹽漬土地區模擬, SOC比作物產量模擬精度要高; 將試驗區與非鹽漬土地區模擬結果進行比較, 作物產量模擬精度皆在5%—6%, 模擬精度好。但試驗區銨態氮模擬精度大于 15%, 相比太湖區域銨態氮 10%模擬精度較差, 硝態氮模擬精度與其持平, 鹽漬土區域模擬土壤銨態氮精度較差, 原因可能是試驗田模擬區域尺度比太湖區域尺度小, 采樣點少, 造成數據的不確定性大, 導致模擬精度較低; 與種植作物同是水稻的松嫩平原相比, 試驗田水稻產量模擬精度(5.06%)比松嫩平原豆—稻—玉米輪作的模擬(15.1%)精度要好, 在同是鹽漬土的地區, 在水稻產量模擬中, 可能中緯度模擬精度要比高緯度模擬精度高;與種植小麥和玉米的模擬結果相比, 試驗田水稻產量模擬精度(5.06%)、重慶市稻麥輪作產量模擬精度(6.77%)高于公主嶺玉米模擬精度(11.62%)和曲周縣小麥—玉米輪作(13.35%), 可見, DNDC模型對水稻或稻麥輪作作物產量模擬精度要優于玉米作物產量的模擬。同時, DNDC模型適用于我國多數地區大田作物模擬。模型不僅適用于像濱海地區1.76畝的試驗田局地、小尺度模擬, 也能滿足如一個縣、一個市、一個平原大尺度模擬[19,33-35], 對區域土壤肥力變化與大田作物產量大到宏觀把握, 小到微觀調控皆具有決策指導的實際作用。
4.2 濱海鹽漬土水稻種植管理優化途徑
江蘇東部灘涂鹽漬土圍墾地區為江蘇省農作物低產區。土壤含鹽量大、地下水礦化度高極大的抑制鹽漬土地區作物產量提升, 其水稻產量相較省內其他地區明顯偏低。試驗田實測產量為 7214.99 kg·ha-1, 比江蘇平均水稻產量低約 11.86%(8185.79 kg·ha-1), 且低于周邊城市淮安市約 7.98%(7840.8 kg·ha-1)[36]。尋求科學的施肥方法, 提升水稻產量, 是研究濱海鹽漬土碳、氮以及生物量變化的現實意義所在。借助DNDC模型模擬可以有效的揭示不同施肥管理方式對水稻產量的影響。

表7 我國各個區域DNDC模擬精度評價Tab. 7 Accuracy evaluation of DNDC simula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不同施肥條件下, 水稻生物量、耕作層(0—10 cm)C、N變化也有所差異。DNDC模型對比分析試驗田施尿素745.31 kg·ha-1的基準施肥量和不施肥條件下生物量以及土壤 C、N變化(如圖5所示)。施用745.31 kg·ha-1尿素比不施用肥料生物產量增加3684.87 kg·ha-1。施用尿素時, 土壤銨態氮、硝態氮含量變化影響顯著, 較不施肥條件下土壤銨態氮、硝態氮含量增加明顯。但肥料施用對土壤有機碳影響不顯著。故而, 合理施用氮肥能夠提高耕作層土壤氮含量, 促使土壤肥力提升, 從而提高水稻產量。以試驗田中在水稻生長期內所施尿素745.31 kg·ha-1為基準, 依次增加或減少 10%的氮肥數量, 模擬水稻生物量(如圖6所示)。在減施肥料10%、20%、30%的試驗可見, 種植期內投放521.717—745.31 kg·ha-1時, 水稻產量的增加呈直線型迅速增長, 增長速率為14.77; 而當肥料從基準增施至10%后即氮肥投放至 745.31—819.84 kg·ha-1后, 化肥的增施對水稻產量的影響減緩, 速率為 3.40; 當施肥量增至 20%、30%時, 水稻達到最大生物量, 再增施肥料水稻的產量不會增加。由此可見, 在采用加施10%至20%氮肥時, 濱海水稻田產量可達到最大值, 通過增施肥的方法起到增產的目的。但使田中作物產量達到最大值的施肥量, 是否具有經濟效益, 還需進一步探討。

圖5 基準施肥量與不施肥條件下耕作層生物量、C、N對比Fig. 5 Comparison of biomass, C and N of tillage layer under reference fertilizer and non fertilization

圖6 不同施肥狀況下水稻產量Fig. 6 Rice yield under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conditions

圖7 不同土壤鹽漬化指標下水稻總生物量Fig. 7 Total biomass of rice under different soil salinity indexes
4.3 DNDC模型中土壤鹽漬化系數的討論
自DNDC模型9.3版本始, 在定義土壤理化性質的界面中出現了土壤鹽漬化系數(Soil Salinity Index)參數。該參數的出現引發鹽土研究人員的廣泛關注。在DNDC 9.5版本的操作手冊中對該參數如此定義:土壤鹽漬化系數取值范圍為 0—100, 如果參數大于 0, 土壤鹽分將影響作物生長和土壤微生物活性。目前國際上廣泛使用的土壤鹽漬化分級標準為:依照土壤含鹽總量(干土重%), 將鹽土分為弱鹽漬土(0.3%—0.5%)、中鹽漬土(0.5%—1.0%)、強鹽漬土(>1%)[37]。可見, 模型定義的土鹽 0—100取值范圍與國際慣用標準相異, 而操作手冊上缺乏對該系數定義的具體說明。從中外文獻索引中使用 Soil Salinity Index關鍵字進行索引, 相關文獻數量為0, 尚無學者對這個參數有詳細的研究。為研究定義該參數對模擬實驗的響應, 試驗中將該參數定義為0、50、100以觀察作物產量對此參數的影響。結果如圖7可知,改變土壤鹽漬化參數, 對水稻總生物量沒有影響,即便將土壤鹽漬化系數定義為模型的上限 100, 水稻仍舊正常生長。可見, 作物生長過程生物量變化對土鹽指標無響應。因此可以發現, 該模型對于土壤鹽漬化水平對作物上生長的影響機理刻畫還有待進一步提高, 未來需要重點關注土壤鹽分與作物生長的回饋耦合關系。這在提高模型在濱海鹽漬土生物地球化學循環模擬精度, 提升模型在鹽漬土農業管理中的應用價值具有更大的潛力。
5 結論
(1)DNDC模型能夠很好的模擬濱海鹽漬土水稻田0—50 cm各土層SOC、N與生物量的變化, 模擬的土壤碳和生物量 RMSE均小于 10%(7.05%、5.06%); 銨態氮和硝態氮RMSE小于20%(18.75%、15.04%); 在對水稻各個部分生物量的模擬中, 果實(6.2%)、莖(7.34%)模擬精度好, 而根(13.57%)、葉(18.59%)模擬精度相對較差, 模擬結果可信。
(2)DNDC模型模擬在鹽漬土區域 SOC的模擬精度表現最好, 作物產量其次, 銨態氮和硝態氮精度最差, 模型模擬水稻生物產量精度相對玉米較高。當前DNDC 9.5版本定義的土壤鹽漬化系數對鹽漬土區域土壤鹽分含量與作物生長之間的互饋耦合關系的表達較差, 對于目前廣泛種植的高產雜交水稻作物品種的考慮不夠, 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3)借助DNDC模型模型, 在改良水稻田種植管理方式上, 根據試驗區水稻種植管理的經驗提出適當增加氮肥的投入促進水稻增產的思路。結果表明,加施 10%—20%氮肥可使試驗田水稻產量最大化,相比不施肥情況下, 試驗田水稻最大可增產56.65%。
[1] SUN Zhigao, SUN Wenguang, TONG Chuan, et al. China’s coastal wetlands: Conservation history, implementation efforts, existing issues and strategies for future improvement [J].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2015, 79: 25-41.
[2] 李建國, 濮勵杰, 朱明,等. 土壤鹽漬化研究現狀及未來研究熱點[J]. 地理學報, 2012, 67(9): 1233-1245.
[3] DUAN Huabo, ZHANG Hui, HUANG Qifei, et al.Character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analysis of sea land reclamation activities in China [J].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2016, 130: 128-137.
[4] 李建國, 濮勵杰, 徐彩瑤, 等. 1977—2014年江蘇中部濱海濕地演化與圍墾空間演變趨勢[J]. 地理學報, 2015,70(1): 17-28.
[5] 劉立軍, 徐偉, 桑大志, 等. 實地氮肥管理提高水稻氮肥利用效率[J]. 作物學報, 2006, 32(7): 987-994.
[6] 李長生. 土壤碳儲量減少:中國農業之隱患——中美農業生態系統碳循環對比研究[J]. 第四紀研究, 2000, 20(4):345-350.
[7] 張黎明. 太湖地區水稻土有機碳演變模擬的尺度效應研究[D].南京: 南京農業大學, 2009.
[8] 夏文建, 周衛, 梁國慶, 等. 稻麥輪作農田氮素循環的dndc模型分析[J]. 植物營養與肥料學報, 2012(1): 77-88.
[9] 高崇升, 楊國亭, 王建國, 等. Century模型在農田生態系統中的應用及其參數確定[J]. 土壤與作物, 2006, 22(1):50-52.
[10] 韓其飛, 羅格平, 李超凡, 等. 基于 biome-bgc模型的天山北坡森林生態系統碳動態模擬[J]. 干旱區研究, 2014,31(3): 375-382.
[11] 王金洲. Rothc模型模擬我國典型旱地土壤的有機碳動態及平衡點[D]. 北京: 中國農業科學院, 2011.
[12] NOIROT-COSSON P E, DHAOUADI K, ETIEVANT V, et al. Parameterisation of the ncsoil model to simulate c and n short-term mineralisation of exogenous organic matter in different soils[J]. Soil Biology & Biochemistry, 2017, 104:128-140.
[13] 李長生. 生物地球化學的概念與方法──dndc模型的發展[J]. 第四紀研究, 2001, 21(2): 89-99.
[14] 王相平, 楊勁松, 姚榮江, 等. 蘇北灘涂水稻微咸水灌溉模式及土壤鹽分動態變化[J]. 農業工程學報, 2014, 30(7):54-63.
[15] 王巧環, 任玉芬, 孟齡, 等. 元素分析儀同時測定土壤中全氮和有機碳[J]. 分析試驗室, 2013, 10(10): 41-45.
[16] 何瑞銀, 羅漢亞, 李玉同, 等. 水稻不同種植方式的比較試驗與評價[J]. 農業工程學報, 2008, 24(1): 167-171.
[17] LI Changsheng, FROLKING S, HARRISS R. Modeling carbon biogeochemistry in agricultural soils [J]. Global Biogeochemical Cycles, 1994, 8(3): 237-254.
[18] LI Changsheng, ZHUANG Y H, FROLKING S, et al.Modeling soil organic carbon change in croplands of China [J].Ecological Applications, 2003, 13(2): 327-336.
[19] 邱建軍, 王立剛, 李虎, 等. 農田土壤有機碳含量對作物產量影響的模擬研究[J]. 中國農業科學, 2009, 42(1):154-161.
[20] LI Changsheng, FARAHBAKHSHAZAD N, DAN B J, et al.Modeling nitrate leaching with a biogeochemical model modified based on observations in a row-crop field in iowa [J].Ecological Modelling, 2006, 196(1/2): 116-130.
[21] SHLOMO ORR, LI Jing. Modeling of virus transport in the subsurface, southern oahu, hawaii [D].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1997.
[22] 喻朝慶, 李長生, 張峰, 等. 大尺度農業因旱減產動態預報及不同空間尺度的災情重現期變化評估:以遼寧省為例[C]. 北京: 中國氣象學會年會, 2014: 1-17.
[23] GUO Miao, LITTLEWOOD J, JOYCE J, et al. The environmental profile of bioethanol produced from current and potential future poplar feedstocks in the eu [J]. Green Chemistry, 2014, 16(11): 4680-4695.
[24] 陳海心, 孫本華, 馮浩, 等. 應用 dndc模型模擬關中地區農田長期施肥條件下土壤碳含量及作物產量[J]. 農業環境科學學報, 2014, 33(9): 1782-1790.
[25] 高效江, 胡雪峰, 王少平, 等. 淹水稻田中氮素損失及其對水環境影響的試驗研究[J]. 農業環境科學學報, 2001,20(4): 196-198.
[26] 李娟, 彭金靈, 康娟, 等. 減施氮肥對稻田土壤剖面養分分布特征的影響[J]. 熱帶作物學報, 2012, 33(8): 1378-1383.
[27] 李娟. 不同施肥模式對水稻生長發育及稻田剖面養分分布的影響[D]. 北京: 中國農業科學院, 2011.
[28] 趙言文, 劉輝, 胡正義, 等. 不同時期圍海造田水稻土肥力剖面分布特征[J]. 土壤通報, 2009(1): 56-59.
[29] 宋亞娜, 林智敏, 林艷. 氮肥對稻田土壤反硝化細菌群落結構和豐度的影響[J]. 中國生態農業學報, 2012, 20(1):7-12.
[30] 鄧建才, 陳效民, 柯用春, 等. 土壤水分對土壤中硝態氮水平運移的影響[J]. 中國環境科學, 2004, 24(3): 280-284.
[31] 王艾榮, 羅漢金, 梁博, 等. 硝化細菌在3種沉積土壤中的變化規律研究:Ⅰ硝化細菌與土壤種類的關系[J]. 農業環境科學學報, 2008, 27(2): 665-669.
[32] 李晨光, 王暄. 碳源利用方式對好氧顆粒污泥同步硝化反硝化的影響[J]. 工業水處理, 2009, 29(12): 66-69.
[33] 陳旭, 陳效民, 張聰聰, 等. 太湖地區小麥生育期麥田土壤銨態氮和硝態氮含量的模擬與預測[J]. 南京農業大學學報, 2015, 38(1): 93-100.
[34] 王德營, 姚艷敏, 司海青, 等. 黑土有機碳變化的 dndc模擬預測[J]. 中國生態農業學報, 2014, 22(3): 277-283.
[35] 楊興. 基于dndc模型土壤有機碳變化和作物產量空間估算[D]. 哈爾濱: 哈爾濱師范大學, 2015.
[36] 杜永林, 張巫軍, 吳曉然, 等. 江蘇省水稻產量時空變化特征[J]. 南京農業大學學報, 2014, 37(5): 7-12.
[37] 劉賽. 北疆引水工程邊坡防護現狀調查與植物的適應性[D].北京: 中國科學院大學,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