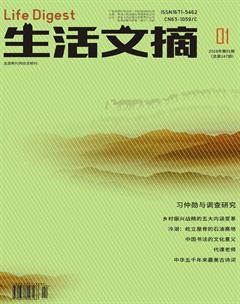西商之真偽與西安之進退
張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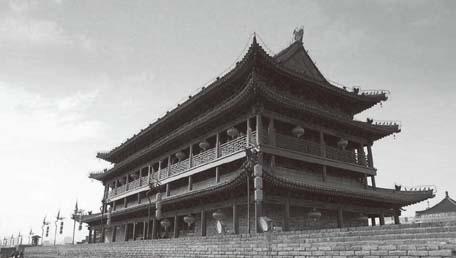


2017年7月份,西商大會宣傳廣告正式發布,這讓很多人迷惑,陜西商人一直以“秦商”或“陜商”稱呼,“西商”僅在明清之際因陜西和山西商人地緣相近、習俗相同、利益一致,合稱為西商或山陜商人。現在提出的西商能否作為西安商人或陜西商人的簡稱呢?在新的時代背景下,西安對西商又是如何界定呢?對此概念的提出,認為牽強附會、生搬硬套者有之,認為包容開放、切中西安時弊者亦有之。
8月18日,西安日報“長安新語”對西商解釋如下:“生在西安、長在西安、學在西安、創業在西安、結緣在西安的企業家都是‘西商”,我們總結為與西安有鏈接的商人都是“西商”。
眾所周知,中國歷史曾縱橫十大商幫,在以農業經濟為主體的封建社會促進了商品的流通、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明清之際,陜西商幫曾主導中西部食鹽、布匹、茶葉等貿易長達500年之久,宗鳴安先生在他的《秦商入川記》中認為陜西商人深受“關學”影響,亦稱儒商,以仁義為生財之道。
那么在今天,秦商大會已經召開8屆,西安市選擇另辟蹊徑召開首屆世界西商大會,用意何在?意欲何為?
對這一問題思考的直接背景之一是,改革開放39年來,我國區域經濟的較量逐步演變為城市乃至城市群的競爭,西安當前不僅落后于曾經的“西三角”成都和重慶,甚至被鄭州和武漢所超越,關中城市群亦落后于中原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曾經的長安繁華僅剩孤獨的自尊。
2017年以來,西安新的主政者開始正視差距,刮骨療毒,以改革創新、堅忍不拔之精神踐行西安“追趕超越”之路。在這樣一場變革中,西安的邏輯很明確,一方面以大招商的姿態試圖從外部引進更多的資本和產業,另一方面在內部則通過政府行政效能改革,優化營商環境,并激勵本地的創新創業來完成產業結構調整。
效果是明顯的,自從西安開啟這一輪變革以來,海航、京東、華僑城、吉利相繼攜巨資入陜,8月19日,馬云現身長安,并用一篇熱情洋溢的演講對西安的戰略價值和商業價值大加褒獎,阿里巴巴宣布將在西安建設西北總部基地。
無論是“央企入陜”還是“浙商入陜”,這些新西商們已經開始了各自在西安的征程,而西安市也開啟了自己的“追趕超越”之路。我們謹慎期待的是,經過這一輪的發展,西商的概念能夠真正地被歷史所記住,并為關中商幫的變遷貢獻新的價值。
一、西商之歷史溯源
周秦漢唐,西安曾是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長安城曾是絲綢之路的起點,唐代以后,隨著行政中心的北遷和經濟中心的南移,西安商業繁華逐漸衰落,回憶歷史,長安曾是絲綢之路的起點,中國商業文明的“元典”城市,亞歐大陸東西方貿易的交流中心,長安城東來西往之商賈,應是“西商”之鼻祖。
葛劍雄教授在《統一與分裂》中認為,秦、漢的政治中心在關中,而經濟中心在關東。因此,秦始皇“徙天下富豪于咸陽十二萬戶”,西漢遷徙關東富豪至關中諸陵8次。因政治原因強遷關東商人直接促成了長安財富的聚集和營商環境的提升,為絲路繁榮打下堅實的基礎。
西北大學李剛教授認為,公元前216年,秦國商人烏氏倮用絲綢同部族首領交換牛羊,部族首領則用這些絲綢,向盤踞在河西走廊的月氏和塞人交換他們從中亞、西亞、羅馬人手中交換來的黃金。漢武帝派張騫鑿空西域的原因亦因匈奴人阻礙了絲綢之路的貫通。
隋唐時期,長安城進入“客行野田間,比屋皆閉戶,借問屋中人,盡去作商賈”的商業高潮時代,唐代長安城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國際大都市。大唐西市聚集來自中亞、南亞、東南亞各國商人,尤以中亞與波斯、大食的“胡商”最多,現今西安回民街亦有絲路商旅之后裔。由于絲綢之路道路艱險,基本為秦商所經營。
明清時期,政府在陜西實行“食鹽開中”“茶馬交易”等優惠政策,陜西商人抓住歷史機遇,以西北川貴蒙藏為勢力范圍,輸茶于隴西,販鹽于江淮,運布于蘇湖,銷皮于江南,壟斷中西部貿易500年之久,位列中國十大商幫前茅, 甚至超越徽商和晉商。
通過梳理秦商的歷史脈絡,我們發現,統一的政權、開放的政策、變革的機遇都是秦商崛起所不可或缺的歷史和人文因素,當然,緊抓機遇、不畏艱辛,不辭勞苦與誠信經營等秦商精神亦是其發展壯大不可或缺的內因,清末的社會動蕩造成了秦商的衰落,直到改革開放后以浙商為代表的南方商幫迅速崛起壯大。
那么秦商與西商究竟有何關系?我們認為,西安具有悠久的歷史、開放包容的文化、便利的交通區位、久遠的商業文明,而當這一切成為歷史記憶,我們所要面對的是一個封閉落后的西部城市之時,西安需要以史為鑒,發揮秦商對于地區經濟中流砥柱的開創精神,引進央企、浙商等全國產業、資本與科技相融合,打造西北龍頭城市,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橋頭堡。
二、西商與現代西安
改革開放以來,西安匯聚了全國商賈,成為東西部經濟貿易的樞紐和平臺,涌現出一批知名企業和企業家,如秦商代表東盛集團董事長郭家學、步長集團董事長趙超;晉商代表金花投資控股集團董事長吳一堅、立豐集團董事長顏明;浙商代表中國廣廈西北區域集團董事長金欽法等。
在西安大街小巷,福建人經營連鎖超市和沙縣小吃、浙江義烏人經營小商品市場、四川人開川菜館和火鍋店,這其實都是改革開放以來西安商業文明的凸顯,也深深影響著這個城市的商業基因,2012年曾有媒體報道,10余萬來自福建寧德市周寧縣、福安縣、壽寧縣的“閩商”,懷揣幾萬乃至幾十萬元、幾百萬的資金,爭相闖進西安的背街小巷,將3萬多個規模不等的福建小超市開到百姓家門口,每年利潤45億元。
然而,無可否認的是,西安當地的營商環境并不強,尤其是本地人喜歡穩定,以進入體制內為榮,或者去南方打工。和沿海的創業精神形成鮮明的對比。西安的各個開發區則以均招商引資為己任,吸引外來投資逐漸成為西安市場經濟的中流砥柱,但這也部分掩蓋了城市內生動力不足的問題。
在本次西商大會表彰的10名“最具影響力西商”和12名“杰出西商”中,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馮侖和馮軍是作為西安人是當之無愧的秦商;柳傳志和周鴻祎是在西安讀的大學;王傳福和陳宇紅是新西安人;張朝陽和劉若鵬是生在西安,由此可見,西安寄希望于凝聚和團結西安商界有生力量,匯聚成發展的動力和源泉。
在當今全球化的市場經濟秩序下,交通設施、網絡媒介、信息技術正在深刻影響著商業環境,在當下,僅僅以戶籍和地域來稱謂傳統的地域性商幫也逐漸失去意義,以傳統產業、交通區域和團隊協作形成的商幫正在逐漸淡化,而以區域市場、科技成果和人文交流形成的經濟共同體正在逐步形成,西商就是在新的互聯網信息時代形成的以西安為地域、以地區經濟變革為己任的新的商幫,他的責任與使命已非常清晰,那就是“一帶一路”:新西安、 新經濟、 新活力。
浙商今年來在西安投資建設了很多項目,像復星集團入股永安財產保險,新光集團建設了“世界蘋果中心”,吉利汽車落戶經開區、正泰集團建設屋頂光伏發電項目。全國商幫正在齊聚西安,合作共贏將是西商新的起點與征程。
正如馬云所說“一個古都,如何能變成了一個商業之都,一個歷史名城變成一個時尚名城,一個原來良好的工業科技基地如何變成未來高科技、黑科技、硬科技的基地,這中間對每個人來說,都是挑戰,但更是一個機會”。
三、西商與大西安“追趕超越”
馬云認為,浙商、秦商絕不是狹義上的浙江人、陜西人,只要是在這片土地上生根成長的、血液里流淌著中華民族企業家精神的,都是助力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西商將給西安帶來什么?
雄厚的資本?規模化產業?科學的思維?領先的技術?我們認為主要是變革的力量和進取的勇氣,包容的心態和謙遜的做事風格,這才是一個現代化城市發展與超越的核心力量,從一句“讓院士先走”我們看到了秦商精神的回歸,西商正以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匯聚大西安“追趕超越”的能量,踐行經濟變革之時代使命。
西安擁有科研機構3000多家,院士60多人,科技人員100多萬,各類高校63所,在校大學生120萬,由于人才吸引力不強形成了“孔雀東南飛”,如何吸引人才?形成西商的人才支撐;西安是全國軍事裝備最強的城市,軍工技術實力雄厚,尤其在航空航天、核、電子、船舶、兵器領域具有明顯的領先優勢,由于國有企業體制的僵化、轉型困難造成市場化不足,深化改革將是西商發展的科技和產業力量。
當前的西安,國家戰略、全國商賈、科技人才已成澎湃匯聚之勢,無商不富,西商將是西安叱咤全國商海、縱橫全球市場的依托,新時期的西商,也當有符合時代潮流的商業精神,我們認為,西商將成為開拓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先行者,亦有秦商之不畏艱難之精神;西商為與西安有關聯商人之合稱,應具備合作共贏之精神;西商需要將西安的科技優勢轉化為生產力,應具備改革創新之精神。
西商應具備積極主動融入全球化的意識,總結起來,當代西商精神或可歸納為:不畏艱辛、合作共贏、改革創新、匯通全球!
這將是西商所凝聚的西安企業家的精神力量。8月21日,西安日報“長安新語”發表文章“要把西商大會辦成一場永不落幕的大會”,指出一是要平臺常態化;二是要聯系制度化;三是要服務精準化,讓西商大會和西商品牌,為大西安實現追趕超越發展凝聚更多力量!正如聯想董事長柳傳志所言,西安進入“實干期”。
商人是市場經濟的基石,市場經濟是深化改革的方向,深化改革需要市場主體的緊密配合,在我們看來,西商的開放性定義將是我們重新定義新時代商幫文化的一個典范,而這種開放性和包容性定義本身就意味著像西安這樣的區域和城市已經發生的改變。
摘自《方塘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