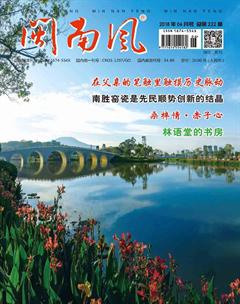思想、詩意、激情的完美融合
陳思慧
喜愛梁衡,是從讀到他的《大無大有周恩來》這篇散文開始的。當時我正被周秉德寫的《我的伯父周恩來》這本書感動得熱淚盈眶,剛好讀到梁衡的這篇散文更是潸然淚下。從此無可救藥地迷戀上他的所有人物散文。后來開始關注梁衡這個散文家,才知道原來他還是新聞理論家、科普作家和政論家。他的正業曾是新聞寫作、公文寫作,業余才是散文寫作。他寫的散文前期主要是山水散文,后期主要是人物散文。《千秋人物》這本書收入50篇人物散文,寫的大多是名垂宇宙,家喻戶曉的偉人,還有文驚當世,傳之百代的文人,每一篇都氣度不凡、精彩絕倫。這些散文深深地吸引著我影響著我,當我人生得意時,便去他的散文中找到理性和冷靜;當我暫時失意時,又在他的散文中找到勇氣和智慧。
梁衡的人物散文蘊含著大氣磅礴的思想。他把千秋人物當做普通人來寫,一人一事均能引發自身命運乃至國家、歷史命運的思考。他評價人物相當客觀、立體、生動、深沉。比如把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張聞天、鄧小平等政治人物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結合當時的國際國內環境、歷史發展狀況、擔當的政治角色等角度,客觀全面、實事求是地評價,亮點紛呈;比如寫范仲淹、辛棄疾、李清照、柳永、諸葛亮等歷史人物,以史實為依據,重點挖掘人物心靈,探究歷史沉浮,思考文化變遷,既感人肺腑又催人奮進;比如寫馬克思、居里夫人、普京等外國名人,充分體現“語不驚人死不休,篇無新意不出手”的標新立異和賞心悅目。
梁衡寫的人物,往往是民族的靈魂、歷史的脊梁和時代的驕子,他們的身上有著政治的理想和時代的氣質。如《周恩來讓座》中,寫周恩來的作風是,盡量為他人著想,絕不擺什么架子。而《鄧小平的堅持》中,鄧小平的堅持是意志力的表現,但意志力的背后是思想的穿透力。對韓愈這位命運坎坷的唐代文學家,梁衡最敬佩的是“當其獲罪海隅、家破人亡之時,尚能心系百姓”;對宋代名將范仲淹,梁衡最為折服的是他那“先憂后樂”的名言,“能創造一種精神,能提煉一種符合民心、符合歷史規律的思想”,讀后有耳目一新之感。同時,他寫的人物大都帶有濃郁的悲劇色彩。諸葛亮、韓愈、范仲淹、柳永、辛棄疾、李清照、林則徐、瞿秋白、彭德懷、張聞天……他們有時身處命運的逆流卻能在逆境中奮起,他們的人生經歷讓人在感嘆唏噓之外,更體會一種悲壯之美。正如梁衡說的“復雜的背景,跌宕的生活,嚴酷的環境,悲劇式的結局更能考驗和拷問一個人的人格。”
我想,梁衡之所以選擇這些人物書寫,之所以能夠寫出他們可歌可泣的靈魂氣質和悲壯之美,肯定也是與他憂國憂民的情懷分不開。季羨林就曾這樣評價過梁衡,說他是一位肯動腦,很刻苦,又滿懷憂國之情的人。“難得他總能將這一種政治抱負,化作美好的文學意境。在并世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這樣一種境界的人,除梁衡以外,尚無第二人。”
讀梁衡的人物散文,還能享受到優雅浪漫的詩意,這當然得益于他遣詞造句的用心和節奏韻律的自如,從而帶來心理鏡頭的韻味。他曾在《我的閱讀經歷》中提到古詩詞對他的寫作影響很大。當碰到某個感覺、某種心情無法用具像的手法和散體的句式來準確表達時,就要向詩借他山之石,以造成一種意境、節奏和韻律的美感。
所以,在他散文的字里行間總是流露出濃濃的古詩詞的美感。《一座小院和一條小路》寫鄧小平“文革”中被貶到江西強制勞動。“他每天循環往復地走在這條遠離京城的小路上,來時二十分鐘,去時還是二十分鐘,秋風乍起,衰草連天,田園將蕪。”這里用古詩里的句子,借秋景來營造一個意境,抒寫他憂郁的心情。如《梁思成落戶大同》一文的結尾:“我手撫這似古而新的城墻垛口,遠眺古城內外,在心中哦吟著這樣的句子:大同之城,世界大同。哲人之愛,無復西東。古城巍巍,朔風陣陣。先生安矣!在天之魂。”這種驚心動魄、蕩氣回腸、余音繞梁、久久不息的效果,沒有借助詩詞又如何能夠表達到位呢?
梁衡的散文語言還特別講究節奏韻律。《讀柳永》文末,梁衡直接抒懷“嗚呼,人生在世,天地共性。人各其志,人各其才,無大無小,貴賤不分。只要其心不死,才得其用,就能名垂后世,就不算虛度生命。”這段短句節奏明快、字字珠璣,振聾發聵,醍醐灌頂。而《青州說壽》結尾寫到,“在山上刻字的人終究留不住,留下的是這默默無言的山;把門樓修得很高的人還是存不住,長存的是那些曾用生命去肩動歷史車輪的人。”這里使用舒緩的長句,將全篇的立意再次升華。《紅毛線,藍毛線》中“紅毛線,藍毛線,二尺小桌,石頭會場,小石磨、舊伙房,誰能想到在兩個政權最后大決戰的時刻,共產黨就是祭起這些法寶,橫掃江北,問鼎北平的。”這里則把長句和短句完美結合,節奏韻律顯得輕松自如又貼切意境。梁衡對于人和事的觀察都非常細致,對細節的勾勒又特別具體,從而帶來了心理鏡頭的韻味,營造了優雅浪漫的詩意。
梁衡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做《為文第一要激動》。他談到為文為什么要激動,就是為了產生一種爆發力,才能震撼人心,感動讀者。我在閱讀梁衡散文時,確實每時每刻都在體會著這種爆發力。《把欄桿拍遍》,梁衡說辛棄疾的詞不是用筆寫成,而是用刀和劍刻成的。他是以一個沙場英雄和愛國將軍的形象留存在歷史上和自己的詩詞中。他說辛棄疾的成名,要有時代的運動,像地球大板塊的沖撞那樣,他時而被夾期間感受折磨,時而又被甩在一旁被迫冷靜思考,所以積三百年北宋南宋之動蕩,才產生了一個辛棄疾。讀著梁衡的這些文字,內心激動不已。正所謂“心不動,難為文”,這種“目既往還,心亦吐納”的爆發力也推動著梁衡在寫作的過程中,既有豐富自由的想象力,又有反觀當下的現實力。
《假如毛澤東去騎馬》,梁衡想象1965年至1969年,毛澤東深入民間四年,當他騎馬走黃河流域時,勾起對戰爭歲月的回憶和對老區人民的感念;當他走長江一線更多的是政治反思,是關于在這里曾發生過的許多極“左”的思考。歷史不能重復,但是可以思考,在思考中尋找教訓,捕捉規律,再創造新的歷史。讀完這篇文章,不由得佩服梁衡的想象力。《心中的桃花源》在梁衡的筆下,陶淵明不是政治家,卻勾勒出一個理想社會,讓人們不斷地去追求;他不是專門的游記作家,卻描繪了一幅最美的山水圖,讓人們不斷地去尋找;他不是專門的哲學家,卻給出了人生智慧,設計了一種最好的心態,讓人們去解脫。而《普京獨行在空曠的大街上》更有意思,是梁衡在網上看到普京對內低調對日強硬的幾條新聞,隨即寫成的一篇短文。文中,他想象著微風吹起普京西服的下擺,他揚起光頭,甩開一幅摔跤手的臂膀,目光向前。他一身膽氣,淡定自然。這不只是因為他柔道出身,有一身好武藝,還因別有一種政治上的自信。隨后他又聯想起毛澤東在延安的街頭,周恩來說戲,希拉里與兒童對話,默克爾買菜等等,梁衡說“他們都有一個坦誠的我,不是總拿自己當個官”。梁衡通過分析新聞或史實的資料,結合當下所有歷史環境因素和人物的性格心理狀態,竟然寫出一篇篇像“紀錄片”似的巧奪天工的散文。他的散文還能讓人們對照現在發生的事情,新的矛盾、新的課題,想起過去的偉人,發現許多事情在他們那里早已解決,或者深受啟發,得到一把打開現實之鎖的金鑰匙,讓人讀著不禁拍案叫絕,又似經歷了一場靈魂的洗禮。
梁衡踐行形、事、情、理、典“文章五訣”,倡導書寫大事、大情、大理。我以為,梁衡的散文是一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他的散文具有很強的教育意義,但這種教育不是說教,不是唱高調,而是能啟發人的哲學思考,這正是梁衡所說的“散文的哲理之美”。我想,這也是梁衡散文31篇、71次入選各類大、中、小學課本的原因所在吧。